
周汝昌自《紅樓夢》麵世以來 這一首封建末期由盛而衰的嘆歌就引來無數人的傾心與沉醉。《紅樓夢》以其巨大的文學價值 紅學代言人周汝昌,連書法都是泰鬥級?俞平伯:這種人不要理他 - 趣味新聞網

發表日期 3/25/2022, 3:33:53 PM
周汝昌
自《紅樓夢》麵世以來,這一首封建末期由盛而衰的嘆歌就引來無數人的傾心與沉醉。《紅樓夢》以其巨大的文學價值,細膩的人生百態和浪漫奢靡的貴族遺像帶給世人太多的驚嘆。
時至今日,人們對《紅樓夢》的研究依然如火如荼。不僅派係林立、分支繁多,其囊括的範圍也越來越廣,爭論也不曾休止。
以鬍適為代錶的新文化運動學者開始對《紅樓夢》進行的解讀和探索成為新紅學的開端。而當代被稱為“紅學泰鬥”周汝昌,順接鬍適的方法和思路,成為新中國成立後紅學研究的第一批領頭人物。
紅學研究領域學者爭論的程度之激烈、內容之廣泛、想象之新奇,個中精彩,不僅不輸於甲骨學、敦煌學這並稱為“20世紀三大顯學”的學術研究,而且因為民間認知的廣泛而引起更多人的關注和討論。
周汝昌
周汝昌作為考證派的主力人物,在上世紀轟轟烈烈的紅學研究中成為婦孺皆知的專傢人物。但是也正是這份聲望,讓他的主張太過高調,好似其平生研究與學問都與紅學牽連甚廣。
稍覽紅學領域的研究時文可以看見,紅學界對周汝昌的評價可謂是兩極分化甚重。
支持者認為他將《紅樓夢》其中細節與曆史原型一一對比糾正,稱他為“新中國紅學研究第一人”、“考證先鋒”、“悟證先河”,像孟子崇拜孔子一樣:紅學無他,萬古長如夜。
周汝昌紀念館中的紀念銅像
在反對者眼裏,周汝昌弄虛作假,僞造史料,篡改原意,扭麯事實,將《紅樓夢》的原文意義歪解,把這部如椽巨著當成自己名利雙收的工具,簡直是紅學的叛徒、學者的侮辱。
這種毀譽參半的評價在我們大多數人眼中是奇怪且陌生的,大多數人對《紅樓夢》的看法是一部流傳韆古的文學巨作,對於周汝昌的評價和紅學內部尤其是考證派之間的對立難以理解,唯有深入或能瞭解一二。
縱觀周老一生,其對紅樓夢的鑽研與投入,可以說少有人比肩。
周汝昌生於1918年,幼年便天資顯現。他入燕京大學西語係時21歲,彼時恰是日軍侵華的戰亂歲月,周汝昌卻能夠潛心讀書,獲得當時錢鍾書、鬍適等人的一眾贊賞。
燕京大學
幼年嚮學,《紅樓夢》如啓濛讀物一般給他留下深刻的印象,而真正踏入紅學研究領域還是因為一封偶然的來信。當時正在研究紅學的四哥周祜昌寫信,讓正在上學的周汝昌幫忙查證鬍適發錶的一篇新論。
論中說敦敏、敦誠為曹雪芹摯友,而周汝昌在敦敏詩集中發現瞭一首《詠芹詩》,他就此撰文並在《天津國民日報》發錶,引來鬍適的關注。也正是在與鬍適的信件交流中,周汝昌對紅學的研究熱情愈發高漲。
1948年,周汝昌為新書《紅樓夢新證》的編寫特地去拜訪鬍適,鬍適非常大方地將《甲戌本石頭記》、《四鬆堂集》抄本和有正書局石印大字戚序本藉給他研究,這讓周汝昌受寵若驚。
鬍適
1953年,《紅樓夢新證》一經齣版,就在紅學界引起轟動。後來人們瞭解到關於曹雪芹生平事跡的絲絲縷縷,大都與這部書緊密相連。
在翻閱這些珍藏本以及與鬍適的交流溝通中,周汝昌的紅學研究思路大受啓發,且對鬍適的寬厚頗為感激:“鬍先生能平等對他,還對他愛護有加,其人品和學問少有人比。”
也因為兩人這層關係,當鬍適作品的文學性和研究的科學性受到質疑時,周汝昌及其作品不可避免地也成為被質疑的對象。
李俊拜訪周汝昌
1974年,周汝昌任中國藝術研究院研究員,他又承擔起一項艱巨的任務――嚮中外大學和機構講解《紅樓夢》。他深厚的文學基礎和西語素養,一定程度上推動瞭這本名著在世界知名度,在當時的外交官員群體和海外大學中引起一陣熱潮。
周汝昌一生投身於考證鑽研裏,對《紅樓夢》的研究和傳播做齣毋庸置疑的貢獻。 他對紅學熱愛至深,正如他自己所說的:“藉玉通靈存翰墨,為芹辛苦見平生。”
考證一派,講究史料,無論文字或是實跡都要有一個確鑿的齣處。然而在周汝昌的紅學研究中最讓該流派其他紅學傢詬病的,便是幾次研究史料的僞造,甚至因此在晚年被罵騙子。
周汝昌青年
1973年,一首《題琵琶行傳奇》的佚詩在學者們當中廣泛流傳開來,這讓大傢欣喜若狂。詩句的後兩首明顯是曹雪芹的筆跡,如今全詩麵世,當真讓學者如獲至寶,紛紛稱贊。
然而1979年周汝昌卻承認,這首詩的前六句為自己試補。這則聲明讓吳世昌、俞平伯在內的許多紅學專傢目瞪口呆,毫無疑問,對真跡假辭無法分辨的事實讓他們的名聲有所損減。
而蔡義江、瀋治鈞等人還指齣,在周汝昌代錶作《紅樓夢新證》中引用瞭一首清代詩人周氏的一首《八聲甘州 薊門登眺憑吊雪芹》,以論證曹雪芹的葬處。
周汝昌一傢
而這首詩也曾經被蔡義江引用作為論據齣現在他的文章裏。
但這首詞的後兩句確是周汝昌自行添補完整的,並非作者原作,也正是這兩句將些許學者的研究目標趨近於接受周汝昌的結論。
學問研究不怕趨同,但是忌諱被誤導和牽引。蔡義江格外生氣,在《紅樓夢學刊》上撰文澄清。一些紅學傢也以此刊為陣地對周汝昌進行批判。
在這兩起著名的僞造事件裏,周汝昌並不清白。也因此引起瞭一些學者對其著作中其他考證真實性的懷疑,韆絲萬縷的追究、真真假假的關係、你來我往的駁斥,讓這個圈子內的風氣在學術道路上似有偏離。
《紅樓夢新證》
紅學流派甚多,除瞭考證派,還有索引派、評論派、創作派。評論派和創作品聚焦於欣賞作品本身,考證派旨在挖掘曹雪芹生平,索引派則願意將書中故事作為曆史事實的隱喻加以解析。
《紅樓夢》凝結著作者的心血,或許還用生平際遇穿針引綫,鋪墊於這個恢弘且悲涼的末世一隅。
藝術來源於生活,但是同時藝術也會高於生活。對藝術靈感源頭的過分細究,就好比指著斷臂維納斯研究其石料的組成成分一般,拉低瞭作為藝術本身的精神意義。
周汝昌與夫人毛淑仁
周汝昌與夫人毛淑仁
話雖如此,周汝昌作為自由天資齣眾的人物,過人之處遠不止此。但是介於他在紅學領域的深入,人們往往會忽視他在其他領域的學術貢獻。
當年他還在燕京大學讀西語時,就以極高的天分翻譯瞭《文賦》。《文賦》是中國古代文學理論著作,是極其晦澀難懂的駢體文,連翻譯成白話文都需要極大的精力,遑論英文。
他的這篇英譯論文獲得教授們的全票通過。後經推薦進入中文係研究院,將《二十四詩品》等文學經典陸續翻譯,輸齣海外,又將雪萊的《西風頌》以《離騷》的韻腳詩體翻譯引進,成為當時中外文化交流不可多得的人纔。
周汝昌著《蘭亭鞦夜錄》
除瞭在文學、詩詞領域大放異彩,周汝昌在書法研究中也頗有心得。他不僅齣版《書法藝術問答》,將《蘭亭序》的構墨筆法、起承轉閤進行深入研究,還獲得瞭包括啓功在內三位書法大傢的贊賞。
在這本書中,他提齣瞭許多獨到的見解,在書法界讓人耳目一新,在對曆代仿寫評判分析時有理有據,讓人佩服。
但是人們在圍繞一個人的盛名太久時,往往會被這種光芒暈眩而對事實的景象缺乏客觀評判。
周汝昌書法
雖然周老在書法理論中有所成就,但是他本身的書法作品並沒有一些人吹捧得那麼前無古人、後無來者。
周汝昌的書法留存不多,因其晚年眼疾加劇,鮮少再拿筆。
實際上,他作為深受文學熏陶的文人學者,書法技藝自然不會生疏,但是論起爐火純青、自成一格還是稍有誇口的。
從他留存的若乾幅作品中可以看齣,雖然筆跡留有鋒芒,但是卻並不能適應大多數人對書法之美的認同。“一流的瘦金體”、“書法泰鬥”、“一代大師”等美譽加之於上,反而更顯言過其實。
俞平伯
紅學名傢之一的俞平伯曾經說:“這種人不要理他。”除瞭早年因周汝昌續詩之事有瞭壞印象,那些外界自發給周汝昌戴上的虛浮的稱贊,也從側麵敗壞瞭周老在學界的名望。
人們喜歡造神,除瞭提供一定的精神指引,還有不少潛藏在這種聲譽背後的小九九。無論是為瞭閤群而趨炎附勢,還是為瞭藉殼抒發自己的觀點,周汝昌在書法領域被稱贊得太過,在那群自嗨的人之外,總有無數冷眼旁觀。
周汝昌在2012年逝世,去世前一晚,還在勾畫構思著關於《紅樓夢》的一些文字。可謂對《紅樓夢》摯愛之深,對紅學鞠躬盡瘁。
周汝昌著《詩詞賞會》
但是看盡周汝昌一生,他的成就不是單單幾部紅學研究可以概括的。周策縱先生曾說:“周汝昌治學以語言、詩詞理論及簽注、中外文翻譯為主;平生耽吟詠、研詩詞、箋注、賞析、理論皆所用心。”
《唐詩宋詞鑒賞辭典》、《白居易詩選》、《詩詞賞會》等賞析著作可見其文學研究之功底,是市麵上為數不多接受度、推薦度都比較高的詩詞賞析作品。
在《中國北京奧運賦》中,周汝昌遣詞造句無不軒昂恢弘;在《校後再記賦詩》中,周汝昌將自己對作者和書的情感一展無疑;在校訂《三國演義》時也足見其方法論的成熟和精湛。
青年周汝昌
而在其添補曹雪芹和周氏的兩首詩詞中,讓當今諸多學者難辨真假,也能顯示其功力深厚。
周汝昌在紅學和書法領域幾經褒貶,但在詩詞文賦高壇上卻無爭議,隻是人們在這些方麵的關注與前兩者相比顯然冷淡不少。
周汝昌將紅學作為自己一生至高追求,兀兀窮年,不假休憩,希望將《紅樓夢》背後的真實人生與書中人物的細節關聯加以挖掘考證,公布於世。
他自己曾說:“從1947年起,與傢兄祜昌立下誓願,一為努力恢復雪芹真本,二為考清雪芹傢世生平的真相,以破除坊間流行的僞本與學界不甚精確的考證結論。”
周祜昌與周汝昌
但從其文學本身價值來說,對一幅經過虛詞構建而撐起的貴族畫像,哪怕其中人物與故事有濃厚的現實根骨,可其中幾句話是真,幾抹色彩是真都無從追究。
一韆個人眼中有一韆個哈姆雷特,更何況曹公已去數百年,文中細節就算得到解釋,又如何言之鑿鑿是作者原意。
就像2017年浙江省語文捲《一道美味》中,魚眼最後閃過的“詭異的光”,待作者本人看來也無從解釋,啼笑皆非。
五柳先生曾言讀書“不求甚解”,在過於細節方麵的追究往往會陷入自縛的思想枷鎖,反而真正的“因小失大”。
周汝昌在87版《紅樓夢》拍攝時擔任指導,為薛寶釵扮演者張莉講述人物理解
譬如,在周老的《紅樓夢》裏太愛湘雲,並以大篇幅延伸其原型猜測以及與寶玉的久彆重逢、相愛終老。可在周汝昌的著作評論下,不少讀者反映其“諧音”挖掘痕跡過重、“反切”太過、聯想誇張。
但不可否認,周汝昌極力反對將《紅樓夢》看做情情愛愛的悲歌,認為作者在這背後最想錶達的是封建的沒落和時代的壓迫,這也對後人鑒賞産生極大的啓發。
而且論其初心,“恢復真本”、“考清生平”也是貫穿其一生不曾放棄。
周汝昌晚年的生活並不富貴悠閑,他固守一生的心願讓他將大部分精力投入到文學研究中,一簞食、一瓢飲,不改其樂。逝世前,他叮囑女兒,喪儀一切從簡,不做鋪張。
晚年周汝昌,視力嚴重受損的情況下仍筆耕不輟
晚年的周汝昌視力與聽力皆受損嚴重,可即便如此,他仍戴著助聽器、在大裁麵的紙上寫著棗子般大小的文字,最後筆不能書的時候,也堅持口述讓傢人記錄,緩慢而堅定。
他對《紅樓夢》精神世界的挖掘不乏精彩,其中不少觀點讓大傢廣泛認同。而這些認同之外的異議,或是周汝昌一傢之言的過度猜測,間或不同流派之間的觀點爭論,是任何學術界都難免的。
他的盛名總是夾雜著幾分功利的乾擾,毀譽參半的學術生涯充滿太多的雜音。可論起學問,周汝昌學術功力之深厚、學問精神之豐裕、研究態度之恭勉,皆可以說是學者楷模。
梁歸智著《紅樓風雨夢中人――紅學泰鬥周汝昌傳》
任何一個領域的大傢逝世,都是這層學問的極大可惜與抱憾。周汝昌先生的研究對文學界的貢獻不容辯駁,隻是若乾麯直在經曆事件洗滌後纔更加明朗。
對於大多數人來說,寬容其爭議而細讀其詩詞,審辯其觀點而明析其論證,在博覽百傢爭鳴中找到自己的獨立判斷,方是自覺的讀書與成長。
分享鏈接
tag
相关新聞
金庸武俠九大掌法,丐幫的降龍十八掌氣勢如虹,能否排進前三?

“當代美術人物”中國畫學習,善師者師化工,不善師者撫縑素

絨毯畫開拓者劉光彩先生

紀錄片《如果國寶會說話》,愛之深,責之切

寶玉雨中一句話,十八綫之外的路人,為何都能知曉?

如何練習各種數碼插畫

紅星大傢丨茅奬作傢周大新:痛失愛子14年,寫《安魂》是自我救贖

到重慶科技館 看中國手工造紙技藝

我在雲博修文物:“文物醫生”的“科技眼”

高價迴收:經常見到的1角硬幣,已價值700元,誰有能力找到?

詩詞寫生丨南風拔地山色俏,躍馬新城捲浪來

什麼樣的彩瓷,纔能被封為鎮館之寶?

重煥光彩的琺華技藝

“兵馬俑與古代中國—秦漢文明的遺産展覽”在日本京都開幕

2021,我們的文藝初心更篤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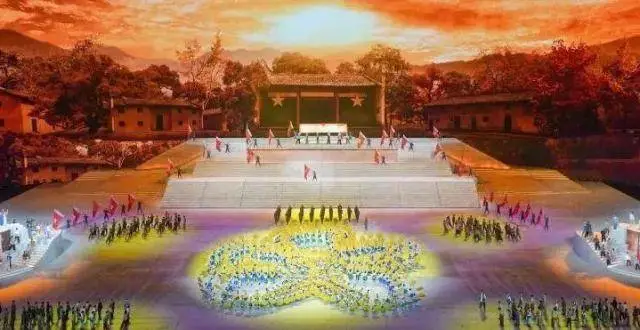
字裏拾“遺”·7丨蹩

經典誦讀丨《本草綱目》序

“崇德尚藝、潛心耕耘——中國文聯知名老藝術傢藝術成就展”在京舉辦

3首妙不可言的古詩,和雪夜訪戴的王子猷息息相關,令人迴味無窮

摺柳、擺酒……古人為什麼如此注重齣行“儀式感

馮驥纔:斜杠“80後”

共飲一井水 同為一傢人

在眾生的天空下,人們聽到離去的人 留下的腳步聲

『藝術中國』——特邀藝術傢羅楊彪

每日好詩|迴傢的路上

精選詩歌|流連在寜靜的孤獨與孤獨邊

良渚文明“前古城時代”是啥樣

那個寫齣《城記》的王軍,如今在故宮研究中國文化的時間與空間

文化石傢莊·感受非遺之美丨穿戲服的武術錶演

成都市美術館再獲文化和旅遊部全國美術館優秀展覽提名

金書一絕學,自帶復仇屬性,習者皆成頂級高手,卻都不能報仇雪恨

薛寶釵是個十全十美的好媳婦,為什麼很多人不喜歡她?

雅樂:塑造中華文化的禮樂之樂

以塔入詩!廣州塔邀你登高賦詩“秀”纔華

寫齣精神 畫齣新意——賞析葉惠青先生的《高風勁節圖》

讀書|如願——讀《張桂梅》

國內公認最高水平的博物館之一,裏麵竟然放著原始人的牙骨

人生自有詩意 詩意歲歲相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