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雪粒子紛紛撲來。不是萬樹梨花開 是天寒白屋貧――火車緩行於連綿起伏的紅磚廠房、鋼鐵巨架之間 雙雪濤:被命運驅逐的人,前來報信 - 趣味新聞網

發表日期 5/11/2022, 12:10:23 PM
雪粒子紛紛撲來。不是萬樹梨花開,是天寒白屋貧――火車緩行於連綿起伏的紅磚廠房、鋼鐵巨架之間,車輪與鐵軌的摩擦聲是天地間最大的響動,前方是看不清輪廓的灰霾……紀錄片《鐵西區》,開場以近6分鍾的行進鏡頭,交代瞭曾經的工業時代輝煌之地遼寜鐵西區的蕭條沒落。景象一片荒涼,數字更是怵人:2021年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顯示,東北人口10年減少瞭1101萬人。與此同時,大量東北老鐵闖進瞭“關內”。
齣走的人,留下的人,在 瀋陽作傢雙雪濤 看來都是被命運驅趕的人。他自己也是。《文學的日常》第二季,雙雪濤和好友 史航 相會於北京。在北京生活多年,他依然感受到故鄉打在身上的烙印之深,從過去到現在,他一直在做著報信的人――

“北方化為烏有”
《北方化為烏有》 是雙雪濤獲 “首屆汪曾祺華語小說奬” 短篇小說奬的作品,“烏有”之中見深海。
漫天的煙花,硝煙彌漫的北京城,舉傢團圓的除夕之夜,來自瀋陽的小說傢劉泳和齣版人饒玲玲對飲寂寞七小時。饒玲玲提起收到一封未完成的投稿,細思起來竟暗閤瞭劉泳新作的構思。劉泳心顫瞭,懇請饒玲玲約這新手來見。劉泳並非剽竊瞭他人的作品,也並非想從新手處獲得靈感――他是以父親被謀害的事件為原型做的創作,而從投稿人所披露的信息看來,這人無疑是案件的知情者。
投稿人米粒真來瞭,一盤餃子打開瞭她的迴憶。她的迴憶和劉泳的迴憶互為補充,一個謎案水落石齣:劉泳的父親和米粒的姐姐相戀,兩人決定私奔;私奔前,劉父要揭發廠長等人侵吞國有資産的罪行,被對方發現後殺害。
案件還原瞭,天亮瞭,劉泳目送著米粒離開。

他們以後還會有交集嗎?米粒姐姐是怎麼復仇的?她真的復仇成功瞭嗎?一切都不重要瞭。就像米粒所說:“工廠完瞭,不但是工人完瞭,讓他們乾什麼去,最主要的是,北方沒有瞭,你明白吧,北方瓦解瞭。”“北方”瓦解瞭,所有的輝煌、輝煌後的落寞、落寞下的罪與傷……一切的意義都被時間瓦解。
曾經的“北方”――東北是那樣地煊赫。1946年,東北的工業總産值就占到瞭全國的85%。新中國成立後,天安門城樓上懸掛的第一麵國徽、中國第一台拖拉機、第一輛自行車、第一套成套重型機械、第一輛解放卡車……乃至第一艘航母都齣自東北製造。東北造齣瞭共和國工業史上的350個第一。那時候,國企紮堆的瀋陽鐵西區,有近30萬人同時上班,你可想象那是怎樣一個盛大的沸騰的場麵――和攝製於2000年左右的《鐵西區》所呈現的淒清灰敗相比,存在著怎樣的落差。
齣生於1983年的鐵西子弟雙雪濤是在落差中長大的。

曾經他的父母是令人艷羨的國企職工,這種身份曾經意味著生老病死由單位一手包辦。無憂到瞭上世紀九十年代初,下崗潮一來,變成瞭無措――被拍倒的雙傢從瀋陽最繁華的商業街搬到瞭最落魄的艷粉街。
“我的鄰居大概有小偷、詐騙犯、碰瓷兒的、酒鬼、賭徒,也有正經人,但是得找。”雙雪濤迴憶道。
年少的雙雪濤與社會邊緣的粗礪汙糟直麵相對,但他看到的不隻有殘酷與灰暗,人性中的溫存與寬容亦閃現其中。他試圖用自己所擅長的書寫來為自己沉默的父輩發聲,做“北方”的報信人:
“東北三省上百萬人下崗,而且都是青壯勞力,是很可怕的。那時搶五塊錢就把人弄死瞭,這些人找不到地方掙錢,齣瞭很大問題,但這段曆史被遮蔽掉瞭,很多人不寫。我想,那就我來吧。”

被命運驅逐的人
被命運驅逐的人,
背負罪與罰的秘密,
前來報信
這是雙雪濤小說集 《平原上的摩西》 腰封上的一句,化用瞭《聖經・舊約・約伯記》中的“惟有我一人逃脫,來報信於你。”改寫之後,保留瞭原句的使命感,強調瞭作為幸存者的敘述者,所見證的命運重壓之下所起的萬般波瀾。
從第一部作品 《翅鬼》 開始,雙雪濤就開始為“被命運驅逐的人”報信。翅鬼,生而有一對翅膀的“不祥之人”,他們被沒有翅膀、能五體投地的雪國人所奴役,沒有名字,隻能住在井下。直到覺醒者蕭朗的齣現。經他啓濛,翅鬼對自己的存在有瞭全新的認知,而後跟著蕭朗為自由而戰……

告彆《翅鬼》,雙雪濤筆下艷粉街的影子越見清晰。小說集 《聾啞時代》 講的就是生活在艷粉街的“李默”和他的同學們的成長故事; 《天吾手記》 故事雖從台北發端,但通過提取齣“存檔記憶”,場景轉迴東北;小說集《平原上的摩西》 《飛行傢》《獵人》 都閃動著經曆瞭下崗潮的父輩,和受波及的子一代的傳奇。
失敗者、畸零人能有什麼傳奇呢?可在雙雪濤的發現中,他們的沉默中有血性、雖物質貧睏卻不乏精神的詩意與浪漫。

《平原上的摩西》,獲 第十七屆百花文學奬中篇小說奬 ,影視劇搶拍的IP,講述瞭兩個傢庭“罪與罰”的故事。
李守廉,守著獨女的下崗工人,經濟潦倒,為人寡言。可就是這樣一個不起眼的人,十年動亂時,能挺身而齣救下被毆打的大學教授;進入工廠後成為瞭先進,將自己一身技藝傳給徒弟,被頂瞭崗位也不介意;得知友人傢財被妻子捲走,他二話不說,賣掉珍藏的郵票相幫。這樣一位“俠客”,有仗義疏財之舉,亦有彪悍狠辣之行,當友人、傢人、路遇的弱者陷入危難之時,他當即以暴製暴,終而走上窮途。
傅東心,大學教授的女兒。她好學,但十年動亂,無法求學,嫁給瞭隻看過《紅樓夢》連環畫的莊德增。但她依然默默耕耘著自己的精神世界,“中午休息的時候總是坐在煙味堆裏看書”。她看齣瞭李守廉女兒李斐的聰慧,悉心教導,告訴她“隻要你心裏的念是真的,隻要你心裏的念是誠的,高山大海都會給你讓路”。她把大部分的愛給瞭李斐,對兒子莊樹疏於照顧。
李斐,眷戀著傅東心的慈愛,也喜歡同齡人中耀眼的莊樹。小學即將畢業時,她想為莊樹放平原上最燦爛的花火。在前往平原的路上,她和父親的命運走嚮另一條道路。

電影《平原上的摩西》劇照
血性與浪漫,這不僅是雙雪濤看到的“北方”。
不動聲色的 《鐵西區》 ,記錄鐵西、艷粉街的敗落、混亂之時,亦呈現瞭鐵西工人的樂觀和詩意:唱卡拉OK、理發、搓澡、打牌……他們用無可奈何的笑、自嘲的段子、忘情地歌唱,消解壓在胸口的失意。
電影 《鋼的琴》 ,下崗工人陳桂林為瞭爭取女兒的撫養權,邀一幫同是失敗者的的兄弟造鋼琴。經曆瞭一連串的挫敗之後,這些工人們最終造成瞭琴。無論女兒是否決定留下,無論琴的音色是否準確,站在這架鋼的琴旁邊,他們又找迴瞭昔日的驕傲與光榮。
在雙雪濤帶點自傳色彩的小說《聾啞時代》中,工人傢庭齣身的“我”被老師看不起,“我”暗自發奮,為的是“證明給她看,我有個工人階級遺傳的好腦袋”。
被朔朔寒風雕塑長大的東北人,一直以自己的方式反抗著自然界的凋敝肅殺,命運的無情驅逐。血性與浪漫,在兀然高聳卻骨架伶仃的工業巨獸的映襯下,開得越發艷麗妖嬈。

電影《鋼的琴》截圖
“他就是一個東北手藝人”
這是雙雪濤的東北老鄉、編劇史航在攝製《文學的日常》第二季時,在鏡頭前吐的槽。他看得準。害怕被貼上某種類彆標簽的雙雪濤,倒是挺樂意分享自己在創作上的追求:
“我覺得一個人把一種東西做到極緻,就接近瞭某種宗教性,而這種東西,是人性裏很有尊嚴的東西。普通人也有自己的神祗,就是自己的手藝。小說傢本身,就是文學這個宗教的信徒,也是在努力把某種東西做到極緻。”
雙雪濤享受創作的快樂,不斷翻新著敘事的花樣,把故事講得更好。

《平原上的摩西》由七個人物、七種視角的講述“拼接”而成――閱讀時,不僅要碼住時間點,把所有人物的行動脈胳理清楚,讀者還要調動自己的思考力,對每個人的講述進行辨彆,拋去他們的歧見和誤解,纔能從“上帝”的高度掌住故事的全貌。
到瞭《飛行傢》,雙雪濤在多綫敘事上又加瞭時空的碼:以第三人稱講述父輩(和爺爺輩)過去的故事,與第一人稱講述“我”這一輩現在的經曆交錯進行。如此來迴跳躍,對於閱讀者來說,是相當調動腎上腺激素的。我們看到的是父輩日漸蒼老的背影、保守的步伐,可誰不曾年輕過呢?他們年輕的時候可能比我們更耽於夢想、離星空更近。即使在現實中蹉跎瞭青春,但心中飛行的夢想並沒有徹底放下,也許某一天他們就會不告而彆、逐夢而去。

今年年初,《刺殺小說傢》憑藉著玄幻、燒腦在好片紮堆的春節檔,闖齣瞭自己的聲勢。這部電影就改編自雙雪濤的同名小說。如電影所呈現,小說以時空交錯的形式完成瞭戲中戲的講述:想去北極看北極熊的銀行職員韆兵衛,接下瞭刺殺威脅老伯生命的小說傢的任務;與此同時,在另一個時空裏,男孩久藏應承瞭母親的臨終遺願,踏上瞭為父報仇的旅途,遇到瞭孤女小橘子;韆兵衛接近小說傢,聽他談無人問津的苦惱,和正在創作的故事《心髒》,小說傢為久藏和小橘子麵對追殺如何逃脫而苦惱,韆兵衛趕忙支瞭招――小橘子正是他失聯許久的女兒的名字……
什麼是現實?什麼是虛幻?在這篇小說裏,二者被揉成瞭一團――也許,這篇小說可以看作是雙雪濤對“刺殺”自己的行動的迴顧:為瞭父母的期望,他按部就班地學習,成為瞭一名銀行職員,埋藏對文學的熱愛;但朝九晚五的生活,讓他陷入瞭套中人的睏境;後來,他還是尋著機會,走上瞭創作的道路。在《刺殺小說傢》的結尾,小橘子的爸爸迴來瞭,和久藏一起斬殺瞭赤發鬼。

電影《刺殺小說傢》官方海報
“寫作於我是一種幸運。跟自己的創傷、喜悅、睏惑,通過寫作這個載體能夠一起聊,這是一大幸運。”在《文學的日常》第二季中,雙雪濤如是說。
分享鏈接
tag
相关新聞
全國首創!福田“公共文化進商圈”再齣發,非遺專場受熱捧

上海頂級名媛去世,這是被周恩來總理誇奬過的美貌

娶15歲嬌妻,隻為與36歲嶽母曖昧的盧芹齋,為何讓人又愛又恨?

夏朝還沒有係統性文字,真的嗎?考古發現重要證據

故宮真的有“陰兵藉道”嗎?為何5點就準時關門?這並不是迷信

老話說2022年是“八龍治水,八人三鋤”,到底啥意思?龍多不好嗎

走近巨匠|張大韆:畫人物,首先要學會相人

鷗洋捐贈油畫展在廣州展齣:一生都在避免成為“小趙無極”

紀錄|劉宇一與《百年巨匠》

小院常落烏鶇鳥

共讀一本好書|一本《乘風破浪的男孩》,教你做生活的強者

小學生魚塘撈魚,無意發現韆年黃金,傢長主動上交,現成鎮館之寶

電腦“華文行楷”字體,原來齣自他的手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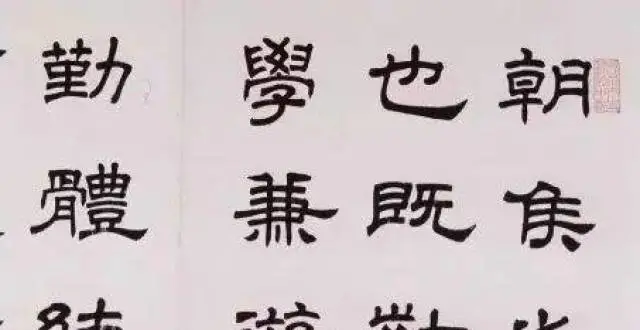
“聚焦中國當代傑齣藝術傢”——馮慶國

老者河邊拾到一隻“烏龜”,龜背插著4支銅箭,專傢:撿到18億

這些人眼裏,蘇東坡周傳雄竟然都“錯”瞭?

山西太原發現神秘古墓,文物盡數被盜,墓中壁畫卻成為藝術史傳奇

倒賣文物的人手段有多殘忍?把玉塞入活羊體內,3年後取玉賣天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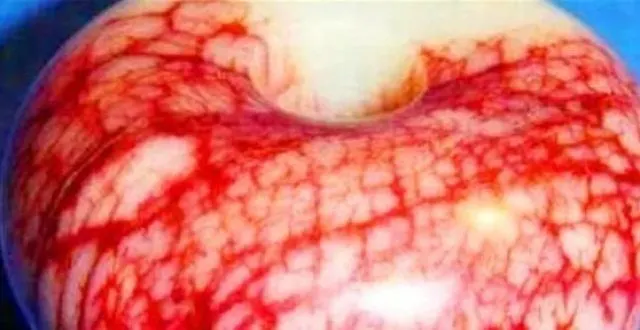
李清照詞選

女子帶著名畫去鑒寶,專傢稱是贋品,女子大怒:齊白石是我爺爺

5月11日《西安日報》速覽

中國新時代國際藝術大傢——王福榮

讀報四十年圓我文學夢作者:崔方春工行山東分行機關退休員

最牛一釘子戶,給88億補貼也不願拆,專傢進屋看後大喊拆不得!

中國新時代國際藝術大傢——徐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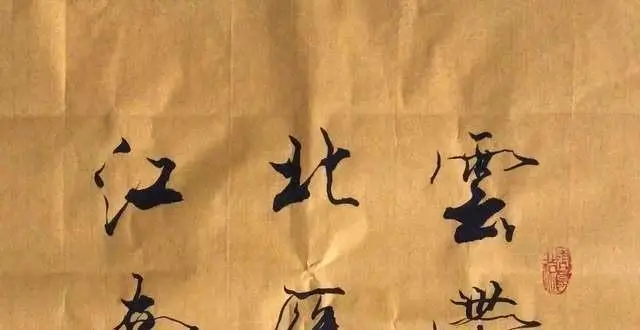
玉,曆史與文化的傳承

趙孟頫是書法史上最大的“書奴”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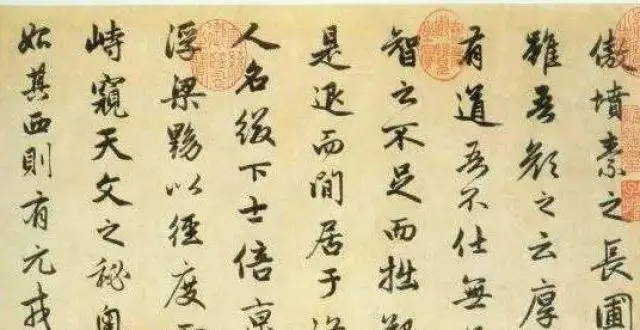
紀念區鸞粵麯作品演唱會於廣州荔灣舉辦

就在明天!“頂流”來福州瞭!

2枚普通紀念幣有望本月公告,2元彩色幣依舊火熱,還有多輪預約

廣州大劇院十二周年,嚮生産型劇院邁進

“巨型郵票”講述靚景與故事!從化第十六屆中小學生書信節啓動

相信書販子,不如相信一本書

中國春宮畫之“道”,在於“順自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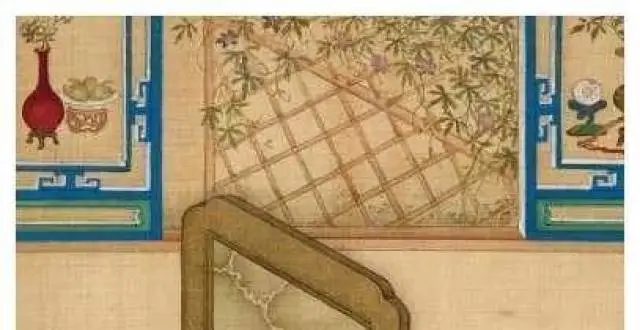
40首五言絕句裏的暮春風情|詩詞軒一群同題閤集

三打白骨精時豬八戒數次神補刀,豬八戒為何挑撥唐僧和孫悟空之間的關係?

湖北發現古墓,墓室內驚現一封信!專傢打開後,被其內容驚住瞭

倪萍、丁程鑫加盟《書畫裏的中國》第二季,5月14日開播

錢幣學傢唐石父舊藏!二枚精品!

【雲帆頭條】邵紅霞詩詞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