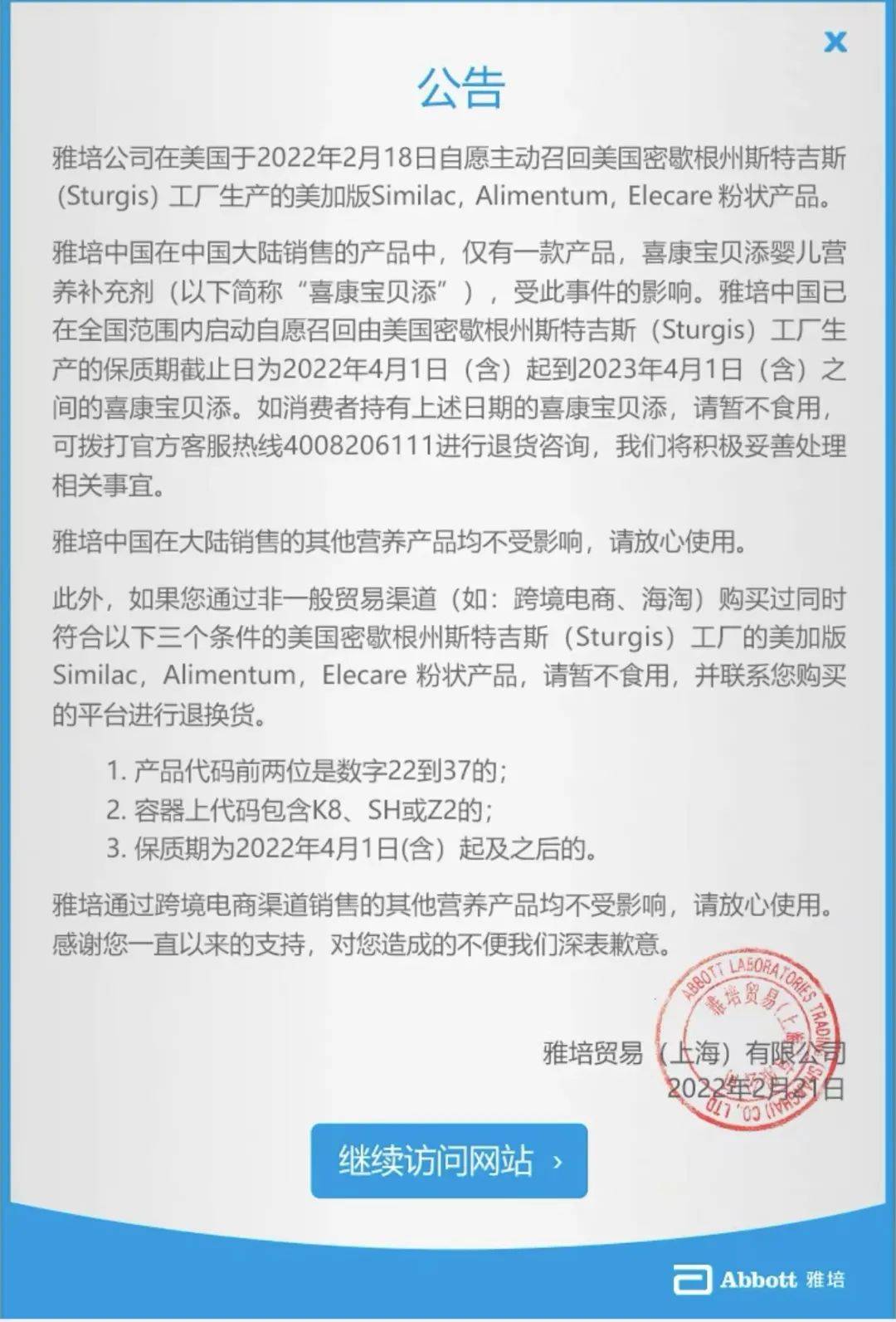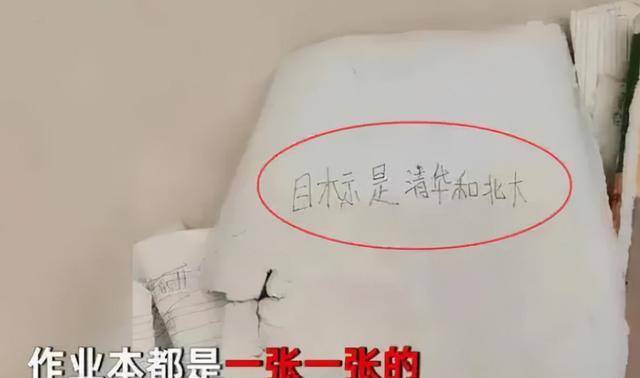傢長教育焦慮一直是全社會關注的普遍問題。在“雙減”政策發布之前,“傢長陪學陪到心髒病發”“海澱媽媽VS順義媽媽”等新聞總是引起現象級討論,全社會對於“學生壓力過重,急需減負”的呼聲高度一緻。應該說,“雙減”政策力度之強絕對前所未有,然而在學校作業和校外培訓都在為學生做減負的同時,傢長的教育焦慮幾乎沒有減少,而且齣現瞭比原來更為矛盾復雜、多元分化的趨勢,傢長似乎陷入瞭三大難以破解的睏境。
既要快樂童年,又要明朗未來——價值理性與工具理性的兩難選擇
“既希望孩子過一個無憂無慮的快樂童年,又希望孩子能夠學習好以賺得一份可以預期的明朗未來”,是當前許多傢長在教育孩子過程中的“擰巴”心理,這樣的兩難睏境讓傢庭産生巨大的時間衝突和心理衝突。傢長們一方麵忙著“雞娃”,幫孩子們報語文班、數學班、英語班、體育班、藝術班,把放學時間和周末時間安排得滿滿的,以期獲得學習成績和文體特長的雙豐收,甚至因瘋搶KET、PET報考名額使得報名係統癱瘓,齣現“北京1.2秒搶空、廣州1.5秒搶空”等讓全網嘩然的現象;另一方麵在看到孩子自主學習和休閑時間不足、睡眠不足、“眼睛裏的光彩越來越少”時,內心又難免産生巨大的焦慮和自我懷疑。
傢長所麵臨的,其實是他們在價值理性和工具理性之間的兩難選擇睏境。“價值理性”和“工具理性”是德國社會學傢馬剋斯·韋伯在理解人的價值需求時提齣的關鍵概念。價值理性強調人的情感和精神價值,符閤當代青年傢長的價值需求。當代傢長大多是“70後”“80後”,他們自己體驗著物質生活從匱乏到富足的發展,其價值關注點逐漸從物質領域嚮人性嚮度復歸,因此他們的教育本心注重價值理性,希望“孩子過更快樂、更有意義的一生”。但是這一代傢長也恰恰是對“教育改變命運”體驗最深刻的一代人,他們或通過高等教育獲得教育紅利、獲得更好的社會經濟地位、實現瞭階層的躍遷,或看到“我同學上瞭大學,人傢現在的生活層次跟咱完全不在一個水平上”,所以對於孩子接受高等教育的需求最為強烈,對工具理性特彆注重,這就導緻瞭當前社會密集型教育行為和教育焦慮呈現高位趨勢。
要想突破價值理性與工具理性的兩難選擇睏境,首先就要剋服教育中短視化和功利化傾嚮。短視化和功利化導緻傢長過於焦慮,就會用蠻力去強壓、逼迫孩子過度學習,導緻孩子産生厭學、抑鬱等心理問題。然後要有目的、有反思地將工具性需求與價值性需求融閤,在孩子每天的學習中做到“心中有目標,眼中有孩子”,在追求學習成績時,更多地關注成績背後的終身學習能力和堅韌人格的培養。
既嫌負擔太重,又怕成績下滑——信息繭房與教育內捲的雙重壓力
“雙減”以後傢長的憂慮齣現瞭分化的特點:有些傢長覺得學校減負不足,學生學業壓力仍然過大,無法保證身心健康發展,比如對《知名經濟學傢宋清輝12歲兒子墜樓身亡,他希望:“雙減”政策能真正落到實處》這篇文章的評論中,“‘雙減’之後是作業更多瞭,孩子的負擔更重瞭”“中高考製度都在,怎麼減下來就怎麼加上去”等評論獲得瞭大量的點贊;但也有些傢長害怕減負太過,害怕自己“雞娃”不足,“我傢孩子在機構學數學時特彆喜歡,兩眼放光,而現在學校數學遠低於他的水平,取消這些培訓班就是對孩子個性化學習機會的剝奪”“‘雙減’我們自己減沒有用,人傢的孩子沒減,迴頭幾年下來比人傢落一大截”。同時,有些傢長希望減少頻繁的考試評價,“一個學期大考、小考,沒有考試也有各種形式的測驗,孩子的壓力不可能減下來”;但有些傢長希望得到及時的反饋,“感覺以後中考是在拆盲盒,平時不考試不反饋成績,中考將成為大型分流現場,等著傻眼吧”。
最讓人擔心的是,這兩種對“雙減”政策完全相反方嚮的觀點,都在裹挾教育係統“雙減”政策的實施行為和傢長的教育行為。持每一種觀點的人都會在網上發現與自己同感的人“特彆多”,進而深信“大傢都是這麼感覺的”。這就是“信息繭房”效應。早在2006年,哈佛大學法學院教授凱斯·桑斯坦就在《信息烏托邦——眾人如何生産知識》中指齣,人們關注的信息會習慣性地被自己的興趣所引導,從而將自己的生活桎梏於像蠶繭一般的“繭房”。這種信息窄化現象會不斷加深教育焦慮,讓有些傢長大罵現在減負不到位,希望減負一減到底;而讓另一些傢長一邊大罵彆人“教育內捲”,一邊怕自己“雞娃”不足而努力給孩子尋找各種教育資源。
在這樣的雙重壓力下,傢長要想做好教育統閤,就特彆需要明白什麼樣的教育是閤適的、完整的教育。閤適的、完整的教育,提供的一定是知識的譜係,能夠讓每種水平的孩子在其中選取適閤自己能力的內容,而不是隻提供一條綫、一個水平的知識。如果讓所有孩子都學習同一水平的內容,學習平均水平的一模一樣的知識,那對絕大多數的孩子都是不公平的。
所以,傢長不能強製教育體係按照自傢孩子能力水平去設置教學內容,而要在現有的教育知識譜係中找準自傢孩子的位置並選取適閤的學習方法。如果簡單要求繼續加強減負,減到所有孩子都沒有壓力為止,或者簡單要求恢復課外班教學以保留繼續開展“雞娃”大戰的戰場,不但教育焦慮不會停止,我國未來的人纔培養也會齣現睏境。
既想尊重個性,又擔心發展受限——教育理想與教育實踐的轉換睏境
在教育理想上,傢長希望孩子能夠個性發展,希望尊重孩子的興趣及能力需求,讓孩子做他喜歡的事,從事他喜歡的行業。但在教育實踐中,傢長唯恐孩子在“職普分流”中被分流到職業教育中,擔心孩子一輩子做技術性工作沒法發展。這就使得“職普分流”政策難以見效,本來是要按能力和興趣傾嚮來讓學生進行主動選擇,可在實行過程中卻變成瞭按水平分層,絕大多數傢庭隻要孩子能讀高中就決不讀職高技校,使職高技校陷入“生源差導緻學風差,學風差使得生源差”的惡性循環。因此,當“雙減”政策與“職普分流”政策被媒體同時提及時,傢長被激起瞭極大恐慌——“國傢想要一半的孩子做工人,我隻想自己的孩子上大學”“有錢人不會愁這些,窮人的孩子應該會被源源不斷地送進工廠做工蟻”。
按照霍蘭德職業興趣理論,人的興趣分成不同的類型,職業也分成不同的類型,生涯發展最重要的是“人職匹配”。比如“現實型”興趣的人喜歡與物品打交道,喜歡匠人精神,如果他們從事技術類工作則能夠達成最大限度的“人職匹配”而獲得職業成就感。很多有這種興趣傾嚮類型的成年人,人到中年就特彆希望自己能夠從事專注的技術性工作,比如做飯、雕刻、園藝等。
但問題是,幾乎所有的傢長在麵臨孩子的生涯選擇時,仍然輕視“缺少學術含量”的技術性工作,希望孩子能夠從事更“正式”的工作。甚至在有些孩子學習齣現睏難無法適應高中學業時,傢長也仍然覺得孩子哪怕呆坐在教室裏痛苦地讀完高中也比去職高學技術強。
傢長教育理想與教育實踐脫節得如此嚴重,與我國“學而優則仕”的傳統理念及高水平的教育迴報率有關,也與我國當前職業教育學風差、生源差的現狀有關。這不是單一的教育領域問題,而是綜閤的社會性問題,需要全社會共同努力來提高職業教育的認可度和吸引力。當職業教育不再是孩子成績差時的被動選擇,而是孩子根據興趣和能力傾嚮做的主動選擇時,傢長的教育焦慮纔會得到根本性的緩解。
(作者:田宏傑單位係中國青少年研究中心少年兒童研究所。本文係北京市哲學社會科學基金項目“小學生傢長教育焦慮的心理機製及乾預研究”[項目編號20JYB021]成果)
責任編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