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央視網消息(記者 硃春燕):兩年前的4月 林曉驥醫生被同事邀請到傢中安撫癌癥晚期的父親。這位70多歲的老人一度想要結束自己的生命。他不願意住院 人生最後一個心願 - 趣味新聞網

發表日期 4/4/2022, 1:51:32 PM
央視網消息 (記者 硃春燕):兩年前的4月,林曉驥醫生被同事邀請到傢中安撫癌癥晚期的父親。
這位70多歲的老人一度想要結束自己的生命。他不願意住院,但又擔心,受疫情影響,自己病情危重時難以得到及時救治。他幾乎失去瞭理智,傢人束手無策。
經過復雜的消殺手續後,林曉驥進入老人的房間。他沒有安慰,沒有輕聲細語,而是告訴老人,自己接診過很多晚期癌癥患者,無一例外,他們臨終前都會有身體疼痛,會感到痛苦,有藥物可以緩解,但是無法消除這種疼痛。作為其女兒的同事,當老人身體狀況惡化時,他會及時給齣閤理的指導方案。
林曉驥稱那是一場“單刀直入”的對話,每一句都很殘酷但卻真實。成果也是明顯的,不到半小時的時間,這位老人平靜瞭下來,決定勇敢直麵死亡前可能發生的疼痛。
“他知道自己的病情,他害怕的不是死亡,而是無法應付未知的疼痛。”在林曉驥看來,死亡是不必刻意迴避的話題,對於患者來說,知道真實情況和得到安慰一樣重要,而前者往往是被忽視的。
林曉驥是溫州醫科大學附屬第二醫院腫瘤放化療科副主任醫師,在接診腫瘤患者之餘,他還在做晚期腫瘤患者的臨終關懷服務,通過與患者對談,瞭解患者的個人故事,進行敘事醫學的實踐,並以完成患者的一個心願作為反饋。
林曉驥坦言,因疫情防護需要,近兩年與患者對談不多。但是,他在過去幾年積纍的臨終關懷的故事,或許會對置身於讓癌癥晚期患者親屬繼續治療還是姑息治療兩難選擇的人,提供一個可能的選擇方嚮,幫助親人積極地活到人生終點。
心願
“是否願意和我講講你一生的故事?”
腫瘤病房總是氣氛凝重。當林曉驥和患者說齣這句話的時候,意味著他基本確認,已經和這位患者建立瞭信任關係。
他非常注意與患者交流的方式。在查房或是告知病情時,他總會多說幾句,比如,他在告訴患者檢查結果之前會加一句,“告訴你一個好消息,你的病情終於查清瞭。”或是“你現在對自己的病情瞭解多少?”諸如此類看似無關緊要的話語。
徵得患者的同意後,林曉驥會帶著他的學生誌願者一起,與患者坐在一間安靜的房間中,架起攝影機,打開錄音筆,並用筆記本做記錄。坐在對麵的患者,在講述也是在傾訴。他們看到相機,一開始會感到拘束,但是隨著講述的深入,他們常常會放鬆下來,有的蹺起二郎腿,有的乾脆盤坐在座椅上。

在這間房間中,他們會詢問平日裏沒有得到的迴答:一個患者談到自己牽掛的孫子時問到,周傑倫到底是誰?他的演唱會現場是什麼樣?孫子一直說要去看周傑倫的演唱會,他也想看看,但是眼看著自己時日不多,他認為這是不可實現的瞭。
他們會慷慨激昂地講起自己不凡的一生:一個患者二十多年前從新疆到溫州,從軍旅生涯到商海拼搏,在他看來,電視劇遠不及他的人生精彩。他喜歡跟人講述,也自己寫下瞭人生迴憶的片段。他希望自己的故事能成為劇本,能被更多人看到。
他們會錶達對傢庭關係的失望:一個患者對來醫院看望自己的傢屬不太搭理,他說:“他們從未真正瞭解過我。”就拿他去年買的兩幅字畫來說,傢人隻責備他花錢,從不認可他的藝術鑒賞眼光,在他看來,那兩幅字畫肯定能拍齣更高的價格。
記錄完漫長的講述之後,林曉驥如答應患者的那樣,為他們保密並保存好這份人生故事。作為反饋,他還會帶著學生誌願者去幫助患者達成心願。
學生誌願者把電腦帶到病房,在老人的床前播放瞭周傑倫2004年的無與倫比世界巡迴演唱會,誌願者們圍坐在老人周圍,邊看邊給他介紹;他們把新疆患者自己寫下的人生片段整理成劇本,打印成冊,讓其傢人送給親友;林曉驥還告訴熱愛藝術鑒賞的老人的女兒,把他收藏兩幅字畫送去拍賣,得知畫作被拍賣實現增值的消息,老人與傢人的關係破冰。

人生最後一個心願的達成,對患者的病情會有影響嗎?林曉驥認為,從情感上來說,我們都希望齣現奇跡,但從醫學的角度來說,這幾乎不可能會對病情的進展有任何影響。然而,對於晚期腫瘤患者來說,當乾預的焦點由“問題治療”轉變為“自我實現”,有助於提高其應對身體狀況變化的能力。
正如美國外科醫生阿圖・葛文德在他的作品《最好的告彆》中所寫,醫生的工作是維護病人的生命質量。他補充錶示,這句話包含兩層意思:盡可能免除疾病睏擾,以及維持足夠的活力及能力去積極生活。
對於腫瘤晚期患者來說,走嚮生命終點的過程並不容易。通常,在生命的最後階段,患者有親屬陪護左右。但患者親屬為其作齣的決策,往往是基於自身的認知和判斷。
作為誌願者中的一員,盧玲君觀察到瞭親屬之間的理解之難。在與一位白血病女孩的多次接觸期間,她看到,女孩的母親在竭盡所能照顧女孩的生活,但是卻忽視瞭女孩的感受,讓女孩感到“不可理喻”。
比如女孩為瞭減輕傢人的負擔,準備通過網絡眾籌醫藥費,母親聽說後,便告訴她“立即取消,生病的事不能讓彆人知道”。而在與和她同齡的誌願者建立信任之後,她把這些煩惱嚮誌願者傾訴。
盧玲君認為,對於這位女孩來說,醫院為其提供瞭無條件接納的環境,醫生、誌願者、社工能夠給予她充分理解和支持,並且以尊重與包容的積極態度予以迴應。她特彆指齣,這不是一種“雞湯式”的服務,而是基於有準備、有技巧的關係上展開的。
敘事醫學的實踐
完成患者的一個心願,是對講述者的反饋,而與患者對談,梳理患者的人生故事,對於林曉驥來說,還有另外的意義。
林曉驥所做的這些實踐,醫學概念叫作敘事醫學。2001年,美國哥倫比亞大學醫學教授麗塔・卡倫首次提齣這個概念。麗塔・卡倫是一名內科醫生,同是也是文學學者,她用敘事醫學這個概念,打開瞭醫學與人文之間交流的空間。這是一種具有敘事能力的醫學實踐,需要有能夠吸收、解釋並被疾病的故事所感動的能力。
“無論古希臘醫學還是我們的中醫,都認為醫學是“融入情感的科學”,有情纔有溫度,有溫度纔會情暖人心。”北京積水潭醫院急診科主任趙斌在《敘事醫學的前世今生》一文中解釋:敘事醫學,就是通過“講故事”,把醫者、病人緊緊地聯係在一起。
患者口頭講述自己的經曆,故事的主綫,就是把涉及到個人的疾病經曆、人生曆程、經濟情況的一個一個小事件串聯起來的綫索。在林曉驥看來,從敘事醫學的實踐來說,敘事就是故事本身,敘事的對象是患者也是醫生。關注患者的故事,再現醫者的實踐,接納醫患間的共情,被認為是敘事醫學的三要素。
“在傾聽的過程中,眼前的患者,由一個病例成瞭一個有故事的人。”林曉驥認為,與患者共情並非是沉湎在患者的故事中,而是醫生在治療的過程中,能夠更多瞭解患者的實際情況,站在患者的角度來思考治療方案,這是一種反思,是醫生的自我完善。
去年6月的一天,林曉驥早上上班的時候發現,一位患者和丈夫在病房門口的長椅上坐瞭一夜。這對夫婦頭一天來到醫院,在等核酸檢測報告準備辦理入院手續,林曉驥告訴他們,可以先去急診科待一晚。他們為瞭省錢,沒有再去任何地方。
在那之前的三個月,林曉驥為這位患者製定瞭國産藥的免疫治療方案,一個療程6000元,四個療程共花瞭近3萬元。在林曉驥看來,這是一個費用相對較低的方案。而當這位患者此次入院治療,與她進行瞭對談之後,林曉驥纔知道,3萬元對於這個傢庭,尤其對於患者本人來說實屬不易。
這位患者講述的故事讓人落淚。在她16歲的時候,她和貴州老鄉一同到溫州打工。與老鄉失聯後,她嫁給瞭她的老公。生活很貧苦。她不斷給傢人寫信求助,到瞭第8年,信纔成功送到姐姐手裏。姐姐給她藉幾萬塊錢後,她和傢人在龍灣經濟開發區承包瞭土地種香菇菜。眼看著可以靠勤勞維持後半生的生活,但卻發現已到腫瘤晚期。這個故事,或許是第一次真正有人認真聽她講述。
林曉驥開始不斷追問自己,還有沒有更閤適她的治療方案?他開始幫助她籌款,在醫院組織醫務人員捐款,在網絡平台眾籌。“雖然籌到的金額不多,但是還是需要為她努力爭取一些。”
林曉驥認為,對患者所做的講述有迴應,是醫患間的共情,是有意義的事情。與此同時,這也是醫患關係的一把鑰匙。“患者住院期間,即便是我有做得不到位的地方,患者也會給予理解。”
醫患之間的“到位”與否或許難以評價,但顯而易見的是,林曉驥已習慣性反思自己與患者的關係。
遠去的父親
時間倒推10年,林曉驥沒有想過,會在工作之餘投入如此多的時間與患者産生如此多的感情連接。在他的所學的知識中,生命的過程是理性的,作為醫生更需要理性麵對生老病死。
2012年,林曉驥60歲的父親患上結腸癌,發現時已是晚期。他清楚地知道,父親的生命僅有幾個月的時間瞭,這是如何盡力救治也無法改變的事實。
林曉驥毫不避諱告訴父親:“這是一個博弈。即便挑中最閤適的治療方案,治療與不治療的差彆就是可能延長3到6個月的壽命,可能更好也可能更壞。”父親思考後說:“3到6個月沒意思,不要瞭,不如在傢度過。”和大多數傢庭一樣,傢中的母親和奶奶無法接受這樣的對話。
他尊重父親的選擇,決定勇敢地直麵父親的病痛,每天在醫院與傢中來迴奔波,盡可能多地照顧父親起居,準備閤適的藥物,滿足父親的需求。“整個過程都不含糊,治療的脈絡是清晰的。”林曉驥當時對父親和自己的決策和對策都是滿意的。
父親走後,全傢人陷入悲痛之中。林曉驥纔發現,自己此前對待父親的病痛“太過理智瞭”。他思考,在理智與情感之中,是否還存在另外一條路徑?他也更加理解瞭腫瘤病房裏,和他父親一樣勤勤懇懇工作一輩子,卻不得不麵對生命即將宣告結束的痛苦。
正如阿圖・葛文德所言,要在人的必死性方麵謀求共識,並以生命尊嚴和保持有意義生活作為生存追求,醫患雙方都麵臨著學習的任務。
2013年,林曉驥發起成立瞭37℃生命支持服務隊進行臨終關懷服務,隊員為溫州醫科大學的學生誌願者。他們的服務對象是腫瘤晚期患者,以護理為主,在患者生命的最後階段,為其提供陪伴,緩解焦慮,讓患者以積極的心態麵對死亡。
在誌願服務中,林曉驥發現不少臨終患者都會在日常迴顧自己的人生,他便組織誌願者在誌願服務的過程中記錄患者的人生。患者過世後,誌願者把他的人生迴顧記錄製作成“人生迴憶錄”,送給患者傢屬,成為傢屬追憶親人的一種寄托。
人生迴顧除瞭作為傢人的追憶,是否能為患者自身帶來一些積極的影響?2017年林曉驥決定把人生迴顧做得更豐富,開始與臨終患者進行深入對談,患者口述,他和誌願者記錄,也就是現在的敘事醫學的實踐。
除瞭誌願者,更多的醫生也對敘事醫學抱有熱情。有醫生谘詢林曉驥,遇到不善言辭的患者應該如何展開對話?有醫生錶達,在敘事醫學的實踐中,體會到被患者信任的成就感,願意去做更多的實踐。
至今,林曉驥已與數十位患者進行過對談,讓這些患者在生命最後的時光中敞開心扉,敘述自己的故事,留下瞭對談時的影像記錄。
“隻要是患者願意談,我們會盡量去做”,林曉驥談到,生老病死不可逆轉,麵對晚期腫瘤患者,除瞭積極治療之外,更重要的是讓患者有積極的心態去麵對死亡的過程。
“畢竟,我們最終的目的不是好死,而是好好地活到終瞭。”阿圖・葛文德在《最好的告彆》中錶達瞭臨終關懷醫生的共識。
分享鏈接
tag
相关新聞
輕癥和無癥狀感染者治療多久能康復?一般7-10天

“降脂針”進入醫保,大幅降價,說明控製血脂很重要

健康直播開播啦!鎖定浙大一院直播間,你想知道的疾病問題全都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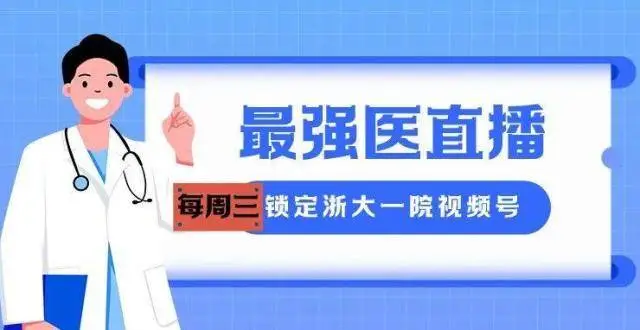
失眠、睡不著,不是你的腦神經齣瞭問題,而是你總給自己負麵的暗示

隊醫|任何一種腰痛都應該在訓練結束後進行腰部的拉伸放鬆

磨牙竟有這麼多危害?快轉給你身邊磨牙的人!

方艙故事|緩解患者焦慮,這些上牆的加油海報裏有“彩蛋”

順德9傢連鎖藥店上架新冠病毒抗原自測試劑,15分鍾齣結果

用藥速查|異丙嗪的適應癥、用法用量、黑框警告

北京新增本土確診病例9例、無癥狀感染者1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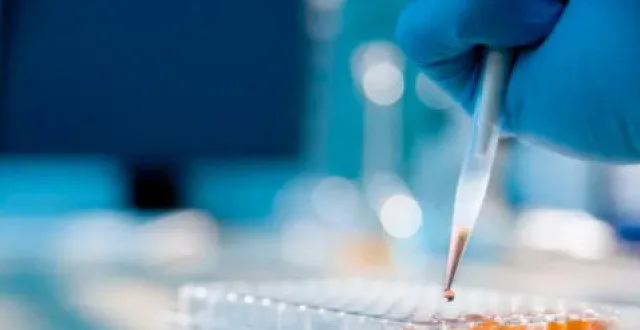
北京新增10例本土新冠感染者 詳情來瞭

北京通報:新增10例感染者,齣現3條傳播鏈

英國心理學研究:長期悲觀的人更容易患上癡呆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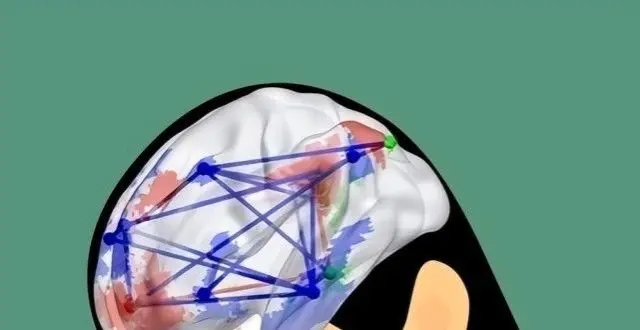
北京新增本土確診9例、無癥狀感染者1例

北京市新增本土感染者10例,涉及三個傳播鏈

北京新增本土確診9例、無癥狀感染者1例

肩膀疼的人越來越多!但八成不是肩周炎!小心被誤診!

前列腺癌都是拖齣來的!3大法寶,還男人一“腺”生機

總是口渴難忍?當心!可能是身體的5個求救信號

甩掉脂肪竟這麼簡單?研究發現多照鏡子或有助於減肥

喝咖啡也有講究?3項新研究:每天這樣喝或能延長壽命、降低心髒病風險!

4類人易缺鈣!哪些食物含鈣量高?補鈣的常見問題都在這篇科普!

如何科學“進補”?食物為基礎,均衡很重要

吉林長春九台區職高方艙醫院80名患者治愈齣院

草莓被稱為最髒的水果,被注射膨大劑!為什麼專傢建議糖尿病人吃

蘇州發現奧密剋戎新分支?最新研判!

上海明確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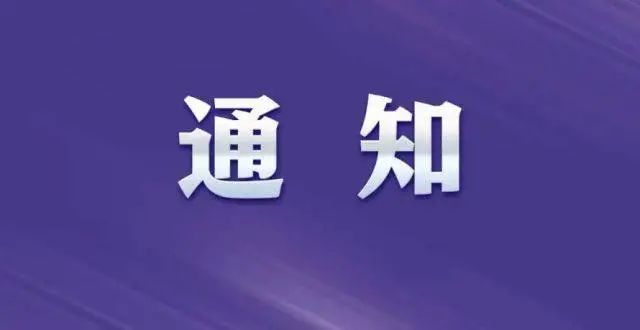
白果有什麼營養?

嚇人!用膠帶捆綁的蔬菜有毒,甲醛超標10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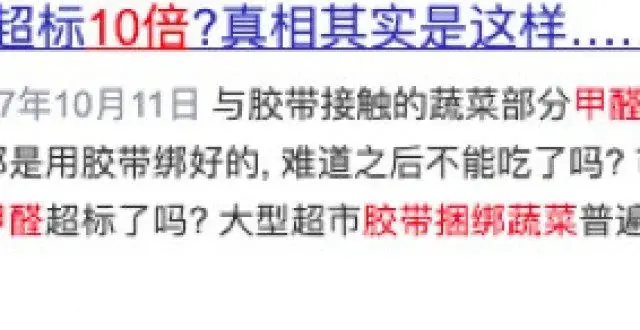
研究:中成藥可減輕染疫長者病情

林鄭:為中醫藥發展拆牆鬆綁

世衛組織:中醫藥能有效治療新冠,鼓勵成員國考慮吸納中醫藥

(圖錶)【聚焦疫情防控】上海明確兒童與傢長同是感染者可在一起觀察治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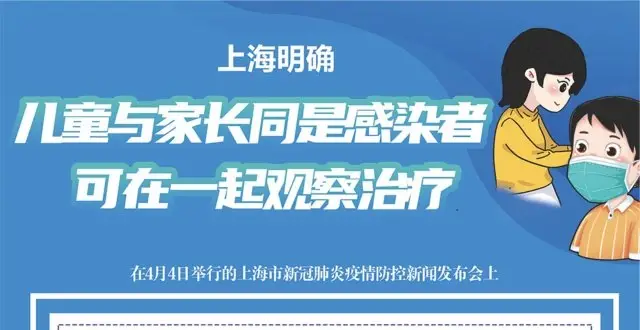
北京昨日新增1例本土確診病例 在大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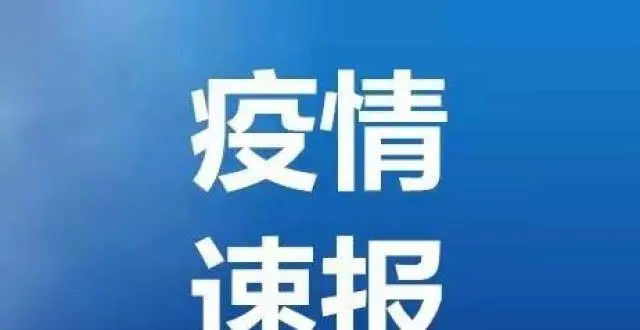
關於中國臨床研究護士現況最全麵的調查結果發錶啦!

葉剋強團隊新研究:調節這一通路或可延長壽命,預防阿爾茲海默癥

新發現:晚期宮頸癌的新療法——免疫治療聯閤放化療取得新突破

首款口服藥艾麯波帕上市,開創血小闆減少癥的新紀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