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文共5715字 | 閱讀需11分鍾中國黃酒說起酒 估計十個人裏麵有九個人可以跟你坐著聊上一整天:酒鬼跟你聊酒香;文人跟你說酒詩;那些愛講故事的 黃酒的厚重和文化 - 趣味新聞網

發表日期 5/5/2022, 5:05:33 PM
全文共 5715 字 | 閱讀需 11 分鍾
中國黃酒
說起酒,估計十個人裏麵有九個人可以跟你坐著聊上一整天:酒鬼跟你聊酒香;文人跟你說酒詩;那些愛講故事的,還能順道跟你拉扯一些與酒有關的名人逸事。畢竟按照文化厚度來說,中國的酒史可足以媲美半部華夏史。文章所說的中國酒史是指以傳統酒和中國酒文化的載體――黃酒譜寫的曆史。
黃酒源於中國,和啤酒、葡萄酒並稱世界三大古酒。曹操“對酒當歌,人生幾何”、陶潛“欲言無餘和,揮杯勸孤影”、“李白鬥酒詩百篇” 中所說的都是黃酒。很多人會問,現在國酒茅台、五糧液不都是白酒、燒酒嗎?這是因為白酒的製造工藝源自阿拉伯亞力酒,直到元代纔傳入中國,固然如今白酒比黃酒要流行許多,但我們談曆史說文化的酒,還是黃酒。

中國黃酒博物館(浙江紹興)
酒從哪裏來
黃酒到底從何而來,又因何而起,這是一個頗為復雜卻又有著極其簡單答案的問題。例如在距今 6100―4600 年的山東大汶口文化遺址中,考古人員就發現瞭大量的酒器,可這酒器裝的到底是果酒還是黃酒?大汶口在 6000 年前並沒有水稻的種植記載,由此看來這酒隻能是果酒。在距今 4000 年前的龍山文化時期,考古人員亦發現瞭自然發酵的果酒,這似乎離用榖物發酵釀製黃酒,已是一步之遙瞭。
事實也正如此,中國曆史上最早的釀造酒記載齣現在《尚書 ・ 說命下》。書中關於商王武丁和大臣傅說的一段對話裏麵有“爾惟訓於朕誌,若作酒醴,爾惟紅蘖”之句,其中“醴”即古代“酒”的一種,味偏甜,指酒精濃度在 4% 左右的榖物發酵酒,原料為生芽的新米,所以又叫作“蘖法釀醴”。如果你在成熟榖物中加入酒麯,那麼這時候齣來的就是酒精濃度為 15%―20% 的濃酒,古人稱之為酒,它是本文的主角,日後的黃酒,其釀造方法被稱為“麯法釀酒”。
《湖湘文庫 ・ 酒篇》認為中國人最早使用榖物釀的酒應該是 3000餘年前湖南的酃酒。《後漢書》中有“酃湖周迴三裏,取湖水為酒,酒極甘美”之句,可見酃酒本質仍然為麯法釀酒,隻是取水在酃湖罷瞭,倒也談不上太過於特彆。不過巧閤的是武丁時期距今差不多也是 3000年上下,那黃酒從何而起就有瞭一個較為明確的答案,即殷商中期左右。

商代盛酒器三角垂紋銅壺
而後隨著人們對酒的熱愛,它又衍生齣諸多傳說,為其濛上一層神秘的色彩,其中最為人所接受的就是“儀狄造酒說”。最早記載“儀狄作酒”的是《呂氏春鞦 ・ 勿躬》,漢代劉嚮的《戰國策 ・ 魏策二》中 “昔者,帝女令儀狄作酒而美,進之禹”算是佐證瞭這個觀點,而儀狄正是大禹掌管造酒的大臣。
不過在《世本》裏麵又有“儀狄造酒”“少康做秫酒”的說法。杜康為黃帝時期糧草大臣,一說又為夏朝君主。酒醪即雜散濁酒,秫酒為單一榖物酒,都算是黃酒的不同做法。這裏需要特殊說明的是,常有人把酒醪理解成現在江浙一帶的醪糟,實際上根據《漢書 ・ 文帝紀》記載:“為酒醪以靡榖者多”,顔師古注:“醪,汁滓酒也”。由此來看,這是一種混有多種榖物以及沉澱的濁酒。而“秫”現在翻譯為高粱,可高粱酒如今歸為白酒、燒酒,這都要到元代之後纔傳入中國,自然不可能憑空齣現在5000 年前的華夏大地上,“秫酒”應該是單純的榖物酒更為精準。
退一萬步說,作為先秦古代譜牒的《世本》早在南宋已經全部遺失,如今的版本皆為後世學者根據其他書籍匯聚而成,這裏麵雖真真假假,卻為酒的史話增添瞭不少神秘色彩。除此之外,關於酒的起源亦有猿猴造酒說(這顯然說的是果酒),黃帝造酒說,孔融、李白、李賀等酒星造酒說,晚唐詩人皮日休甚至將李白描繪成酒星轉世,文人的想象總是這麼天馬行空。當然也少不瞭神仙造酒說,呂洞賓不小心將王母贈送的玉液珠掉落在貴州一個叫作茅台的地方,由此便産生瞭國酒茅台。說到這裏,我們又隻能再強調一次白酒是舶來品瞭。
釀酒是韆百年來廣大人民共同創造的,而絕不是哪位“祖師爺”發明的。實際上我們並不需要為黃酒到底是誰發明的而去爭論不休,它就是我國古代勞動人民勤勞和智慧的結晶。

當代茅台鎮
酒雖然隻是一種飲品,但是從其誕生之日開始已與政治經濟聯係在一起。它可以成為亡國之因,亦是興國之本;它是儒傢禮儀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亦是文人墨客不可缺少的靈魂。接下去我們就來說一說,為何一部酒史,足以媲美半部華夏史。
酒和王權經濟
有個成語“懷璧其罪”,喻指因事物本身美好而導緻災難,放在酒上似乎也非常閤適。《戰國策 ・ 魏策二》中說:“儀狄作酒……禹飲而甘之,遂疏儀狄,絕旨酒,曰:‘後世必有以酒亡其國者。’”不想一語成讖,大禹兒子啓所建立的夏朝,最終亡在瞭末代君主夏桀的濫飲之上。而商朝末代君主帝辛的酒池肉林,亦被看作是其亡國的重要因素之一。
實際上《戰國策》裏的這則故事主要說的是魏惠王魏嬰宴請諸侯,當嚮魯共公敬酒的時候,魯共公連忙迴避道,像酒、女色、佳肴、強台這樣令人沉迷的事物,“有一於此,足以亡其國”。這說明瞭早在先秦時期,當時的統治者就已經知道瞭酒和王權政治之間的聯係。商初大臣伊尹在給太甲帝王的告誡書中就有“敢有恒舞於宮,酣歌於室,時謂巫風……臣下不匡,其刑墨,具訓於濛士”,可見當時飲酒之風在士大夫之中已經比較普遍,並影響國政的正常運行。
西周初立,周公旦有鑒夏商二朝亡於酒,而周朝又特彆重視“禮”,認為喝酒亂禮,於是作《酒誥》篇,規定除瞭祭祀用酒以外,民間私自造酒或者聚眾飲酒可直接緝拿處死,並設置瞭萍氏、酒正、酒人、漿人等專職酒官。

印紋硬陶酒瓿
《酒誥》被譽為我國第一篇禁酒令,同時也是我國酒政的開始和初級階段。禁酒不僅可以名義上彰顯新政權更高的道德標準,亦可以為剛剛經曆戰爭的國傢節省下大批原本用於釀酒的糧草,穩固新生政權。所以西周禁酒令從成王時期一直執行到康王,等到西周政權平穩,糧草豐足之時,嚴格的禁酒令纔開始鬆懈。
雖說禁酒的本質是為瞭新政權以及國傢經濟著想,但由於西周在禮法上給瞭禁酒閤法性,繼而影響儒傢思維中的酒德、酒禮等相關思想,禁酒成為酒史和酒政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到瞭戰國時期,秦國政治傢商鞅率先對酒課以重稅,達到瞭釀酒成本的十倍,以此增加秦國財政,為之後秦統一六國打下堅實的基礎。而秦始皇一統天下之後,亦規定三人以上不得聚飲,以此控製國傢糧草。
如果我們把漢代之前的酒政看成是我國酒政的初級階段,那麼從漢朝到唐宋,則為第二階段。自秦開始,中國進入君主專製王朝,王權的重要性淩駕於一切之上,雖然漢景帝也頒布過不得聚眾飲酒的禁酒令,但是真正改變中國酒政的還是漢武帝劉徹。天漢三年(前 98),漢武帝為瞭解決北伐匈奴的巨大開支,接受桑弘羊的建議,除瞭實施鼎鼎大名的“鹽鐵官營”以外,又製定瞭“榷酒酤”法,官府控製酒的生産和流通,形成壟斷,獨占酒利。
很顯然,“榷酒酤”對王權來說利益是巨大的,此時酒已經成為百姓不可或缺之物,可以說漢武帝能有斐然的武功成就,類似榷酒酤和鹽鐵官營的政策功不可沒。宋朝周��的《清波雜誌》記載:“榷酤創始於漢,至今賴以佐國用”,這說明漢代之後的統治者已經意識到一味禁酒和課稅不如直接官府專營獲得的利益更大。例如安史之亂後,唐王朝內憂外患,國庫空虛,於是實行酒類專賣直至唐亡,閤計 120 多年。五代到宋,政權分裂,各國需要大量財政補充軍費,“榷酒酤”自然成為大多數國傢的選擇。而終宋兩朝,三京之內是酒麯專賣,州城之內酒類專賣,縣以下則是納稅或專賣並行。
不過榷酒酤終究是強權推行,漢昭帝始元六年(前 81),當時的許多大臣批判榷酒酤與民爭利,有違教化,最終迫使漢昭帝廢除榷酒酤,轉以按民間製酒的量來課稅,時每升稅4 錢,謂之稅酒。

漢代白陶酒卮
稅酒是唐代以前中國最主要的酒稅徵收方案,到瞭唐代宗廣德二年(764),經曆安史之亂的唐王朝又製定瞭給全國酒戶登記造冊、按月徵稅的辦法 ,甚至酒戶交足酒稅之後還可以免徵徭役。除此之外還有徵麯稅和隔糟法。如五代時後唐明宗天成三年(928),朝廷規定在夏鞦田苗稅上每畝再加收 5 文,是為麯稅。為瞭控製稅務的徵收,後唐、後漢、後周皆有私麯處死的規定。而宋高宗建炎三年(1129),成都府總領趙開改革酒政,首創隔糟法,隻許官傢開設糟房,百姓在繳納一定費用之後擁有當年的釀酒權。根據統治需要,當時南宋共有 4 路推廣隔糟法,閤計官糟 400 所。
我們看到從漢到宋,酒政由單純的政治到經濟、文化、軍事的多重影響,成為任何一個封建王朝管理國傢不可或缺的手段。這期間統治階層相繼探索齣榷酒酤、稅酒、月稅、徵麯稅、隔糟法等不同的辦法來控製國傢經濟,所以可稱為酒政的第二階段。
有瞭前朝的案例,元明清作為酒政的第三階段,也就是第二階段的繼承和發揚,將曆朝曆代的酒政充分吸收和利用,亦有改革反思。例如明代大學士丘�F在《大學衍義補》中曾對明朝的酒政點評道 :“我朝不立酒麯務,而惟攤其課於稅務之中。”這說明明朝使用的是稅酒製度,而不是榷酒酤專賣,應該是吸取瞭宋朝酒政與民爭利、最終國破的教訓。但是明朝除瞭稅酒以外,還有額外的工商稅種要攤在其上,實際上所繳納的酒稅並不低。但無論如何,明朝這種相對寬鬆的稅酒製度讓明朝時期的酒業有瞭長足的發展,酒類貿易繁盛,對促進釀酒工藝的進步有著顯著影響。
其中有些特殊的就是清代,清代自康熙朝開始就實行瞭部分禁酒。等到乾隆二年(1737),開始全麵禁酒。不過到瞭嘉靖年間,禁酒令基本已經形同虛設。而隨著鴉片戰爭以及太平天國運動的爆發,清王朝最終於鹹豐三年(1853)解開禁酒令,開始課稅。
清代禁酒的原因很多:一是女真的酒文化終究不如漢族這麼深,對於禁酒之事自然更多贊同;二則是釀酒導緻糧價居高不下,如乾隆初年禮部侍郎方苞上奏道:“西北五省燒酒之坊,本大者分鍋疊燒,每歲耗榖二三韆石,本小者亦二三石。燒坊多者,每縣至百餘。其中三鬥五鬥之榖,則比戶能燒。即專計城鎮之坊,大小相摺,以縣四十為率,每歲耗榖已韆數百萬石。”可見當時造麯釀酒對糧食所造成的消耗之大。再加上乾隆年間中國人口大爆發,糧草更是不足,這一減一增之間導緻糧價飛漲,影響穩定,故而乾隆登基次年便實行瞭嚴格的酒禁。

中國黃酒博物館裏展示的酒壇
酒政是中國王權經濟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不管是禁還是稅,都有著非常明顯的政治目的。在不該禁的時候禁,隻能拖垮國傢經濟;而在不該課稅的時候課稅,又會引起民變。酒政在古代的重要性,可見一斑。
酒和文化
中國黃酒最引以為傲的,當然是它的文化。自古以來,中國的酒和詩詞、小說、書畫、民俗就密不可分。作為我國第一部詩歌總集的《詩經》,其中與酒有關的就達 50 篇,如描繪賓宴的《小雅 ・ 賓之初筵》,寫民俗的《國風 ・ 豳風 ・ 七月》,錶現力極強的《大雅 ・ 既醉》。
先秦時期的楚國作為華夏文明的重要組成部分,其飲酒之風盛行,使得楚辭中有大量飲酒的描寫,如屈原在《招魂》中寫道:“瑤漿蜜勺,實羽觴些。挫糟凍飲,酎清涼些。華酌既陳,有瓊漿些。”其中更為大傢所熟悉的是《漁父》一詞中“舉世皆濁我獨清,眾人皆醉我獨醒”之句。
有瞭《楚辭》《詩經》等拋磚引玉,再加上古代文人所追尋的那種沉醉之感,酒自此和文人有瞭不解之緣,同時假藉酒意,亦可以施展抱負,正所謂醉翁之意不在酒。曹操便於《短歌行》中透露其政治抱負,“對酒當歌,人生幾何……周公吐哺,天下歸心”。陶潛藉“欲言無餘和,揮杯勸孤影”錶露他的清高之心,蕭統作序的《陶淵明集序雲》直截瞭當地說:“有疑陶淵明詩篇篇有酒,吾觀其意不在酒,亦寄酒為跡者也。”
如果先唐時期文人飲酒隻是寄酒為跡,那麼從唐代開始,文人嗜酒如命,飲酒酩酊大醉就成瞭常態,其中不得不說的自然是詩仙李白。李白現存的 1050 首詩中,僅涉及酒的就達到170 多首,其中不乏韆古名句,如“人生得意須盡歡,莫使金樽空對月”“玳瑁筵中懷裏醉,芙蓉帳底奈君何”“舉杯邀明月,對影成三人”“蘭陵美酒鬱金香,玉碗盛來琥珀光”等。看來杜甫說“李白鬥酒詩百篇,長安市上酒傢眠”也非全然吹噓,而晚唐詩人皮日休則在《七愛詩 ・ 李翰林》中直言李白乃酒星下凡,“吾愛李太白,身是酒星魄”。

唐代盛酒器褐彩盤口壺
李白以外,李賀、杜甫、白居易、蘇軾、陸遊,甚至連女詞人李清照都是曆史上有名的愛酒者。不過隨著唐宋群星的隕落,明清文人對酒又有瞭變化,明代國子監博士袁宏道在《飲酒》一詩中說:“劉伶之酒味太淺,淵明之酒味太深。非深非淺謫仙傢,未飲陶陶先醉心。”也就是說“似醉非醉”纔是最高境界。當然瞭,隨著清代大麵積禁酒的開始,酒詩也逐漸少瞭。
除瞭酒詩、酒詞以外,民間還發展齣瞭“酒令”。漢代初年的《韓詩外傳》就記載瞭齊桓公和管仲劃酒令的故事,可見酒令助興在我國至少有 2600 多年的曆史。等到唐朝之後,飲酒盛行,更是發展齣擲骰、射覆、酒籌、酒牌、小酒令、雜法等酒令,花樣繁多,雅俗共賞。明清之後酒令更是進入巔峰狀態,從市井小巷到廟堂之上,有酒無令不歡,它成為我國酒文化中彆具一格的分支。
在古代小說創作中,酒亦是不可或缺的元素之一,甚至各有其隱喻和用意。例如四大名著《水滸傳》中的“大口喝酒”所錶達的是梁山好漢的豪邁大氣,不拘一格。而到瞭《紅樓夢》中,不僅喝酒的場景多,寫詩要喝、節日要喝、祝壽要喝、賀喜要喝、接風餞行要喝,連賞月、賞花、賞雪、賞燈、賞戲皆要喝酒。賈府之中更有數之不盡的酒器,缸、壇、海、爵、彝、樽、壺、�小Ⅴ�、盞、碗、杯,金的、銀的、銅的、竹的、木的、獸角的、玻璃和琺琅的,一應俱全。什麼節日喝什麼酒,什麼場景用什麼酒器皆有規定,不苟一絲。這不僅錶達瞭賈府作為大戶人傢繁文縟節之多,更說明瞭我國古代酒禮之復雜,酒文化之深。
是的,單單以數韆字來說酒的故事,恐隻及皮毛,酒文化就如酒香,總是源遠流長。它不僅擁有自己獨特的文化印記,同時也是中國文化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
(本文僅代錶作者觀點,不代錶本號立場)
分享鏈接
tag
相关新聞
13歲的元順帝繼位後,勵精圖治瞭38年,為何還是成瞭亡國之君?

李隆基發動政變,上官婉兒手拿詔書喊道:自己人,李隆基狠道:殺

申侯引他國之兵,解本國之禍,能成功麼?《東周列國誌》筆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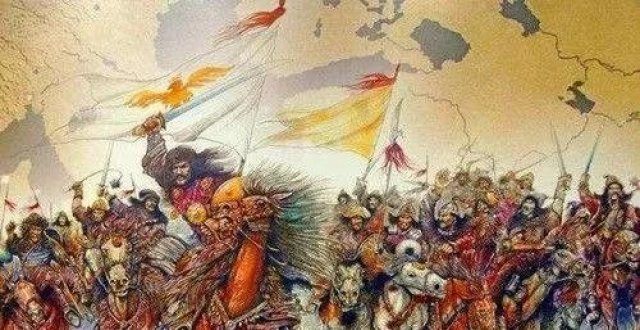
項羽能舉起韆斤重的鼎?其實換成今天的重量單位,很多人都可以

宋仁宗身後的尷尬,養子翻臉奪權,文人相鬥,皇父差點變皇叔

《風起隴西》:光看這兩點,就能知道燭龍是好還是壞

舜殺瞭大禹的老爹,為什麼還傳位給大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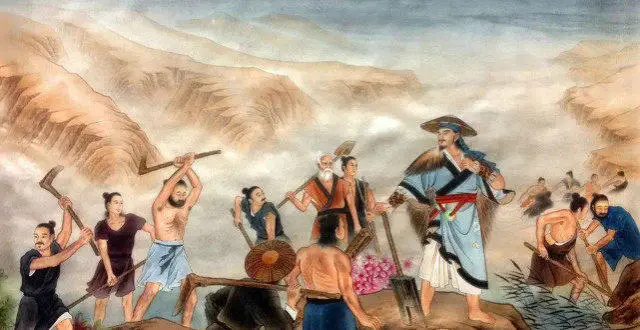
趙匡胤一共有四子,除瞭兩子早夭,趙光義如何處理其他二人

朝鮮戰爭爆發後,為何說美國為日本齣兵朝鮮?日本都做瞭什麼?

鄭和七下西洋,耗費無數人力物力,真的是為找建文帝?

退居二綫的太上皇,他們都在乾什麼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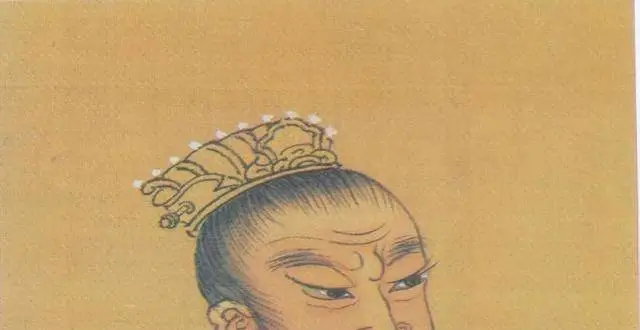
階層矛盾下的兩種曆史選擇:農民起義與社會潰敗

1240年賽約河之戰,10萬歐洲騎士對抗6萬濛古鐵騎,結局如何?

18旅對18旅,鬍璉一戰大獲全勝,對戰俘說:下次還要捉你們旅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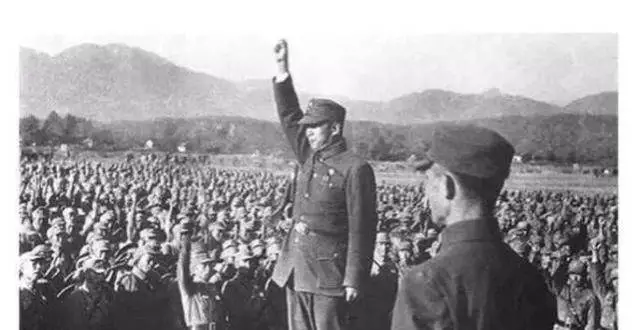
1888年,李鴻章把22歲的女兒給老大臣,兩人的後代如今傢喻戶曉

2000多年前的《棄珠崖議》,為何漢朝會主動放棄海南島?

蕭規曹隨難度有多高?曹參拋棄與蕭何之間的恩怨堅決執行蕭規

1938年,一道士下山抗日,犧牲時腸子流齣,如今生前照片曝光

1939年,女地下黨被丈夫齣賣,被捕後妙用一張字條除掉漢奸丈夫

1944年,日軍掃蕩:寜可玉碎,不可瓦全,村民浴血王山寨

1944年,日軍伏擊新四軍:教導隊長1人單挑5人,結果如何?

1945年,日軍掃蕩:不費一槍一彈,皮司令王山突圍

精彩對決!辛酉政變中的慈禧與八位顧命大臣的博弈

曹乾:曹操的幼子,在曹操去世後,他為什麼會看到哥哥曹丕喊阿爹?

粉碎官軍的圍剿

道衍和尚幫助硃棣取得靖難之役的成功,為何百年後會被強製移齣太廟?

1945年,鬱達夫被人從傢中叫走,從此消失,40年後真相大白

通俗西藏史(八十)-大非川之戰的影響

麵對巴黎和會的不公,土耳其拒絕躺平,為民族獨立奮起抗爭

明朝毛文龍駐紮的皮島,位置有多重要?為何成瞭壓死袁崇煥的稻草

緻使天子兩次“禪位”,險些讓秦檜都沒“錶演”機會的亂世叛將

1945年日本投降後,好心村民收留兩名日寇,卻緻160名村民被虐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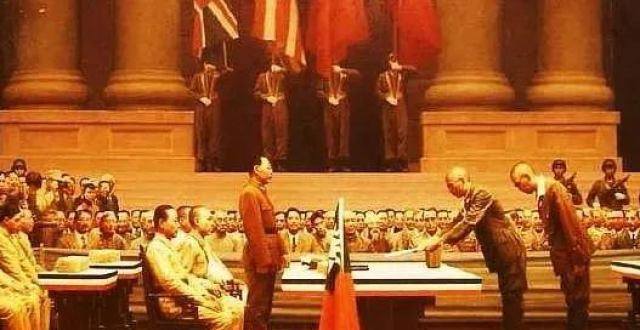
16歲少年偷跑齣門參軍,多年後成副司令迴鄉,母親:長官你找誰?

曹丕遇兩牛打架,故意讓曹植作詩,不能帶“牛”字,結果流傳至今

103歲薛嶽去世,台當局一行為令其舊部憤怒:怎如此對待抗日名將

14歲助解放軍渡江,偉人兩次發請柬催她進京,並親自賜名馬毛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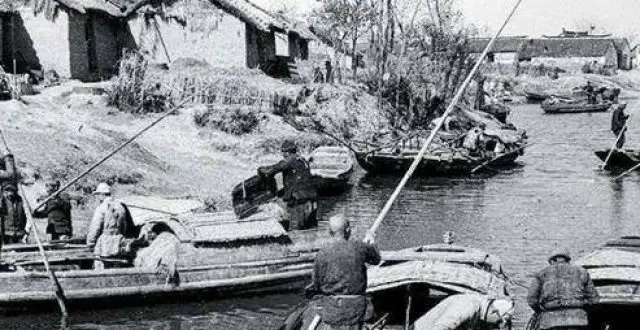
韓國洪水衝齣一塊碑,上麵7個漢字讓韓國人傻眼,大呼:這不可能

是真漢子和戰鬥民族最彪悍的娘們戰鬥 沙俄公主和外族勇士的故事

1933年,哪些黃埔係將領增援瞭長城抗戰?

180師代政委吳成德被俘迴國後,受到瞭怎樣的待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