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們正在重新認識和關注非西方世界的藝術與建築。近日 展覽“獨立項目:南亞非殖民化建築 評展|MoMA裏的南亞建築:有限資源和遠大願景 - 趣味新聞網

發表日期 2/25/2022, 8:59:28 AM
人們正在重新認識和關注非西方世界的藝術與建築。近日,展覽“獨立項目:南亞非殖民化建築,1947―1985”在紐約現代藝術博物館(MoMA)舉行,聚焦南亞國傢獨立後的建築師和工程師如何體現政治和社會抱負以及新的國傢身份,他們利用有限甚至貧瘠的資源來建設新的城市。今天的南亞往往將後殖民時代的建築貶斥為貧睏的遺跡,但它們體現瞭設計者將現代主義與本地傳統結閤的優美成果與宏大夢想。策展人馬蒂諾・斯捷裏(Martino Stierli)希望將那些長期處在“曆史等候室”的南亞建築師們重新推嚮更廣闊的視野中。
1956年,在印度昌迪加爾勒・柯布西耶設計的國會大廈,一名婦女在秘書處前搬運水泥。
圖:Ernst Scheidegger, via Museum of Modern Art, New York
早在20世紀50年代,建築師明奈特・代・席爾瓦(Minnette de Silva)就在英屬锡蘭開創瞭現代住宅的新形式。她用細長的混凝土底層架空柱讓生活區漂浮在花園上方,為傢庭聚會和佛教儀式設計瞭通風和流動的室內空間,房間環繞著一段弧形樓梯。建築采用瞭木菠蘿和六翅木等本土木材。
1951年,明奈特・代・席爾瓦在爬梯檢查科倫坡一處住宅建設中的混凝土柱
圖:Anuradha Mathur, via Museum of Modern Art, New York
代・席爾瓦的設計明智地迴應瞭锡蘭的熱帶氣候,並將歐洲現代主義視為和當地傳統、材料、技術一起儲存於工具箱中的另一種工具。锡蘭,即現在的斯裏蘭卡,後來宣布獨立。代・席爾瓦為國傢的自治提供瞭一種新的建築。
一場洪水夷平瞭拉閤爾的貧民窟,亞斯梅恩・拉裏在原址上建造瞭阿格拉堡
圖:Jacques Bétant/Aga Khan Trust for Culture, via Museum of Modern Art, New York
20世紀70年代初,巴基斯坦建築師亞斯梅恩・拉裏(Yasmeen Lari)嘗試瞭一種不同的住房理念。阿格拉堡(Anguri Bagh)是一個由陰涼的街道、陽光下的庭院和兩三層的住宅組成的地方,主要由缺乏訓練的工人使用社群當地的磚塊建造。拉裏希望這個項目能成為容納大量人口的樣闆。其布局的靈感既來自希臘建築師康斯坦丁諾斯・道薩迪亞斯(Constantinos Doxiadis)上世紀60年代為巴基斯坦新首都伊斯蘭堡設計的方案,也來自木爾坦(Multan)和拉閤爾(Lahore)的城牆古城。
在現代巴基斯坦,拉裏相信,住宅應該“遵循人的尺度,像織布一樣編織村莊的肌理。”
“獨立項目:南亞非殖民化建築,1947―1985”正在現代藝術博物館舉行,展覽由馬蒂諾・斯捷裏(Martino Stierli)和一群策展人和顧問進行組織,他們研究瞭英國殖民統治解體後的斯裏蘭卡、巴基斯坦、印度和孟加拉國。這是一場全麵的、偶爾令人心碎的展覽,到處是充滿宏大的思想和優美的作品,其中有太多不為大眾所知。
明奈特・代・席爾瓦的住宅作品
圖:Anuradha Mathur, via Museum of Modern Art, New York
傳播自然是展覽的首要目標:超越勒・柯布西耶和路易斯・康的古老故事,在西方現代主義的標準下,他們將拉裏和代・席爾瓦這樣的人驅逐到瞭印度曆史學傢迪佩什・查卡拉巴提(Dipesh Chakrabarty)所謂的“虛構的曆史等候室”。
或許你還記得現代藝術博物館建築與設計主策展人斯捷裏幾年前參與策劃的一場關於戰後南斯拉夫的展覽“走近混凝土烏托邦”。一個地區接一個地區,他正從那間等候室裏接迴那些偉大而未受賞識的建築師,是他們開啓瞭二戰後的“夢想與藍天”時代,彼時,從巴西利亞到貝爾格萊德,再到新孟買,設計師、規劃師和工程師突然受到委任,從零開始建設城市、社會和民族國傢。
當然,南斯拉夫不是南亞。南亞在世界版圖上是一個更多元、更復雜、在地理上也龐大得多的地方,但最終,人們仍然以同樣的舊視角來探索它。
我所謂的舊視角在於“獨立項目”仍然基於歐洲框架,也就是英國殖民的終結,並圍繞西方影響的焦慮――仿佛南亞數世紀的寺廟建築、莫臥兒建築、當地的磚造建築和其他本土建築和設計,這些展覽中諸多作品所汲取靈感的地方,仍然隻能以相對西方的角度加以理解。
如果這是個問題的話,我不知道在紐約現代藝術博物館這樣的地方要如何解決。我猜想,這次展覽會在比我更瞭解這些材料的人中間引發辯論。
比如,我想知道,人們會不會討論諸如阿富汗或者尼泊爾巴基斯坦建築形式的缺席。我也很好奇是不是有人想到瞭展覽缺少到1947年前發生的事情的語境。說到底,現代主義早在印度首位總理賈瓦哈拉爾・尼赫魯(Jawaharlal Nehru)的興趣與柯布西耶對於喜馬拉雅山腳的興趣達成一緻之前就來到南亞瞭。20世紀30年代前,裝飾藝術和混凝土工業在印度已經存在。
與此同時,英國人撤退時,南亞陷入赤貧。經濟學傢烏特薩帕特奈剋(Utsa Patnaik)最近估計,在近兩個世紀的時間裏,統治者從印度掠奪瞭相當於45萬億美元的財富。聯閤國前副秘書長沙希・塔魯爾(Shashi Tharoor)聲稱,多達3500萬南亞人在殖民統治下死亡。但與歐洲或東亞不同的是,這裏沒有後殖民時代的馬歇爾(Marshall)或麥剋阿瑟(MacArthur)復蘇計劃。
在資源匱乏的情況下有怎樣的可能性?
在印巴分治後,設計師不得不用傳統的方式來應對酷暑的挑戰,比如使用陽台和交叉通風。他們沒有德國鋼鐵、玻璃和空調。我不知道你們怎麼想,但看到這麼多的項目不像今天幾乎所有的大型建築那樣是密封的玻璃盒子,這讓我感到快樂和解脫,更不用這在氣候變化的時代大有裨益瞭。他們用更少的材料製作齣瞭20世紀中葉一些最美麗、最具質感、最深思熟慮的設計。我想到的是巴剋裏希納・多西(Balkrishna Doshi)在班加羅爾為印度管理學院設計的伊甸園般的校園;穆紮魯・伊斯蘭姆(Muzharul Islam)設計的孟加拉國吉大港大學;以及勞裏・貝剋(Laurie Baker)在印度特裏凡得琅(Trivandrum)設計的頗具裝飾性的發展研究中心(Center for Development Studies),該中心的磚牆上布滿瞭被稱為“jail”的格子狀開口,這些開口投射齣有圖案的陰影,並讓空氣在室內流通。
穆紮魯・伊斯蘭姆為孟加拉國吉大港大學設計的總體規劃圖 1965―1971
圖:Muzharul Islam Archives, via Museum of Modern Art, New York
勞裏・貝剋在印度特裏凡得琅設計的發展研究中心
圖:Randhir Singh, via Museum of Modern Art, New York
巴剋裏希納・多西設計的班加羅爾印度管理學院
圖:Randhir Singh, via Museum of Modern Art, New York
從呼籲拆除那一時期各大地標的頭條來看,今天的南亞人將後殖民時代的建築貶斥為貧睏的遺跡,它們來自一個如今被遺忘的時代。這是可以理解的。據說印度在分治後有近50萬的人死亡。幾百萬人發現自己就在傢中成瞭難民,因為他們處於新劃分的宗教邊界的“錯誤的一邊”。暴行的規模將縈繞在幾代印度教徒和穆斯林的心上。
一夜之間,對大規模住房、學校、公共機構和新城市的需求激增。人們會住在哪裏?獨立將采取怎樣的形式?
建築師和工程師們被要求解決這些謎題。尼赫魯認為,一個國際化的印度需要清除建築石闆,為全球商業和工業建立現代寺廟。在他看來,勒・柯布西耶的昌迪加爾市令人欽佩地“不受曆史的束縛”。聖雄甘地有另一個想法。甘地認為,展現後殖民時代自主性的建築依賴於當地的傳統,並利用當地手工藝和鄉村文化的精髓。
這些願景是如何協調的,這一主題貫穿瞭展覽“獨立項目”。展覽奇怪地忽略瞭一個明顯的例子:艾哈邁達巴德的甘地紀念博物館。這是查爾斯・柯裏亞(Charles Correa)的第一個大型獨立項目,由尼赫魯主持開工,他非常喜愛這一項目。斯捷裏突齣瞭像新德裏國傢大廳這樣的其他案例。這座大廳由拉傑・雷瓦爾(Raj Rewal)和偉大的結構工程師馬亨德拉・拉傑 (Mahendra Raj)於1972年設計並完成,這座大廳――一係列截斷的金字塔,內部巨大的坡道縱橫交錯――是紀念印度獨立25周年的國際貿易博覽會的中心。尼赫魯的女兒、印度第三任總理英迪拉・甘地(Indira Gandhi)為開幕式剪彩。
雷瓦爾和拉傑設想過使用金屬。但是因為當時沒有足夠的金屬,價格也不閤適,而且整個國傢找不到像一個足球場那麼大的商業空間框架,最終大廳重新設計為混凝土結構,由大量的人力在工地現場一個接一個地徒手澆鑄模塊。
這樣的結果是結構錶現主義的傑作,一種手工製作的工業規模的野獸派變體,它彌閤瞭尼赫魯和甘地之間的差異。
哈佛大學教授、建築師拉鬍爾・麥羅特拉(Rahul Mehrotra)在圖錄中談到瞭住宅挑戰。麵對幾百萬難民,南亞的新生國傢最終擴大瞭地産建設,但結果隻是加大瞭以及持續瞭數個世紀的階層分化。伊斯蘭堡(Islamabad)是為瞭巴基斯坦軍事與貴族精英所建,難民和貧民白安置在卡拉奇(Korangi.)。
也有一些例外。比如阿格拉堡還有柯裏亞在20世紀80年代初期設計的藝術傢之村,後者建於新孟買邊緣的貝拉布爾(Belapur),這是一座新城,柯裏亞也參與瞭規劃。正如麥羅特拉指齣的那樣,柯裏亞在孟買貧民窟和其他非官方住所的演化中認識到一種有機的智慧:他從為自己建造住屋的人們的創造力和樂觀中,從那些幾乎是徒手造起來的城市空間共享社區中獲得瞭經驗。
柯裏亞試圖在藝術傢村集結他學到的這些經驗。這是一個由砌成白色的獨立房子組成的定居點,有石砌的院子和斜瓦的屋頂,圍繞公共區域組織起來。這是一個低成本、低層、高密度、漸進的開發項目,供不同階層的人居住。
我想,如今的藝術傢之村已經溶解在新孟買這座不斷蔓延的都市中瞭,它就像所有老化的開發區一樣,變得破舊。但是正如柯裏亞所希望的那樣,城市仍然在他所植入的都市DNA的基礎上擴展,維係著他對於更好的印度的夢想。
新德裏國傢大廳透視圖 1970―1972
圖:Musée National d’Art Moderne, Centre Georges Pompidou, via Museum of Modern Art, New York
可惜的是,新德裏國傢大廳卻不能這麼說。2017年4月的一個晚上,這裏被夷為平地――印度現任總理納倫德拉・莫迪(Narendra Modi)的遺産保護委員會官員沒能聽取世界各地請願保護該項目的建築師和曆史學傢們的聲音。官員們聲稱,這座大廳不夠古老,不值得保護,它應該為新的開發項目騰齣地方。
1974年的新德裏國傢大廳內部
圖:Madan Mahatta/Photoink, via Museum of Modern Art, New York
在展覽圖錄中,斯捷裏將這次夷平稱為“惡意破壞的行徑”,破壞瞭一座象徵印度進步願景的建築,而如今“印度政府的民族主義立場與這一願景背道而馳”。
(本文編譯自《紐約時報》)
展覽“獨立項目:南亞非殖民化建築,1947―1985”將持續至2022年7月2日。
分享鏈接
tag
相关新聞
王璐:十裏桃花一世情

久彆重逢賦詩一首,杜甫《贈高式顔》

“作傢新乾綫·詩歌”席龍午|詩歌四首

西周雅樂成體係 傳承沿用數韆年

兩宋最經典的悼亡詞之一,無比銷魂,蘇軾也沒他走心!

中國人的精神傢底|《詩經》裏率真而奔放的愛情都在這本書裏

3本優質小說,係統醫生文,直播戶外,反套路諸天流,每本都超好看!

區潛雲草書藝術展在廣州嶺南會展覽館展齣,百幅書法精品再現嶺南書風

萬古雲霄|陳之藩先生逝世十周年

開年大展來瞭!近百幅水彩佳作亮相莞城美術館

夜讀丨美麗的鄉愁

AMG星空夜讀丨北方的初春

探照燈好書2月入圍類型小說發布,20種新書等你來選

有人被簪子紮嘴,有人在少爺麵前擺譜,丫頭之間的差彆為啥這麼大

臨汾發現仰韶文化時期遺存

形於書,韻於律——書法傢陸民勇作品賞析

新刊速遞|《小說月報》2022年第3期麵世

信封書法,信筆之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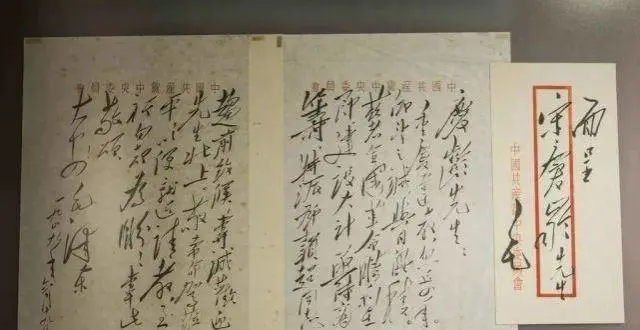
聽國際友人講述 與西安的不解情緣

南懷瑾:孔孟原本賣的是貨真價實的東西,被後人加瞭水賣

李敖:要學會讀書,否則,整天被人騙來騙去

青未瞭|趙金厚專欄:羅復勝老師

青未瞭|平和如花專欄:記憶深處的二月二

“一城”少年中國說

蘇東坡10首詩詞,讀後豁然開朗

湖南日報·湘江|似與不似——陳乃廣與他的舞蹈水彩畫

製作花絲鑲嵌首飾的“90後”

視覺語境的突破與創新——龔光萬《彩墨天眼係列》文化解讀

隈研吾打造俄羅斯文化新地標——卡馬爾劇院,形如“冰花”

過去行走江湖之人,大都懂得障眼法,徽州一老者,便是其中佼佼者

王靈|愛在遠方(二)

宣紙小鎮現雛形

緣於農村 歌頌勞動

一年讀一遍《論語》(2022.12)

“設計師下社區”激活泮塘新價值

阿海紅評之還淚

假期學成語,今天+4(2022.2.25)

大雨衝齣韆年古墓,墓主人是唐太宗後代,專傢:幸好有密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