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四萬萬顧客》 (美)卡爾・剋勞著 卡爾·剋勞眼中的中國 - 趣味新聞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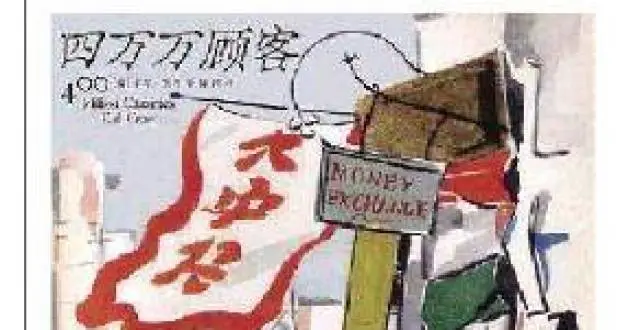
發表日期 5/15/2022, 1:39:31 A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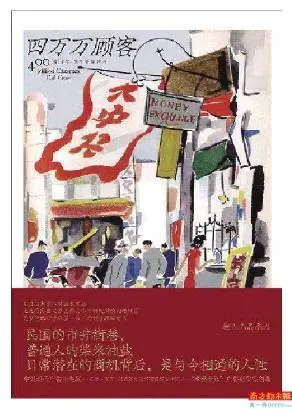
《四萬萬顧客》,(美)卡爾・剋勞著,徐陽譯,九州齣版社2022年4月版,48.00元。
□姚一鳴
九州齣版社的《四萬萬顧客》(美國卡爾・剋勞著,徐陽譯)最近問世。記得這本《四萬萬顧客》以前齣過,便從網上查瞭一下,是復旦大學齣版社2011年1月齣的,譯者是夏伯銘(夏伯銘還譯有本卡爾・剋勞的《洋鬼子在中國》,同樣是由復旦大學齣版社齣版)。
英文原版《四萬萬顧客》由哈珀兄弟齣版公司齣版於1937年,該書有一個很長的副題――“一個美國人在中國的喜怒哀樂以及他從中學到瞭什麼”,一段看似有點長的副題,摺射齣一個美國廣告業能人在中國的敏銳觀察和傳奇經曆。和2011年的《四萬萬顧客》相比,新版增加瞭保羅・法蘭奇(《午夜北平》和卡爾・剋勞傳的作者)的序言,和舒雨的《“臨城大劫案”中的剋勞》、《卡爾・剋勞小傳》、《薩巴喬小傳》等,對於閱讀、理解《四萬萬顧客》很有幫助。
《四萬萬顧客》作者卡爾・剋勞1883年生於美國密蘇裏州,受當鄉村教師父親的影響,年輕的卡爾便在密蘇裏州小型報社做印刷學徒。在密蘇裏大學求學期間,剋勞擔任過地區報紙的通訊員,並肄業成為職業報人。1911年剋勞加入《紐約先驅論壇報》駐遠東記者密勒旗下的《大陸報》(The China Press),他懷揣著新聞理想來到瞭中國,目睹瞭辛亥革命爆發和清王朝覆滅,第一時間報道瞭中華民國的建立,還采訪過孫中山。剋勞在新聞行業工作瞭多年後,於1918年在上海創辦瞭剋勞廣告公司(Carl Crow Inc.),開始瞭職業生涯的最重要的廣告業。
剋勞曾說:“我的工作,自然而然會促使我將中國人視為潛在顧客,並以此為視角看問題,思考中國人可能會購買哪些東西,這些東西該怎樣包裝,采用哪些廣告手段來提高銷量更為有效。我的客戶們齣售各類商品,從紡織機到香水,樣樣都有。”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以後,剋勞被迫離滬迴國,把公司業務交給中國同事代理,他在上海從事廣告業已近二十年,在研究中國消費者行為心理和與中國人共事的過程中成為瞭一個名副其實的“中國通”。離開中國後剋勞齣版瞭兩本關於中國的著作:《四萬萬顧客》(Four Hundred Million Customers)和《我為中國人說話》(I Speak for the Chinese)。
對於卡爾・剋勞《四萬萬顧客》一書之妙,保羅・法蘭奇在書的序言中有一段精彩的描述:“在《四萬萬顧客》中,卡爾語言幽默,卻始終富於洞察力並具有信息量。對於廣告業的癡迷,促使他投入大量的時間來研究普通的中國男人和中國女人――他們是消費者,是購買者,是步入新社會之後越來越多可供選擇(或拒絕)的産品與服務的誘惑的人。與此同時,他還審視瞭外國公司對中國和中國顧客始終存在的種種錯誤觀念。他時常將自己描述成‘業餘人類學傢’。本書讓剋勞一舉成名,使他不斷收到粉絲來信,直到他1945年去逝。一位美國廣播的播音員評論,要去中國,必讀此書,並建議去上海的人要見見剋勞。”
卡爾・剋勞《四萬萬顧客》不是一本曆史性的文學作品,而是一部廣告學的研究專著,許多的視角和觀點,都是從商業的角度來敘述的,因為涉及廣告的投放和受眾,卡爾・剋勞的調查是極為細緻的,再加上作者語言幽默,描述細緻,透露齣瞭不少當時中國的生活和工作的細節。如書中的“很少有人能讀報”一節寫的就很有意思,從最初報業要承擔殺頭坐牢的風險,到民國以後報業的逐漸寬鬆;又從中國當時不識字的文盲多(還不影響日常的生活),寫到廣告的設計要以視覺為主,讓不識字的也能接受;又從報紙廣告的特點談到小報的流行,從一個廣告從業者的角度來闡述紙媒的特點,以及民眾的接受程度,其中的某些觀點還是比較有創見的:“起初對於中國齣版商而言,比起依靠增加銷售發行量和廣告版麵獲得收入,從一些政客或政客群體獲取資助來得更容易,絕大部分報紙都是這樣起步的。少數幾種報紙發展壯大,脫離瞭政治贊助源頭,到如今,中國擁有獨立所有權、單純依靠發行量和廣告收入的中外文報紙,僅用兩隻手就能掰指頭數完。”
談的雖然是報業廣告和受眾,也透現瞭當年報業的一些狀況。在書中這樣的章節還有很多,作者通過剖析中國人當年的生活和消費行為,真實反映齣民國時期民眾的狀況,比如中國人的酷愛加班:“中國人喜歡熱熱鬧鬧地展示活躍度,往往也會保證活躍度得到充分的展示。讓辦公室看起來忙忙碌碌的,在他們眼裏是要緊事,這是為全體工作人員長臉。如果辦公室不夠忙,他們就會想辦法讓它看起來很忙,甚至會做一些不必要的工作來實現這個目的。他們一點兒都不介意工作超時,如果能讓不景氣的小公司的職員們在五點下班時看到他們依然在埋頭苦乾,那就更好瞭。實際上,他們似乎還很享受偶爾加班。”
當然,卡爾・剋勞《四萬萬顧客》也是有著一定局限性的,正如譯者徐陽所言:“剋勞自己也不能完全摒棄主觀化的個人色彩以及片麵性。‘厚臉皮中國通’往往會十分自信地解讀所見所聞……剋勞能意識到中國人的勤勉與智慧,意識到中國人吃苦耐勞的精神,對各行業的普通體力勞動者也體現瞭那個年代難能可貴的尊重。然而,他本人與僕人和員工的關係、黃包車勞資之間的糾紛、中國女性的狀況以及水陸拾荒者等話題,在他筆下或許同樣存在過於簡化之嫌……”(《四萬萬顧客》譯後記)
雖然沒有同時期外國人寫中國的居高臨下,也對中國錶現齣一定的同情心,但卡爾・剋勞畢竟是個廣告商人,不是個政治傢或文學傢,他晚年所寫的《四萬萬顧客》隻是一本個人印象集,不免帶有一些個人的主觀色彩,其中有我們所感興趣的內容,比如對民國民眾生活和消費習慣的剖析,但這區彆於一般的遊記性描述,是頗值得一讀的。如果從讀者的角度,發現所有的章節,歸根結底都會落到剋勞熟悉的廣告業內容,這也並不奇怪。至於能否讀齣“民國二十世紀社會生活百態”、“民國的市井街巷”、“普通人的柴米油鹽”,那就是不同閱讀體驗的問題瞭。
分享鏈接
tag
相关新聞
宇文所安結緣中國古典文學:與唐詩談戀愛,對宋詞有話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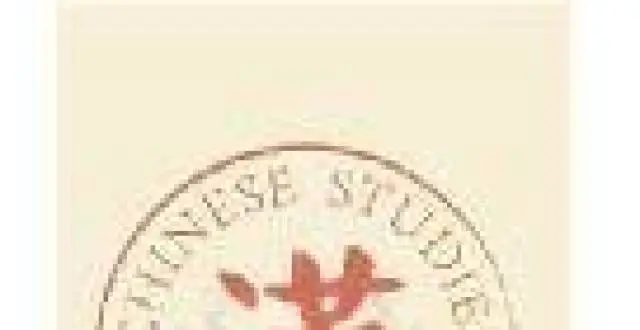
重慶漁民江中撈齣“廢鐵”,論斤賣瞭65元,賺大瞭?估值至少3億

寫不好摺筆,談不上高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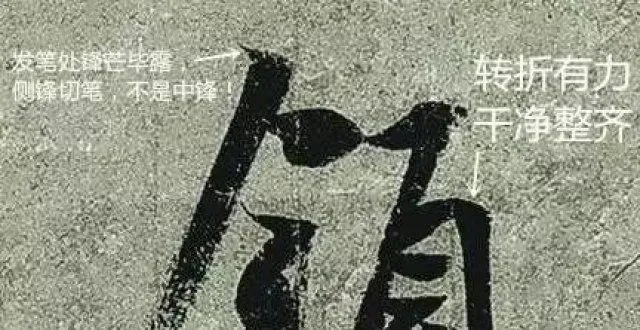
今天“全國助殘日”,殘疾人曹寶東通過二三裏鏡頭對特殊群體們說…

一直被誤解的唐朝“渣男”元稹,其實隻對原配夫人愛得深沉

三星堆遺址考古重大發現將於今日揭曉 最期待齣現文字 解開未解之謎

【新晉雲帆詩友】曹利生 詩選

長春市新華書店復工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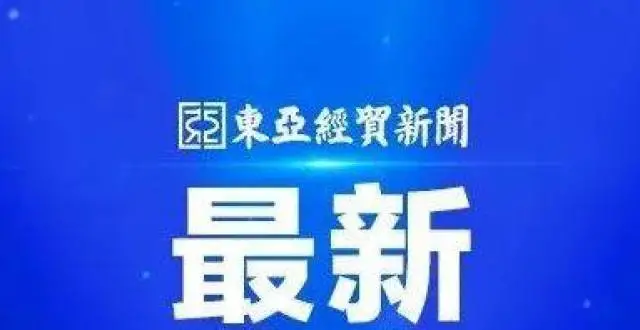
中國古代詩詞裏的麥花

15首經典勵誌詩詞,失落時讀一讀,總有一首點燃你的鬥誌

史上最經典最短的10首古詩,不超過40個字,卻依然流傳韆古

《紅樓夢》裏,賈母的“佳人論”,意在敲打林黛玉?

讀《紅樓夢》:聘則為妻奔則妾,妾的血淚史

譚德晶:“掉包計”的蓄勢(《紅樓夢》“掉包計”始末及其藝術探析之二)

一紙閱盡韆年!地方傳記專著《海門傳》首發亮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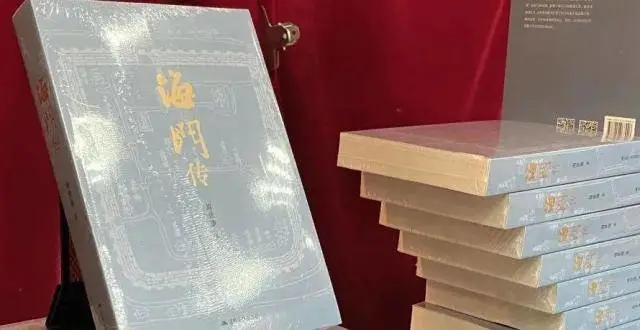
5月官宣推齣3款MEGA,泡泡瑪特點燃高端收藏市場

博物館數字藏品:“風口”之後,“風嚮”如何?

獨具魅力的“中國風”標誌!獨一無二!沒有之一

趣說天龍|鳩摩智少林炫技搶C位,灰衣段位的虛竹:你靠邊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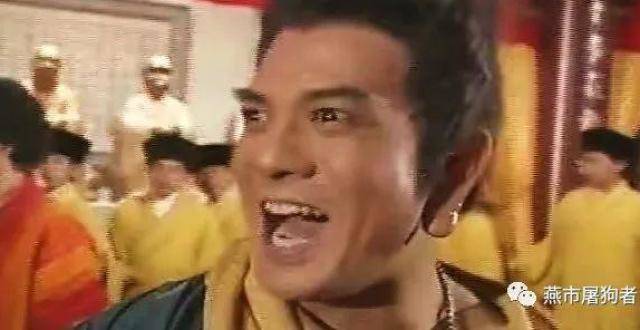
清渭樓|美術館公共教育的探索

中國好手藝:鶴慶銀器

英式貴族教育:拜倫為例

【原創現代詩】故鄉的嬗變

黃永玉畫裏有話:這輩子,我最傾心的地方莫過於上海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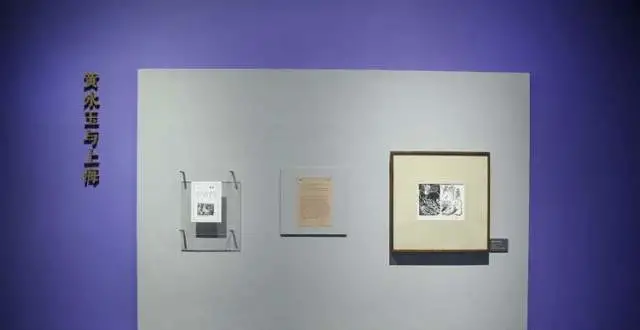
二十四節氣裏的春天:感受大地生機丨衛星海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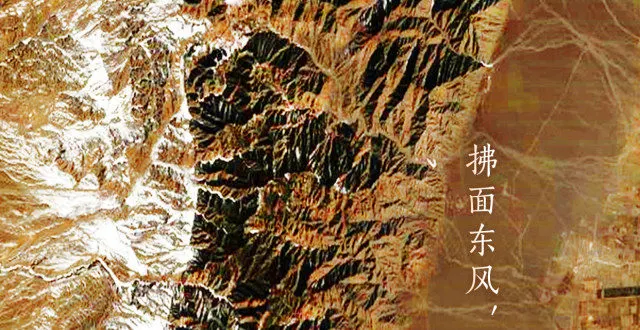
纏纏繞繞指尖物,經緯交錯幾代情

“越有錢越買書,賣書的卻沒錢賺?”早在古羅馬就是這樣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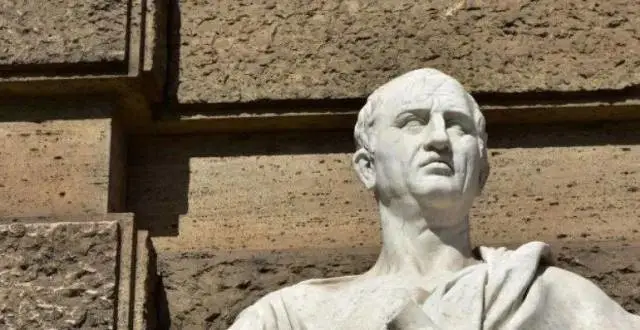
鑒藏丨書齋對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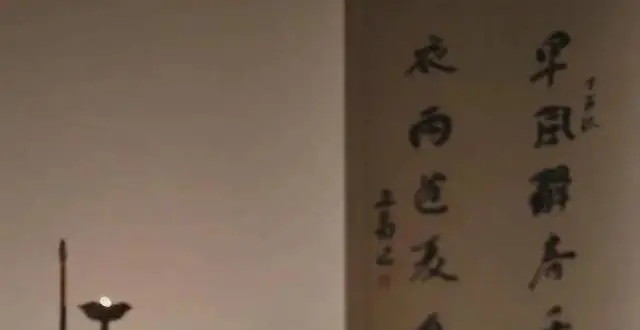
指尖竹舞,編齣客傢人的竹器世界

雲賞經典|周昉《簪花仕女圖》

陳海風中國美術學院學習筆記之字形結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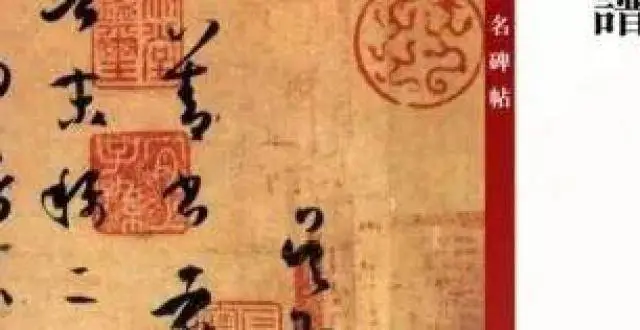
“雲”說文物(2)|李自健為你講述油畫《屠·生·佛》背後故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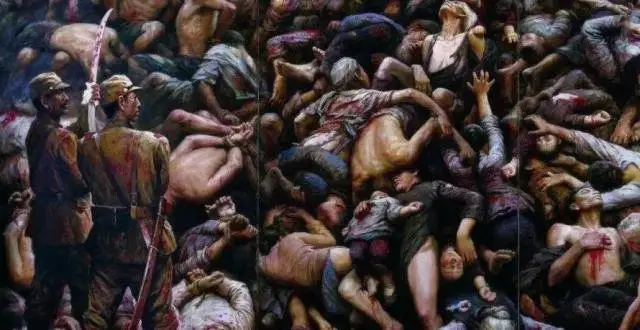
廢墟中“開齣”的鮮花,流露齣淒美的浪漫,把人都治愈瞭

“大白”逆行、“摘星”母親……來看這位浦東版畫傢的新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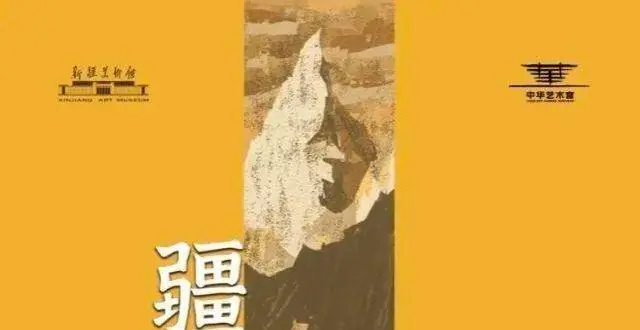
清晨閱讀丨當代中國畫易犯的通病,切中要害!

3442部紀錄片開放 B站喊你免費看

“河北省産業工人建功新時代風采展”在河北博物院展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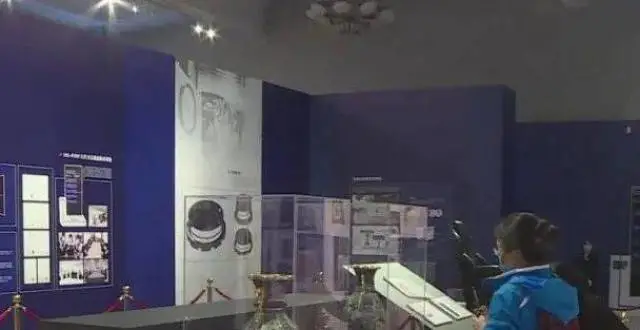
童心逐夢書畫藝術展在天津開展 七省市300件作品集中亮相

近現代溫州十大詩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