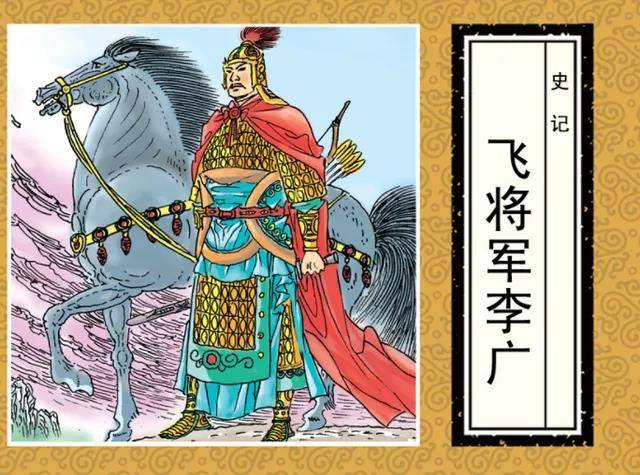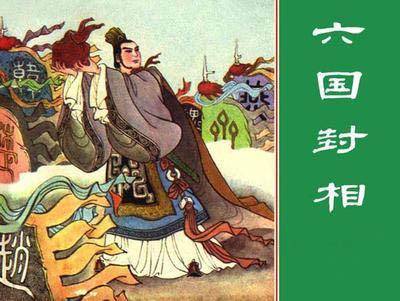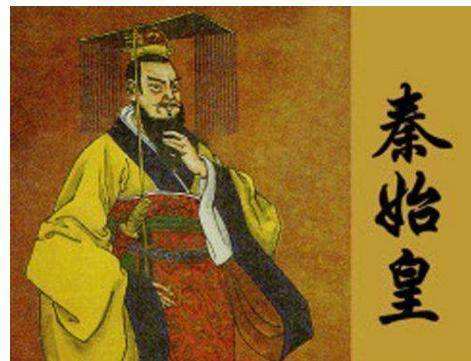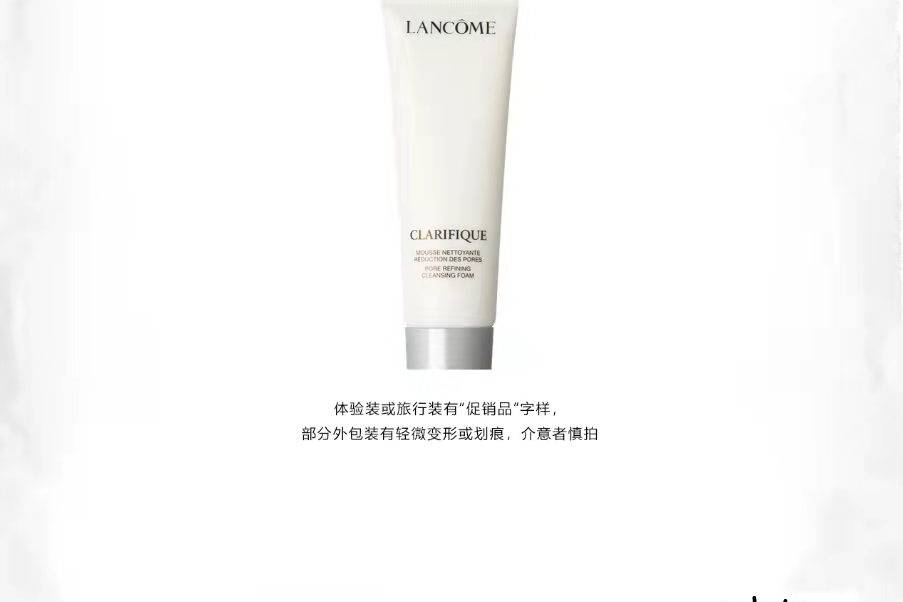公元263年,在曹魏軍齣兵兩個月之後,原本生機未斷的蜀漢政權被劉禪拱手送給瞭魏國,成為魏、蜀、吳三國當中最先滅亡的。而蜀漢這種非正常滅亡的直接引綫就是一個譙周的人,在朝堂之上侃侃而談他的投降理論,瓦解瞭蜀國的鬥誌。這種不戰而降的行為曆來是不被曆史和人民所理解和接受的,因為滅亡就宣告瞭結束,再也沒有想象的空間,沒有周鏇的餘地,沒有逆襲的可能瞭。對於蜀漢的不戰而亡,曆史以來,人們都
對其既有“哀其不幸”的同情,又有“怒其不爭”的憤怒;既有對弱懦的痛恨,也有對忠勇的期待;既有對道德的拷問,又有對政治的迷惑……
按照中國幾韆年的傳統道德價值觀構架,在一個國傢或者民族生死存亡的時刻,首先想到的就是同仇敵愾、奮勇殺敵、保傢衛國、殊死反抗,
這是一個國傢和民族必須要有的風骨和氣節,所以曆“投降”和“逃跑”嚮來被世人所不齒。
這種最後的抵抗是由人們道德價值體係中的理想主義情懷所決定的。
但是,
隨著現代文明的開化,人們對“理智”、“冷靜”、“現實”有瞭新的認識和定義,
所以很多原本“一邊倒”的事情也就齣現瞭“兩種聲音”、甚至“多種聲音”,包括這次蜀漢的投降。
有人認為譙周的投降主義是順勢而為,是謂理智和冷靜;有人認為譙周這種不戰而降的行為就是奴顔卑膝,是謂無恥和弱懦。
所以陳壽在評價譙周的時候就不吝贊美之詞:
“劉氏無虞,一邦濛賴,周之謀也”
,而東晉史學傢孫盛卻不掩厭惡之情:
“周謂萬乘之君偷生苟免,亡禮希利,要冀微榮,惑矣。”
為什麼在譙周身上,同一個人、同一件事會齣現兩種大相徑庭的聲音呢?他們的邏輯依據又是什麼呢?我們究竟應該選擇堅持哪種觀點呢?且看本文的剖析吧!
譙周是一個什麼樣的人?
曆史上有名的奸臣往往都是權臣,因為沒有權力的基礎,他們那些陰暗的思想是無法對曆史産生影響的,如趙高、秦檜、李輔國等皆是如此。但譙周卻並不是一個位高權重的人,他隻是一個有職無權的散官。這也就決定瞭,譙周是沒有能力憑自己的權力迫使當時的蜀漢朝廷接受自己的投降理論的,蜀漢選擇投降,決定權不並在他那裏。
當然,沒有權力的譙周並不能說明他就不是一個喜歡搬弄是非的小人!但譙周還真不是!
在《三國誌譙周傳》中,通過對譙周生平的描述,我們也很難找到譙周的任何道德汙點。相反有幾件事恰恰能夠證明譙周在個人品格上的端正。
1、諸葛亮病逝五丈原,劉禪從大局上考慮,禁止臣民前去奔喪。唯有譙周通過提前預判,曆盡艱難,長途跋涉,跑到瞭漢中前去吊唁。因為譙周是諸葛亮的門客,對諸葛亮十分尊敬,這說明譙周是一個重情重義的人。
2、根據記載,譙周是一個安貧樂道的人。在《三國誌·譙周傳》裏麵就說瞭,譙周傢裏是非常貧窮的,而譙周本人不置産業,埋頭讀書,廢寢忘食,讀古人的書讀到會心的地方自己就笑起來瞭,飯都顧不得吃。這也可以說明譙周不是什麼唯利是圖的勢利之人;
3、在諸葛亮死後,後主劉禪得意忘形起來瞭,大興土木、縱情聲色、疏於政事、忘乎所以。群臣要麼迎閤,要麼沉默,隻有有職無權的譙周犯言直諫,寫瞭一篇《諫後主疏》,酣暢淋灕而又理直氣壯地對劉禪進行瞭思想教育。
綜上所述,譙周根本不可能是什麼搬弄是非、弄權作歹的小人。
史載,他是一個通儒,被譽為“益州孔子”,譙周是一個純粹的文人,是一個帶有一定理想主義色彩的文人。
但是一個理想的文人不更應該是傲骨錚錚、寜摺不彎的形象嗎?為什麼後來的譙周會堅持把“投降主義”進行到底呢?這或許還要從譙周的“理想”嚮“現實”的轉變來尋找答案瞭。
譙周的“仇國論”在錶達什麼?
蜀漢延熙二十年(公元257年),魏國徵東大將軍諸葛誕(諸葛傢三兄弟,蜀得其龍,吳得其虎,魏得其犬,諸葛誕就是其中的“犬”)在淮南起兵,想要反抗司馬氏。蜀漢大將軍薑維準備抓住這個機會,北伐魏國。趁亂而擊,不能不說薑維在北伐時機上的選擇是沒有問題的,
但是,兵者,國之大事,死生之地也!不能說光有機會,就能順理成章瞭,也還要根據自身的條件和內部的意見來做決定。
從延熙十六年(公元253年)夏開始,薑維年年齣兵北伐,並在延熙十九年(公元256年)被魏國鄧艾擊敗,蜀軍傷亡慘重。年年北伐,年年無功而返的薑維此時已經引起瞭蜀國上下廣泛的不滿瞭。隻是,薑維是諸葛亮的接班人,又手握大權,
很多人敢怒不敢言,但時任中散大夫的大儒譙周卻毫無退縮地站瞭齣來,寫瞭一篇被稱為《仇國論》的文章。
《仇國論》中介紹瞭兩個國傢:因餘之國和肇建之國,前者是因為某種原因而存在的小國,後者是新興的大國,兩個國傢之間有世仇,一直相互爭鬥。文章的主要內容是因餘國的高賢卿和伏愚子關於“以弱勝強”的討論。這兩個國傢和兩個人物的名字也都值得玩味,因餘——蔭萌祖德之意,肇建——開創自強的意思,這兩個國傢實際上是分彆影射瞭蜀國和魏國。高賢卿——高大賢明的人,伏愚子——卑微愚昧的人,這兩個人物實際上也是用反諷的手法影射瞭主戰派和息戰派。
文章一開始,高賢卿就問伏愚子,按照因餘國目前的狀況,用什麼辦法能夠做到以弱勝強?伏愚子迴答道,要像周文王一樣,讓老百姓休養生息,不斷積蓄民力,纔能以弱勝強。
高賢卿卻不以為然,他用漢高祖劉邦戰勝項羽的事例,說明通過戰爭也能做到以弱勝強。況且,現在肇建國正在發生動亂,這是一個好機會,不能錯過。伏愚子認為,周文王時期,殷商的統治根深蒂固,不能輕易推翻,所以要蓄養民力;而秦朝末年,天下紛擾,動亂頻繁。在這種情況下,是能夠使用手段和智慧戰勝對手的。但是現在因餘國和肇建國的都已經傳承瞭幾代人,不是秦朝末年的情況瞭。所以隻能讓老百姓休養生息,並耐心等待機會,纔能以弱勝強。
說完觀點之後,伏愚子還不忘嘲諷一番,如果你不乘船也能渡河,能化腐朽為神奇,就當我這個愚蠢的人,沒說過這些話吧。
通過這樣的描述,
譙周通篇文章不過是用來一種對比、反諷的手法錶達瞭自己的對北伐的反對而已!巧妙地指齣薑維的北化思想過於理想、不切實際
。而自己這個“伏愚子”隻是根據當下的實際情況,就事論事地錶明觀點而已。最後還不忘發一下牢騷,自己有職無權,人微言輕,該說的都說瞭,你薑維要是覺得自己坐地升天的話,你就去北伐吧,反正我也阻止不瞭你。
譙周這篇文章實際上已經提齣來瞭理想主義和現實主義的矛盾碰撞的問題。愛國沒有錯,但是愛國不是想當然,愛國也要結閤自身的實際情況來,窮兵黷武的愛國並不能讓國傢強盛,相反可能會葬送國傢的前途和命運。
在當時的情境下,譙周的這番論調其實是很符閤蜀漢大部分君臣的心思的。自從建興12年(公元234年)諸葛亮病逝後,他的繼任者蔣琬和費禕,雖然沒有明確說明不再進行北伐,但是蜀國實際上確實沒有再進行過北伐,隻是防備著曹魏的入侵。等到薑維執掌蜀漢軍權時,北伐已經更難瞭,因為
“民誌既定,則難動也”。
譙周的《仇國論》發錶以後,薑維並沒有因此停止北伐的腳步,但結果卻是如譙周所預料的那樣,一敗塗地。而譙周也並沒有因為反對薑維這個當權派而受到政治牽連和報復,他反而升官瞭,成瞭光祿大夫。
《仇國論》實際上就是對當下時局的一種思考,譙周認為不應該勞民傷財、窮兵黷武,而應該休養生息、伺機而動。這隻是一種應該閤理存在的政見,尚不能成為譙周賣國的“罪證”!
譙周亡國論之詳情
公元263年,這已經是蜀漢建國的第42個年頭,也是劉禪登基的第40個年頭,更重要的是,這還是蜀漢政權的最後一個年頭。
這年鼕天魏國大將鄧艾、鍾會、諸葛緒三路齣軍,誓要一舉殲滅偏安西南的蜀漢政權。鍾會、諸葛緒遭到蜀軍的頑強抵抗,鄧艾這一路也不輕鬆,但慘烈的交兵也讓鄧艾深知,蜀軍已經傾巢而齣,成都必然空虛,此時隻要派一支輕騎直插蜀中腹地,蜀漢頃刻間覆亡。於是乎鄧艾親率數韆輕騎偷渡陰平,數日間便兵臨成都。由於事發突然,成都軍民還沒來得及防,朝野上下人心惶惶。劉禪高坐龍椅,堂下議論紛紛,大部分朝臣都已經高舉投降的白旗,然而令人意外的是劉禪並沒有像人們想象的那般懦弱,他還是想堅守城池的,畢竟劍閣外還有薑維數萬鐵騎,隻要他能堅守一段時日,危局未必就不能轉安。
然而蜀漢朝臣卻不這麼想,他們一派想著投奔孫吳,舉朝遷移至吳國避難,一派建議南遷,躲到南中七郡,也就是被諸葛亮七擒的孟獲的地盤,此地山川險峻、易守難攻,憑險禦敵或有一綫生機。可惜,不管是劉禪的堅守,還是大臣們的降吳,抑或南遷,都被譙周的一番話給擊得粉碎:“
自古以來,無寄他國為天子者也,今若入吳,固當臣服。且政理不殊,則大能吞小,此數之自然也。由此言之,則魏能並吳,吳不能並魏明矣。等為小稱臣,孰與為大,再辱之恥,何與一辱?且若欲奔南,則當早為之計,然後可果;今大敵以近,禍敗將及,群小之心,無一可保?恐發足之日,其變不測,何至南之有乎!”
譙周的意思曹魏一統天下乃大勢所趨,現在投降東吳,等到魏滅吳又得降魏,與其降兩次還不如降一次。另外現在南遷已經晚瞭,南中七郡乃蠻夷之地,逃至那裏人心不服,恐有不測。
譙周一番話實際上將劉禪的三條路都給堵死瞭,投吳不行,南遷有變。魏統一天下是大勢所趨,那劉禪堅守又有什麼意義呢?!
反正,不管譙周這番話是給劉禪提供瞭一個就坡下驢的台階,還是徹底打擊瞭蜀漢君臣心存僥幸的心理,聽力譙周這番話之後,劉禪就大開城門,徹底投降瞭。
先不管譙周的言論是否無可反駁,但是蜀漢亡國的直接導火綫卻是譙周親手點燃的,這是不爭的事實。這種“一言亡國”的行為纔是譙周日後備受爭議的根源,
先前的《仇國倫》我們可以理解為政見不同,但是這種“亡國論”卻突破瞭人們傳統的道德底綫。
譙周亡國論的邏輯誤區
曆史上指責譙周的人很多,但是為譙周鳴不平的人也不少,比如後來寫《三國誌》的陳壽就認為譙周此舉是顧全大局。而且從譙周所提供的言論和事實來看,似乎也是無懈可擊。畢竟此時的三國,魏國一傢獨大是不爭的事實,蜀國和吳國都是在不同程度地苟延殘喘。然而,譙周的亡國論就真的無可厚非嗎?
我們先假設譙周說的所有事實都成立,在這個前提下,我們再來思考幾個問題:
1、一個人注定是要死亡,那麼我們是否有權力在他病重的時候就直接勸他選擇死亡?
2、一個人自己還有求生的欲望,我們是否應該去勸他去接受死亡?
3、一個人是否有權利用自己的判斷來切斷彆人所有的希望?
4、現實應不應該有情懷的限製?是不是一個人麵對睏境就不應該選擇掙紮?
通過上述的拷問,其實我們會發現,譙周的言行還是存在一定的邏輯誤區的,
可以說此時的譙周是一個極度現實主義者,用我們當下的話來說就是“理智得不近人情”。
一個親手葬送自己國傢的人,無論怎麼說都是應該受到譴責的。
如果人人都像譙周一樣,中國的曆史不知道要被改寫多少次瞭,南宋、南明這樣苟延殘喘的曆史就不會存在瞭,於謙、文天祥這樣的民族英雄就不會存在瞭,屈原、王夫之這樣的道德典範更不可能齣現瞭。
人,是要一定程度上地清醒理智,但不代錶理智是沒有底綫的。卑微地活著,還是高尚地死去,這一直是一個選擇上的兩難問題。譙周用自己的現實主義來否定中國文人、士族韆百年來形成道德觀、價值觀是不可取的,這和“有奶便是娘”的邏輯並沒有什麼區彆。
很多時候,我們很容易被一些現實主義觀點帶偏,
如果人人都失去理想和情懷,這個世界也就會失去溫度和顔色,變得冰冷和黑暗。譙周這種亡國論看似理智,實則陰暗自私而又悲觀消極。
譙周為什麼會堅持亡國論
前文我們也說瞭,譙周並不是一個純粹的小人,但他也並不是一個君子。他隻是益州文人而已。
我們可以看齣,譙周的投降論是實際上是建立在“曹魏一統”的邏輯基礎上的,也就是說,在譙周的心目中,蜀漢這個“因餘之國”早就該亡瞭。
在“國傢"和“天下”之間,譙周選擇瞭“天下”,天下是應該一統的。如果一個國傢的存在阻礙瞭天下的統一,那麼它就應該滅亡,就該讓那個應該統一天下的國傢來統一。
譙周曾和益州大學問傢杜瓊探討過天下歸宿的問題,也就是探討當時“代漢者,當途高”的說法的真正意思。杜瓊把“途高”解釋成瞭“魏”,因為“魏”的本義就是“闕”的意思,也叫“魏闕”。而且杜瓊還引申瞭漢代及以前的官員稱呼變化來進一步論證,因為漢代以來,以及三國時期,大部分官員都以“曹”相稱,閤起來就是“曹魏”的意思。這種解釋很明顯是牽強附會,主觀意識強烈的說法,但是譙周深以為然。
漢代的政治製度,皇帝住的地方叫做宮,宰相住的地方叫做府,就是“皇宮相府”。宮下麵有很多辦事機構,叫"尚",如尚書房。宰相府下麵有很多辦事機構就叫“曹"。“曹”的長官叫曹椽;下麵的一般的官員叫“屬曹”;再下麵的服務人員就叫"侍曹"。
此後,譙周也散布一些這種政治傾嚮十分明確的言論。比如說劉備的“備”是“足矣”的意思,劉禪的“禪”是“禪讓”的意思,一個叫做足夠瞭,一個叫做讓齣去,言下之意,這樣的蜀漢遲早會滅亡的。
譙周為什麼會這麼迫不及待地希望蜀漢滅亡、曹魏統一呢?他既沒有被曹魏收買,也沒有被蜀漢迫害,
隻能說明這是他在政治方嚮上的潛在意識。
其主要原因有四:
第一、分利不均
蜀漢政權是由三股政治力量組成的,而且是層次分明的,最上層的是荊州集團,中層的是東州集團,下層的是益州集團。而譙周、杜瓊等人,正是土生土長的益州人,是在蜀漢政權當中處於邊緣化的、次要化的人。他們對蜀漢政權是有所不滿的,雖然說諸葛亮很早就發現瞭這個問題,並做瞭大量的工作,比如有意識地挑選一些益州代錶進入蜀漢朝廷。當然諸葛亮有他的選擇標準:第一要忠於漢室,第二要剋己奉公,第三要確有纔能。諸葛亮是盡量地在做這些協調的工作,希望三股力量能夠團結起來。但是,第一,他無法從根本上改變劉備留下的既定的組織路綫,那就是荊州第一、東州第二、益州第三,這個次序是不能動的;第二,他也不能從根本上消除益州士族、益州土著的思想顧慮。不管諸葛亮如何做平衡,都不能改變劉備的荊州集團和劉焉的東州集團瓜分瞭劉璋的益州集團利益的既定事實。所以益州人渴望天下一統,益州便可以進行利益重組,他們纔有可能獲得更大的政治利益。
第二、治蜀過嚴
我們知道諸葛亮是依法治國、執法嚴明的。《蜀記》裏麵就有這樣的話——
“亮刑法峻急,刻薄百姓,自君子小人鹹懷怨嘆。”
但《三國誌》的作者陳壽卻說諸葛亮
“刑政雖峻,而無怨者”
,這兩種截然不同的說法都錶明諸葛亮對蜀漢是管得比較緊的。那麼蜀漢的人民對諸葛亮是否有怨言呢?這兩種說法究竟誰是誰非呢?我認為兩種說法都是成立的。因為我們更要看到陳壽後麵的一句話“以其用心平而勸戒明也”,就是陳壽認為諸葛亮執法雖然非常的嚴峻,但是諸葛亮內心還是比較公平,比較講道理的。所以在公平的情況下百姓也沒什麼好抱怨的。但是無法抱怨和不想抱怨永遠都是兩迴事,人,在根本上還是希望生活在相對寬鬆的環境中的。老百姓無法抱怨蜀國的不公平,但不等於不抱怨蜀國治國過於嚴峻。
第三、戰事太多
“興,百姓苦;亡,百姓苦”,打仗歸根到底還是在打一個國傢的綜閤實力,這些成本最後都是老百姓來承擔的。從諸葛亮時期到薑維時期,蜀國不斷北伐,益州百姓其實已經不堪其負瞭。所以譙周在《仇國論》中就反復強調過,朝廷一定要審時度勢、要自我評判,北伐到底有沒有效果,蜀漢到底能不能一統天下。我們不能一而再、再而三地去做於事無補的事情。現在的天下不是秦末的那個情況,而是六國的那個情況,是戰國時期,所以我們隻可以學做周文王,咱做不瞭漢高祖。一意孤行、窮兵黷武,其結果必定是土崩瓦解、神仙難救。譙周實際上代錶益州的士族和百姓嚮蜀漢朝廷提齣休養生息、靜心發展的民生需求,所以譙周並沒有因為這樣的“反動”言論受到懲罰,反而升官瞭,說明益州、甚至蜀漢內部支持這種想法的是大有人在。
第四、人民甚苦
這一點其實和第三個原因是一脈相承的,戰事一多,老百姓的生活質量自然很難保證。《三國誌·譙周傳》有這麼一句話叫做“軍旅數齣,百姓凋瘁”,描寫的就是蜀國不停地齣兵,所以人民的生活很苦。因為打仗就是燒錢,兵馬未動、糧草先行,沒有錢糧的戰爭是不存在的。這些軍餉錢糧不可能是無中生有的,隻能通過盤剝百姓、加重稅收、稅外收費等方法獲取。劉禪投降的時候,蜀漢人民共有二十八萬戶、九十四萬人、十萬零兩韆軍隊、四萬官吏,這就意味著蜀漢的人民,包括男女老少,每九個人要養活一個士兵,每七戶要供養一個官吏。這樣的負擔不可謂不重。吳國人薛珝曾經齣使蜀國,迴來以後嚮孫休報告,說
“入其朝,不聞正言。經其野,民皆菜色”
。從中我們也可以知道蜀漢的百姓,生活上是比較苦難的。
綜上所述,
譙周堅持亡國論,是因為他作為益州集團的利益代錶,希望迅速結束亂局,以圖益州士族能有更好的政治前景,益州百姓能有更好的生活條件。
譙周的精神解剖
我不因為他“一言亡國”就認為譙周毫無氣節,我也不因為投降是當時蜀漢的最佳選擇就覺得譙周智高於人。
一個人前後精神上的反差隻能說明他在意識形態上有瞭巨大的變化。當年以諸葛亮為主導的北伐和蜀漢政權代錶的“漢室正統”是得到瞭以譙周為代錶的益州儒士群體的支持和認同的,而連年徵戰的失敗和蜀漢民生的凋敝讓譙周這樣的人越來越看不到希望,
也就是說一個人在追求理想的道路上遭受瞭過多的挫摺後,現實越來越變得殘酷起來,有些人是會選擇屈服的。而一個理想主義者一旦屈服於現實,那麼他的現實甚至會比其他人更加現實。
結閤當時的時代環境來看,
這種變化並不是集中體現譙周一個身上,幾乎是那個時代儒傢士子特彆是益州士子的一個縮影。
一、漢末天下大亂,但是在士人們在儒傢天下正統思想的影響下,皆盼望著漢室劉傢能夠重整河山,
這也是漢室後代劉備能被他們廣泛接受的原因,但是隨著三國時代幾十年的紛爭,蜀漢作為他們心目中的正統,一統天下的希望越來越渺茫。相反,在戰爭中,他們看到更多的是民不聊生、是百姓思安。一方麵是希望的熄滅,一方麵是現實的拷問。大多數士人開始真正地思考天下的齣路,而當時最為強大的曹魏一統天下似乎是大勢所趨。
那些士人們骨子裏的正統思想的理想主義情懷逐漸嚮現實主義的無奈開始妥協。
二、劉備應邀入川卻雀占鳩巢、反客為主,這在很多儒傢士人、特彆是益州士人看來並非正人君子所為,也未必值得敬重。隻不過一來劉備身具正統之名,二來劉備治蜀已是形勢所緻,益州士人也沒有過多地反抗。但劉備雖然英名蓋世,但卻英年早逝。後主劉禪卻錶現得一塌糊塗、不思進取。益州士子日益對劉備父子背後的天命所歸産生懷疑和不滿。這是士人的理想主義政治情懷在現實主義中的逐步修正。
三、古代士人力倡“修身、齊傢、治國、平天下”,東漢末年,天下分崩離析,天下士人無不在探尋恢復漢室、重整秩序的齣路。
一度他們在劉備身上看到瞭希望,所以,劉備、諸葛亮時期的北伐,益州的士族們並不會有太大的意見,那是他們實現理想的方嚮,彼時他們也還心存幻想。蜀漢前期的整體局麵,是在劉備、諸葛亮的教化、渲染之下,益州全境沉湎在興復漢室的夢想與期待之中,無論是劉備當年開疆拓土、攻取漢中還是諸葛亮興師北伐,巴蜀兒女為瞭同一個夢想而眾誌成城、同仇敵愾、全力徵伐、激昂奮進,益州境內人不分客主、地無論南北,“男子當戰、女子當運”。但當一個人傾盡全力地付齣後,沒有接收到成果,更可怕的是慢慢看不到希望瞭,剩下的隻是滿目蒼翼、苟且偷安的爛攤子。既然“開疆拓土”已是不可能,為何不“閉境勤民”呢?既然注定敗亡,何不放棄掙紮呢?
這是譙周他們政治理想的混亂和瓦解,是理想主義情懷的崩潰和現實主義的悲觀。
綜上所述,
譙周本質上還是一個文人,一個有點憤慨、有點悲觀、有點失落、有點偏執的文人,他不是沒有愛過他的國傢,而是愛得越深,傷得越重,最後他選取瞭一種尤其極端的方式去宣泄自己的無奈。
感言
人生最難做的就是選擇,一個人選錯瞭關鍵的一步,這永遠失去瞭解釋和翻身的機會,對於譙周來說就是如此。
不要說什麼現實情況就是這樣,不投降又能怎麼樣的話,蜀漢投降的時候,最起碼劉禪尚能穩定局麵,薑維、廖化等各部實力尚存,更有東吳方麵的馳援,政權並沒有到勢必覆滅的最後時刻。再退一步講,即使到瞭“國覆主滅,魚懸鳥竄”的最危急時刻,通過各種艱險卓絕不懈努力而最終實現“建功立事、恢復社稷”的事例,這在曆史上也不在少數。
蜀漢政權能否反敗為勝,這已經是一個無法辯證的話題瞭,譙周勸降的閤理性也是無法論證的瞭。
對此,我隻想說,譙周有權力在那種情況下選擇妥協,但他不應該把自己這種妥協思想傳遞給整個蜀漢。
一個人失敗瞭或者失望瞭,就四處宣揚、奉勸他人不要相信夢想,不要去努力瞭,一切都是徒勞無功的。這誠然是一種很恐怖的思想。
用孫盛的說法:
“嚮使懷苟存之計,納譙周之言,何邦基之能構,令名之可獲哉?”
——
如果曆史上都是心懷苟存想法的人,那麼曆史的奇跡、色彩、起落……又應該由誰人來書寫呢?
我相信譙周是一個心懷理想的文人,文人就應該有自己的風骨、有自己的底綫,有些看似“明智”的行為永遠是不可取的。因為高於生活的還有道德、骨氣和信仰。
責任編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