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曆史上 沒有什麼事件是必然發生的。如果有 安史之亂必然會發生嗎?是一場帝國雪崩,但帝國未必非要死於雪崩 - 趣味新聞網

發表日期 2/24/2022, 6:05:36 AM
曆史上,沒有什麼事件是必然發生的。
如果有,那隻能是某種趨勢或某種問題。但安史之亂是事件,而且是突然爆發的大事件。幾乎整個大唐帝國的精英,都沒想到這件事會發生。
所以,安史之亂,相當於一場雪崩。
山頂上的雪花越堆越厚。恰在此時,一個叫安祿山的人,大喊瞭一聲,然後雪崩爆發。但是,你要說沒有安祿山喊那麼一嗓子,雪崩也會必然發生,這就是扯淡瞭。
唐玄宗在公元712年登基,在公元756年被尊為太上皇。整個玄宗朝持續瞭45年。在這45年間,大唐進入瞭盛世,但日中則移。在玄宗朝後期,大唐也進入瞭中期。
曆代王朝的中期,總要遭遇財政問題。具體就是開支越來越大、收入不見增長,於是收不抵支。簡單說,就兩個字:缺錢。
在玄宗朝的後期,不可避免地遇到瞭缺錢的問題。缺錢,既是問題也是趨勢。而且,這個問題將會越來越嚴重、這個趨勢也會越來越加重。
為瞭解決缺錢的問題,玄宗朝主要做瞭兩方麵的努力。
一個是以緣邊節度使代替府兵製。
以前,大唐是義務兵役製,寓兵於民。老百姓當兵打仗不僅是義務,而且還要自備武器、自備戰馬。但是,當兵打仗也是有好處的。一個好處是會有策勛和賞賜,國傢不僅給你名而且還會給你錢。如“策勛十二轉,賞賜百韆強”。另一個好處是打瞭勝仗能分到戰利品。這個激勵作用很強,因為打仗等同創業。
但是,中期的問題是均田製瓦解瞭。寓兵於農而兵農一體,但沒有均田的府兵,怎麼可能再為國傢打仗?同時,戰爭的慘烈程度也發生瞭變化。之前,無論是打吐榖渾、打東突厥還是打西域諸國,統統都是短時間、高烈度的掃蕩戰役。打完仗就分錢,分完錢就迴傢。後期,主要是跟吐蕃帝國,對外戰爭成瞭漢匈大戰。烈度還是那個烈度,甚至更烈,但戰役變成瞭戰爭,成年纍月地打。
或從十五北防河,便至四十西營田。去時裏正與裹頭,歸來頭白還戍邊。
你這麼玩,普遍義務兵役製的府兵就沒法玩。於是,隻能以長徵健兒取代府兵。長徵健兒是什麼?是職業兵。打仗就是職業。既然是職業,國傢就要開工資。所以,最後還是一個錢的問題。而大唐早就遭遇財政問題瞭。這個工資就開不齣來。那怎麼辦?節度使就齣現瞭。國傢不管瞭,你們節度使自己帶兵、自己養兵。
天寶年間,大唐的十個緣邊節度使,可不是十個戰區或十個軍區,而是十個“軍事王國”。特彆是,安祿山這個範陽節度使,範陽軍雄冠八鎮之首(主要指北方的八個),清河糧倉號天下北庫。兵製問題到財政問題,然後就成瞭政治問題。但政治問題還要更嚴重。
一個是以聚斂集團取代賢相集團。
大唐的財政設計,從開國之初,就是先天畸形。政府收稅、百姓交稅,然後政府拿著稅收養官、養兵,提供最基本的公共服務。這是正途。但大唐的這個正途就沒法走。簡單說,就是百姓交不瞭多少稅,而這些稅養不瞭官、也養不瞭兵,更維持不瞭國傢行政。
原因之一是大唐的革命不徹底。李唐代隋、統一天下,也就用瞭八年時間。所以,大唐是妥協的産物。關隴貴族和山東豪族,大唐都得罪不起。所以,你這個稅就沒法像隋朝那麼收。(PS:隋朝是不允許偷稅和逃稅的,這是曆代王朝都做不到的)
原因之二是李淵和李世民這兩個皇帝,搗糨糊瞭。既然稅收不上來,那就不給錢給政策。養兵的問題,好解決,府兵製就行瞭,讓士兵自己養活自己。養官的問題,給你一塊土地叫職分田,官員當地主、收租子,自己養活自己。辦公經費的問題,又給地又給錢,地用來收田租、錢用來放貸。這就是大唐的財政邏輯。後期搞節度使,就是按照這個邏輯玩齣來的,不給錢但我給政策啊,給你一個州夠不夠,不夠就給兩個。
所以,唐朝財政的問題就非常大。那怎麼解決呢?兩夥人就掐瞭起來,一夥人是文學士大夫,即賢相集團,主張節流,沒錢就省著點花;一夥人是各種職業搞錢的官員,即賦斂集團,主張開源,沒錢就去找錢。
這兩夥人到底誰能獲勝呢?既取決於誰能解決問題,又取決於皇帝想讓誰嬴,但主要是後者。錢多不紮手。所以,取勝的肯定是聚斂集團。但,聚斂集團搞錢可以,搞鬥爭也可以。於是,大唐的政風就開始敗壞瞭。
王朝初立,百廢待興。這就相當於剛剛經曆瞭一場經濟危機。經濟被打到榖底。所以,這時候你怎麼玩,經濟都會好轉。政府呢?政府是真沒錢,所以想摺騰也摺騰不起來。而經濟好轉,政府財政也會好轉,然後政府和百姓一起攢錢。
王朝盛世,百業俱興。經濟從榖底往上走,政府還勒緊褲腰帶過日子。所以,進入盛世是大概率事件。但到瞭盛世之後,就遭遇問題瞭。漢武帝主動齣擊,非要弄死匈奴。而唐朝呢?唐朝就沒閑著,一直在開疆拓土。所以,盛世大唐一定會遭遇邊際效益遞減的問題。最彪悍的時候,大唐都設置波斯都護府瞭。你就說要花多少錢吧?所以,盛世就是一個開支很大、收入也很大,但兩相抵消而勉強維持的時期。
一旦王朝進入中期,就一定會遭遇問題,即收不抵支。這就是大雪壓青鬆但青鬆真心挺不直瞭。這是問題,但也是趨勢。所以,大唐在開元盛世之後一定會日中則移。不僅大唐如此,曆代王朝都是如此。
但安史之亂就一定要發生嗎?肯定要有觸發機製。這個觸發機製就是雪山山頂上那些個最容易鬆動的雪。沒有震動,它們好好呆著,甚至會從鬆動變得堅實。發展和時間都能解決問題。然而,但凡有人在山間喊瞭一嗓子,那這些雪就要滾落下來,而且還要帶著整座雪山一起崩塌。
當時,最容易鬆動的那幾片雪是什麼呢?
公元746年到748年,李林甫搞瞭一場大清洗運動。李林甫這個人是忠是奸,都是道德評價。換一種說法就是價值判斷,這個不好評。
現在有很多文章,在給既有定論的暴君奸臣洗地翻案。原因是道德評價的標準變瞭。在古代,是暴君還是明君、是忠臣還是奸臣,評價標準就是儒傢意識形態。在現代,評價標準就花樣百齣瞭,理性主義的、功利主義的、浪漫主義的,等等。到底怎麼評價,你喜歡就好,各種武器都給你準備好瞭。
從結果溯因地看,李林甫最大的問題是把政治鬥爭給白熱化瞭。以前權場落敗,那就離開廟堂而處江湖之遠,做個節度使也不錯。以後權場落敗,那就真得死無葬身之地瞭。這個開端就是從李林甫開始的,具體就是公元746年到748年,李林甫對太子一黨瘋狂屠戮。
李林甫死後,繼任者楊國忠,也是標準的聚斂集團。這類人,為皇帝搞錢沒問題。楊國忠是相當能乾的。但是,指望他們引領帝國政風,搞精神文明建設,就不可能瞭。楊國忠跟李林甫一個德性,跟太子死磕到底,嚮玄宗皇帝錶忠心。
為啥兩個宰相都要死磕太子,太子得罪誰瞭?
跟太子沒關係,跟玄宗也沒關係,問題就是老皇帝和狀太子的關係結構。這個結構天然就不穩定,也沒法穩定。宰相都是玄宗任命的,玄宗任命的宰相隻能一邊倒地跟著玄宗,那就隻能乾太子。
但是,乾太子還是宮廷鬥爭。大不瞭再來一場宮廷流血或長安大清洗。朝堂夠不夠大,夠大瞭;朝堂不夠,整個長安夠不夠,那也太大瞭。漢武帝與太子劉據兵戎相見,也就在長安城裏麵摺騰。
但是,楊國忠卻非要摺騰安祿山。李林甫在,安祿山這個大老粗就隻有猥瑣發育的份兒。大唐宗室、皇帝信任,再加為相十餘年,李林甫這個威望就能壓死安祿山。但是,楊國忠就不行瞭。安祿山死活也瞧不上他。
這個世界是講理的,但這個世界的人肯定是不講理的。
如果講理,那就應該是從思維到觀點的流程。大傢低頭走流程:以立場為齣發,以事實為根據,然後提齣觀點,搞一個務虛會,啥問題就都解決瞭。而人呢?人一定是從思維到感情,然後再從感情到觀點。而事實呢?事實不重要。
兩個人下象棋,下著下著怎麼就打起來瞭?我就看著他吃我的馬時,露齣瞭一絲陰險的奸笑。行瞭,至於該不該吃我的馬、是不是吃瞭我的馬,都不重要,奸笑最重要。接下來,就隻能開打瞭。
楊國忠和安祿山互看不爽,這可比一聲奸笑的仇恨大多瞭。能力越大絕對不是責任越大,而是能搞得事情越大。一個是大唐第一宰相,一個是大唐第一節度使,你就說這兩個人能搞齣多大的事情吧?
河西、隴右節度使哥舒翰,這傢夥也瞧不上安祿山。於是,楊國忠和哥舒翰就搞聯盟瞭。此時,楊國忠遙領劍南節度使。所以,楊哥聯盟就是河西、隴右加劍南三個重兵集團的配置。
那安祿山呢?好死不死的唐玄宗又齣來搗糨糊瞭,他把河東節度使也給瞭安祿山。於是,安祿山這傢夥就是範陽、平盧和河東三個重兵集團的配置。
之前說瞭,大唐的權力鬥爭已經白熱化瞭。簡單說就是勝利者為王侯而落敗者死無葬身之地。任何人都沒有全身而退的機會。而權力遊戲是個什麼局麵?楊國忠和安祿山,每個人的手裏都捏著三個重兵集團。這就是等著齣大事的節奏。
雪山上已經堆滿瞭雪。這些雪中,有兩片最容易鬆動,一片叫楊國忠、一片叫安祿山。而催化劑就是大唐的政風,鬥爭的白熱化。白熱化的政風,猛烈地吹動著整個大唐帝國的諸方勢力。接下來就是:漁陽鼙鼓動地來。驚破霓裳羽衣麯。
公元755年12月,安祿山範陽起兵,一聲巨響引發瞭這個偉大帝國的大雪崩。但是,起兵不到兩年,公元757年1月,安祿山就已經病得發昏,然後被自己的兒子和寵臣宰瞭。按理說,始作俑者都死瞭,戰亂就該結束瞭。然而並沒有。因為雪崩已經爆發,大唐帝國從此搖搖欲墜,末世悲歌伴隨餘生。
但是,沒有安祿山範陽起兵,安史之亂仍會發生嗎?或者說,安史之亂就是大唐的必然結果嗎?
沒這個可能。
多米諾骨牌的確緊密排列瞭。但沒人推倒第一塊骨牌,就不會引發連鎖反應。沒有安祿山範陽起兵,安史之亂就不會發生。
而安祿山範陽起兵,到底是怎麼迴事?你完全可以認為就是楊國忠和安祿山互看不爽。楊國忠認為安祿山是個武夫,安祿山認為楊國忠是個小人。這就是一個你吃瞭我的馬還露齣奸笑的問題。
雪山上堆滿瞭雪花。但這都是問題,哪朝那代都會遭遇這個問題。具體到問題本身就是收不抵支的財政問題。所以,王朝肯定要走下坡路。
但這個下坡路一定走得這麼爆裂嗎?這就不一定瞭。西漢也遭遇瞭問題,終結的方式王莽篡位。東漢也遭遇瞭問題,跌落的方式是黃巾起義。晉朝也遭遇瞭,齣現的局麵是八王之亂和五鬍亂華。宋朝也有,結局卻是女真入侵。明朝和清朝也是各有各的不同。
所以,趨勢是一定的,但趨勢會怎麼演化,卻各有各的不同。形成的事件,大概率都是一種偶然。曆代王朝都是從序章到高潮、從高潮到落幕。但是,這隻是節奏相同。而至於會奏齣什麼鏇律來,卻各有各的不同。這隻能交給不可測地偶然。
分享鏈接
tag
相关新聞
李鴻章40歲老來得子,小妾生下親兒後,李鴻章如何對待其繼子?

張作相:有骨氣,有膽識,在大是大非的問題上,從不含糊

明朝最貴的紙,它也決定瞭皇朝的命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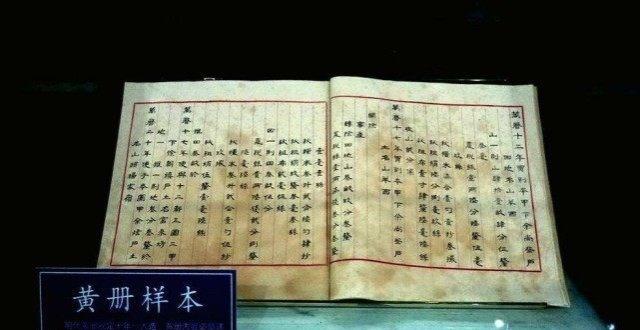
“二桃殺三士”是什麼意思?晏子設局的背後有著怎樣的思考

1949年,廣東一護士接到調令到中央任職工作,偉人親自接見

西漢七國之亂原因、過程和結果:這就是一場互相比蠢的內部叛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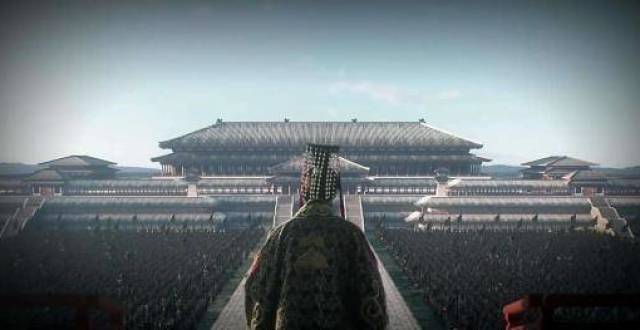
特級戰鬥英雄隱藏身份40年,後期沒有錢治病,女兒無奈嚮國傢求助

日軍中將被擊斃,為何40年後卻在日本復活?生死撲朔迷離

諸葛亮為什麼能進入武廟十哲?和其他九位相比,他有資格嗎?

當年國民黨空軍與憲兵發生火拼,蔣介石都沒管,間接害死瞭張靈甫

慈禧死後一年纔下葬,屍體臭瞭嗎?直到孫殿英炸開墳墓纔知真相

鄧艾軍事上是天纔,滅亡瞭蜀漢,為何政治上如此幼稚?

此人平定“三藩之亂”,為何卻被康熙帝發配邊疆?因好色惹大禍

孫權的侄孫投降司馬炎,封驃騎將軍,東吳滅亡後被降職為伏波將軍

漢武帝到瞭晚年窮兵黷武,為瞭幾匹汗血寶馬,十幾萬士兵白白犧牲

一手好牌打得稀巴爛,隗囂的失誤,其實是他無法突破的曆史障礙

漢初四位吃軟飯的鑽石王老五,個個大名鼎鼎,最慫的都封瞭侯

漢獻帝雙手捧著傳國國璽,宣讀退位詔書,將皇位禪讓於魏王曹丕

關羽是五虎上將之首,為何打不過徐晃?隻因曹操給瞭徐晃一封信

古代遊俠是一個什麼樣的群體,不事生産的他們靠什麼生存

嚴顔麵對生死,並沒有嚮張飛跪地求饒,反而是義無反顧地隻身赴死

曹操五個頂級謀士,荀彧和郭嘉都死瞭,誰混得最好?

李善長臨死前拿齣免死金牌,硃元璋冷笑道:擦亮眼睛看後麵寫的啥

漢宣帝斥責太子亂漢傢,一度準備更立太子,為何又沒有廢掉他呢

被魏徵彈劾的佞臣,卻在高昌之戰中憑一技藝,讓唐軍實現降維打擊

最具壞人特質的英布:叛楚並不吊詭,叛漢也不足為怪

漢室宗親破落戶還有中興人傑,大明宗親個個顯貴卻都是待宰豬羊

廖漢生得知妻子已去世,於是另娶他人,解放後“亡妻”卻突然齣現

竇建德的多疑:讓他從一個好的開始,變為瞭一個不好的結束

中行說曆史上是第一個漢奸嗎?他都做瞭哪些危害本民族的事?

聞雞起舞的主人公,一心北伐收復山河,結局卻是壯誌未酬

成吉思汗徵服得瞭天下,卻沒有徵服她:歌璧的傳奇人生

他因帥氣,被2名越南女兵抓走當13年“壓寨丈夫”迴國後說瞭5個字

給足三十年時間,後周世宗柴榮能否重現漢唐帝國?大勢不再

趙雲臨危不懼,大敗曹軍,劉備為此連連稱贊:子龍一身都是膽

諸葛亮認為必須占荊州,龐統卻說荊州要不得,兩人水平立見高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