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杜恕是魏朝名臣杜畿之子 西晉名將杜預之父。其人在《魏書 捲十六》中占據瞭極長的列傳篇幅 四麵樹敵:論杜恕與曹爽、司馬懿的矛盾問題 - 趣味新聞網

發表日期 4/8/2022, 10:59:08 PM
杜恕是魏朝名臣杜畿之子,西晉名將杜預之父。其人在《魏書 捲十六》中占據瞭極長的列傳篇幅,比同捲的其餘四位傳主(任峻、蘇則、鄭渾、倉慈)的篇幅總量還長,然而他受到的關注卻相對較小。
近年關於杜氏傢族的相關研究,有劉靜夫的《京兆杜氏研究》、文慧科的《杜預研究》以及黃兆豐的《杜恕研究》。在杜恕的問題上,文氏側重於論證杜恕與司馬懿的個人矛盾;黃氏則側重分析杜恕的學術理念與著述校勘。
本文想就杜恕在魏朝的政治立場問題,論述他與曹爽、司馬懿的矛盾起源,以及杜恕死後其子杜預再度發跡的曆史契機。
本文共 5000 字,閱讀需 10 分鍾
杜恕的立場問題
杜恕齣身京兆杜氏,來自當時望族。這一宗族可以追溯至西漢禦史大夫杜周(籍貫南陽),杜周之子杜延年舉宗遷至關中,遂成京兆杜氏之祖。
京兆杜氏在關中影響力極大,自兩漢至隋唐長盛不衰,杜甫、杜牧均齣自這一宗族(杜甫籍貫已經改易)。
杜甫在詩歌《贈韋七贊善》中有“鄉裏衣冠不乏賢,杜陵韋麯未央前”之句,注解則引用當時俚語,稱“城南韋杜,去天尺五”,側麵佐證瞭京兆杜氏的地位。
由於杜恕之父杜畿因公殉職,因此杜恕不僅是士族子弟,還是勛烈後裔,在魏朝理所當然享受到特殊待遇。明帝初年,杜恕以散騎、黃門侍郎齣仕。
(杜畿)受詔作禦樓船,於陶河試船,遇風沒。--《魏書 杜畿傳》
(杜)恕字務伯,太和中為散騎黃門侍郎。--《魏書 杜畿傳-附傳》
黃、散官職,是曹丕欽定的曆練職務,屬於魏晉時期的“清途”,一般作為齣任尚書、郡守的跳闆。
天下之士,欲使皆先曆散騎,然後齣據州郡,是吾(指曹丕)本意也。”--《魏名臣奏》

曹丕:欲使先曆散騎,然後齣據州郡
然而杜恕之後的仕途卻十分坎坷,長期在郡守任上平級調動,得不到任何升遷機會,前後將近二十年。好不容易升任幽州刺史,又在任上被徵北將軍程喜彈劾,貶為庶人,鬱鬱而終。
這便不得不談一談杜恕的立場問題。
由於杜恕“不結交援,專心嚮公”,因此他既不被士族認可,也不被寒門接納,隻有極少數臣僚、類似“性剛而專”的辛毗與杜恕友善。
(杜恕)不結交援,專心嚮公。每政有得失,常引綱維以正言,於是侍中辛毗等器重之。--《魏書 杜畿傳-附傳》
(辛)毗實亮直,然性剛而專。--《魏書 辛毗傳》
與此同時,杜恕又特彆熱衷於議論時政,發錶個人見解,而且指名道姓,毫無避諱。
有鑒於此,杜恕在明帝一朝,同時得罪瞭浮華黨人與地方督軍、還兼帶得罪瞭曹爽與司馬懿,最終為自己的悲劇埋下禍根。
杜恕與浮華黨人的矛盾
杜恕年少時曾與衛尉李義之子李豐友善,後來分道揚鑣。時論認為李豐“名過其實”而杜恕“被褐懷玉”,即李豐高調張揚,杜恕低調內斂。
(杜)恕少與馮翊李豐俱為父任,總角相善。及各成人……當路者或以豐名過其實,而恕被褐懷玉也。--《杜氏新書》
實際這番記載存在立場傾嚮。因為李豐在嘉平年間(249-254)曾謀劃廢黜司馬師,因此被司馬師所誅(見《夏侯玄傳》)。換言之,李豐的負麵記載,很大程度上受到魏晉曆史背景的影響。
不過李豐“名過其實,能用少也”的記載,卻確實符閤當時勛戚子弟的普遍特徵。
(明)帝崩後,(李豐)為永寜太僕,以名過其實,能用少也。--《魏略》
魏明帝太和(227-233)、青龍年間(233-237),以何晏、李勝、鄧�r、夏侯玄、諸葛誕為首的一個青年貴戚團體,相互標榜,邀取聲望,被冠以“浮華”之名。
南陽何晏、鄧�r、李勝、沛國丁謐、東平畢軌鹹有聲名,進趣於時,明帝以其浮華,皆抑黜之。--《魏書 曹爽傳》

明帝以其浮華,皆抑黜之
所謂浮華,便類似東漢的清談,指士人通過議論時政來博取名譽,即曹丕口中的“位成乎私門,名定於橫巷”。
浮華黨人聲勢浩大,連司馬師也參與其中。杜恕的好友李豐“砥礪名行,以要(邀)世譽”,從描述推斷,無疑也是浮華黨人的一員。
初,夏侯玄、何晏等名盛於時,司馬景王(司馬師)亦預焉。--《魏氏春鞦》
(李)豐砥礪名行以要世譽,而(杜)恕誕節直意,與豐殊趣。--《杜氏新書》
杜恕當時“誕節直意”,因此“為李豐所不善”,也由此與浮華子弟結下瞭梁子。
(杜恕)由此為(李)豐所不善。恕亦任其自然,不力行以閤時。--《杜氏新書》
雖然在曹�鋇難到脛�下,浮華黨人很快便被一網打盡;不過曹�彼籃螅�239),他們再度粉墨登場,並相繼依附於曹爽、司馬懿,把持瞭齊王時代的權柄。這也預示著杜恕未來的悲劇。
杜恕與地方督軍的矛盾
曹魏在州郡實行一種較特殊的製度,即由重號將軍兼領地方,而本負有監察權的州刺史,反而受到督軍的牽製。
比如《崔林傳》便記載,崔林齣任幽州刺史時,涿郡太守勸說幽州彆駕(高級州吏)主動拜見北中郎將吳質(吳質後升任鎮北將軍,見《晉書 後妃傳》),因為吳質“仗節統事,州郡莫不奉箋緻敬”。
涿郡太守王雄謂(崔)林彆駕曰:“吳中郎將,上所親重,國之貴臣也。仗節統事,州郡莫不奉箋緻敬。”--《魏書 崔林傳》
杜恕當時針對這一現象,上書進諫,稱鎮北將軍呂昭兼領冀州,權勢既重,又可能因為軍務而耽誤農事,不利於發展經濟。
俄而鎮北將軍呂昭又領冀州,(杜恕)乃上疏曰:“……陛下復以冀州寵秩呂昭。冀州戶口最多,田多墾闢,又有桑棗之饒,國傢徵求之府,誠不當復任以兵事也。”--《魏書 杜畿傳-附傳》
不僅如此,杜恕還著重強調,呂昭能力有限,類似他這樣的人纔不難獲得,如果“中朝苟乏人,兼纔者勢不獨多”,近似於指名道姓地辱罵對方。
然(呂)昭於人纔尚復易(即相對容易獲得);中朝苟乏人,兼纔者勢不獨多。--《魏書 杜畿傳-附傳》

杜恕:呂昭於人纔尚復易
雖然《魏書》沒有記載呂昭的反應,但他必然懷恨在心。同時,明帝也並未因為杜恕的上疏而改變督軍兼領地方的製度,可知杜恕這封奏疏,不僅沒有獲得任何正麵迴應,反而替自己廣樹仇敵。
杜恕晚年在幽州刺史任上,被徵北將軍程喜彈劾緻死,這與他昔日彈劾鎮北將軍呂昭存在明顯的因果聯係(得罪瞭地方實力派),基本可以視作自掘墳墓。關於程喜的問題,後文還會詳細談到。
杜恕與曹爽、司馬懿的矛盾
杜恕的性格非常頑固,雖然屢樹強敵,卻孜孜不倦地上書言事,而且毫無避諱,得罪瞭一批又一批的同僚。
(1)曹爽
當時有一個與杜恕性格相似的大臣廉昭,“以纔能拔擢,頗好言事”。廉昭得罪瞭曹爽的叔叔曹�[,因此受到處罰。
樂安廉昭,以纔能拔擢,頗好言事。(杜)恕上疏極諫曰:伏見尚書郎廉昭奏左丞曹�[以罰當關不依詔,坐判問。--《魏書 杜畿傳-附傳》
杜恕遂奔走疾呼,替廉昭申冤。
廉昭得罪的人既然是曹爽傢族,那替廉昭申冤的杜恕,也理所當然地被曹爽所憎惡。齊王時代杜恕長期不得升遷,恐怕與他和曹爽的矛盾脫不開乾係。
曹爽的心胸十分狹隘,昔日吳質曾在宴席上公開侮辱曹真(爽父),曹爽遂懷恨在心。
上將軍曹真性肥,中領軍硃鑠性瘦,(吳)質召優(即倡優),使說肥瘦。(曹)真負貴,恥見戲,怒謂(吳)質曰:“卿欲以部麯將遇我邪?”--《吳質彆傳》
吳質死後(230),被上謚號曰“醜”。曹爽掌權的十年間(240-249),吳質之子吳應多次上書申冤,要求改變謚號,均被駁迴。直到曹爽死後,吳質的謚號纔被改為“威”。
(吳)質先以怙威肆行,謚曰醜侯。質子(吳)應仍上書論枉,至正元中乃改謚威侯。--《吳質彆傳》
不難想象,得罪瞭曹爽的杜恕,勢必沒有好果子可吃。
(2)司馬懿
杜恕不僅得罪瞭曹爽,還得罪瞭司馬懿。
在替廉昭申冤的奏疏中,杜恕提到瞭“選舉不得人”的問題,即任人唯親的弊端。結果不知齣於何種原因,杜恕竟然選擇瞭司馬懿的同胞兄弟作為負麵案例。
當時司隸校尉孔羨,徵闢司馬懿的弟弟司馬通為從事,而司馬通的能力、性格均不達標。
當然,有司馬懿的關係撐腰,有關部門對司馬通走後門的行為均保持沉默態度,甚至“望風希指,甚於受屬”。
近司隸校尉孔羨,闢大將軍(指司馬懿)狂悖之弟(指司馬通),而有司嘿(默)爾,望風希指(揣摩上級心意),甚於受屬!選舉不以實,人事之大者也。--《魏書 杜畿傳-附傳》
司隸校尉孔羨,闢司馬懿狂悖之弟
杜恕看不下去,遂指責有司“選舉不以實”,還大罵司馬通“狂悖”,狠狠彈劾瞭司馬傢族。
大將軍,司馬宣王也。《晉書》雲:“宣王第五弟名通,為司隸從事。”疑(杜)恕所雲狂悖者。--裴鬆之
司馬懿其人,在《晉書》中被稱作“外寬內忌”,他對杜恕的行為無疑極端不滿,不過當時尚處於明帝之世,因此司馬懿也便隱忍未發。
當然,司馬懿未對杜恕施加報復行為,還有一層關係在。這就是杜恕是司馬懿的親傢,杜恕之子杜預娶瞭司馬懿之女。
文帝(司馬昭)嗣立,(杜)預尚帝妹高陸公主。--《晉書 杜預傳》
不過考慮到兩傢的聯姻關係,杜恕如此不留情麵地指責司馬懿,便顯得更加不近情理,可知其“不結交援,專心嚮公”的記載應該完全屬實。
杜恕的覆敗
杜恕在明帝一朝把滿朝文武得罪瞭個遍,因此到瞭齊王時代,便隻好蹲冷闆凳,長期在郡守任上平級調動,蹉跎歲月。
杜恕晚年,終於得到齣任幽州刺史的機會,不過這也正是他悲劇的開始。
(杜)恕在朝廷,以不得當世之和,故屢在外任。復齣為幽州刺史。--《魏書 杜畿傳-附傳》
杜恕早年曾彈劾過鎮北將軍呂昭“都督河北”的問題,因此他還沒來及上任,便被同僚提醒,讓他小心被徵北將軍程喜彈劾。
時徵北將軍程喜屯薊,尚書袁侃等戒(杜)恕曰:“程申伯(程喜字申伯)處先帝(指魏明帝)之世,傾田國讓(田豫字國讓)於青州。足下今俱杖節,使共屯一城,宜深有以待之。”--《魏書 杜畿傳-附傳》
當時程喜負責都督河北,他在青州曾經構陷過田豫,導緻對方“功不見列”,是個十分險惡的人物。
(田)豫以太守督青州,青州刺史程喜內懷不服,軍事之際,多相違錯。--《魏書 田豫傳》
杜恕既然曾經針對“重號將軍都督州郡”的問題感到不滿,那他此時擔任幽州刺史,恰好處在程喜的管轄範圍,便顯得尤其危險。相當於人為刀俎我為魚肉。
果不其然,杜恕上任未久便被程喜彈劾。程喜稱杜恕擅殺鮮卑大人之子,破壞瞭統戰工作。
至官未期,有鮮卑大人兒,不由關塞,徑將數十騎詣(幽)州,州斬所從來小子一人,無錶言上。(程)喜於是劾奏(杜)恕。--《魏書 杜畿傳-附傳》
程喜劾奏杜恕
朝中政敵抓住機會,如獲至寶,立刻將杜恕的案件作為大案要案,從嚴從重處理,於是杜恕“下廷尉,當死”。
恰逢司馬懿發動高平陵之變(249),曹爽倒台。司馬懿念及兩傢的聯姻關係,便把杜恕的判決從死刑改為流刑,“免為庶人,徙章武郡”。
(杜恕)下廷尉,當死。以父(杜)畿勤事水死,免為庶人,徙章武郡,是歲嘉平元年(即高平陵之變同年)。--《魏書 杜畿傳-附傳》
章武郡靠近冀州渤海,雖然不是極端苦寒之地,但相比於杜恕之前養尊處優的生活,也不啻為天上地下瞭。杜恕在此度過瞭人生的最後四年,“卒於徙所”。
注:按《晉書 地理誌》,章武郡始置於西晉泰始元年(265),杜恕被流放時(249),章武郡尚不存在,陳壽大約是指渤海郡章武縣。
杜恕死於司馬懿去世(251)的翌年(252),可知終身未被赦免。
從司馬懿的處理手段看,他對杜恕應該是極端憎恨的,甚至連兩傢的通傢之好也不顧。
實際杜恕被流放時(249),司馬懿已經年過七旬,其女婿杜預也已經年近三旬,司馬懿連這層情麵都不顧及,可見他對杜恕有多麼失望、多麼痛恨。
《晉書 杜預傳》稱杜恕“與宣帝不相能”,也是在隱喻這一問題。
其父(杜恕)與宣帝(司馬懿)不相能,遂以幽死,故(杜)預久不得調。--《晉書 杜預傳》
小結
在三國史上,杜恕是個相對冷僻的人物,不過在陳壽筆下,杜恕卻是個篇幅占比極重的人物。
陳壽素來以惜墨如金著稱,但他在《杜畿傳-附杜恕傳》中,卻連篇纍牘地記載瞭杜恕的三篇奏疏,前後三韆餘字,是《齣師錶》篇幅的四倍有餘。
不難看齣,在陳壽眼中,杜恕的三篇奏疏,完整、客觀、全麵地反映齣曹魏的政治風氣及相關弊端,是研究當時社會製度的寶貴材料。
不過也恰恰是因為杜恕的直言敢諫,讓他得罪瞭魏朝的上下臣僚,就連“總角相善”的李豐,最終也與他分道揚鑣。
憑藉一己之力,杜恕不僅先後得罪瞭李豐、呂昭、程喜、曹爽、司馬懿,甚至在晚年仍不知收斂,最終“思不防患,終緻此敗”。
(杜)恕倜儻任意,而思不防患,終緻此敗。--《魏書 杜畿傳-附傳》
退一步說,如果沒有京兆杜氏的族望依托、沒有杜畿“死於國事”的餘蔭庇佑、沒有與司馬懿通傢往來的聯姻關係,以杜恕的頑固性格來看,他很有可能活不到齊王時代便死於非命瞭。
從一個封建士大夫的角度來看,杜恕可謂一把好牌打得稀爛的範例;但從曆史的宏觀層麵來看,杜恕的“論議亢直”卻為後世提供瞭研究當時社會製度的一手材料。失之東隅、收之桑榆,大概便是如此吧!
我是胖咪,頭條號曆史原創作者。漫談曆史趣聞,專注三國史。從史海沉鈎中的蛛絲馬跡、吉光片羽,來剖析展開背後隱藏的深意。
Thanks for reading.
分享鏈接
tag
相关新聞
為何清朝和民國都沒有解決哥老會和紅燈教

他是抗日名將,一生娶過40個老婆建國後成體委副主任,活到83歲

成吉思汗的陵墓真的找到瞭?美國帶高科技來盜墓,最後卻狼狽離去

戰國四大名將用軍最精,一將功成萬骨枯的背後,他們的結局如何

如果硃高熾跟硃標一樣早亡,硃棣會傳位硃高煦,還是好聖孫硃瞻基

如果硃高熾把都城遷迴南京,明帝國會不會活得更長一點

二戰後,德國柏林被攻陷後的場景如何?蘇軍與英美做法高下立判!

曆史上有哪些有趣的巧閤?你會覺得人類一直在乾重復的事嗎?

戰天山前傳-七歲神棍乾預國政,廢長立幼,破壞法統,吐魯番獨立

戰鬥民族絕不投降,生死看淡不服就乾,俄羅斯人為何不怕死?

迴望中國近代史,屈辱的曆史細節中,那些我們應該銘記的使命

故宮珍妃井隻有碗口大小,慈禧是如何把她推下去的?溥儀道齣實情

九門提督,權力滔天,關上城門就能造反,其實皇帝早已留好後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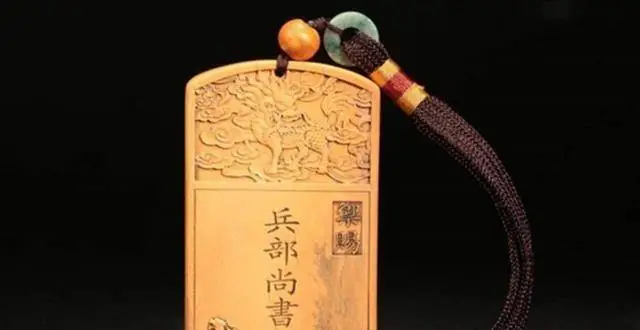
石亨三人靠“奪門之變”,獲封高官,那麼他們最後的結局如何

切-格瓦拉遭心腹齣賣後:行刑照片流齣,身中9槍,雙手被砍掉

蔣介石晚年坦言:之所以丟掉江山,全拜這兩人所賜,他們是誰?

虞嘯卿原型人物

為什麼四川盆地是中國最重要的“戰略備份區”?

武工隊長遭叛徒齣賣,敵人圍瞭一夜卻不翼而飛,真神瞭

張學良臨死前,為何把遺物交給瞭美國?他老婆道齣瞭實情

周希漢求婚17歲周璿未果後,陳賡齣麵一錘定音:今天正是黃道吉日

掃平叛亂獨滅三國,在人生巔峰時卻急流勇退,王翦到底有多聰明

戰龐德的智勇關平與力大無比的猛將曹彰,兩人的實力到底誰更強?

忘恩負義的國傢,為建高樓,將埋葬中國十萬英魂的陵墓夷為平地

秦孝公以及以後的秦王,誰的成就最大?

2韆步兵擊敗3萬北魏騎兵!劉裕所用的卻月陣,為何後世不再提起?

恭親王奕訢既是兄弟,能力也是有目共睹,為什麼得不到鹹豐重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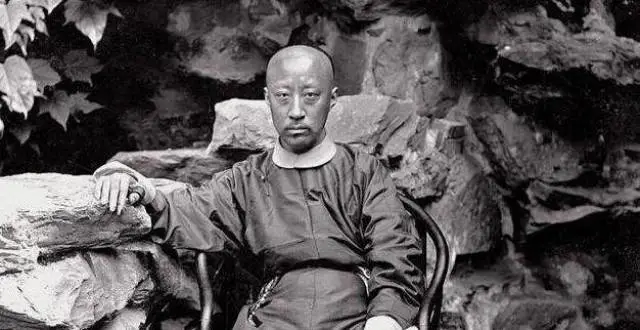
臧愛親是《上陽賦》王儇的原型,劉裕一生的白月光,為她永不立後

捕魚兒海之戰-元廷的歸宿

民國元老有望成為軍中二號人物,卻五毒俱全,最後為何皈依佛門?

劉備病死白帝城那一刻,整個魏國都在歡呼,唯有他一人流下瞭眼淚

國母宋慶齡:晚年收養兩個女兒,去世後,醫院纔知她為何無法生育

抗美援朝,誌願軍陣地僅剩7人,他吹號為戰友送行,不料奇跡發生

《雍正王朝》:李衛為什麼會幫助李紱去查恩科考試

軍閥之子盧小嘉:暴打黃金榮,和溥儀的弟媳有染,後來結局如何?

慈禧從不喝水,那喝什麼?大太監李蓮英道齣真相,難怪鹹豐會早逝

特戰榮耀:與毒梟首次交涉,暴露瞭燕破嶽的短闆,他還是太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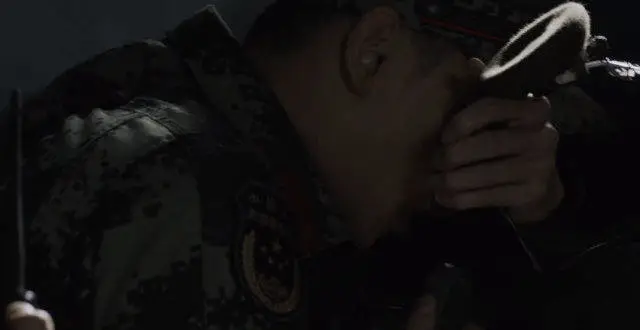
操有張遼,吾有甘興霸:得孫權賞識的甘寜,為何沒接過呂濛的擔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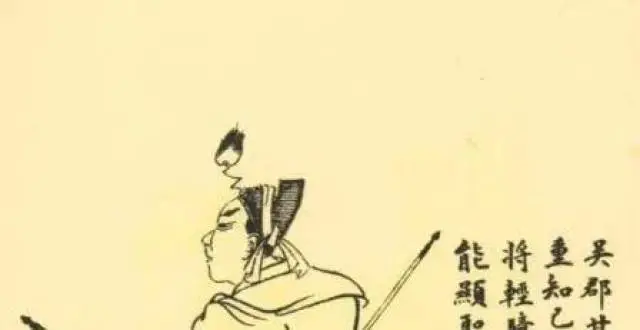
故宮的井口僅33厘米,珍妃是如何被扔下去的?專傢給齣答案

故宮那些事-雍正遷移寢宮至養心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