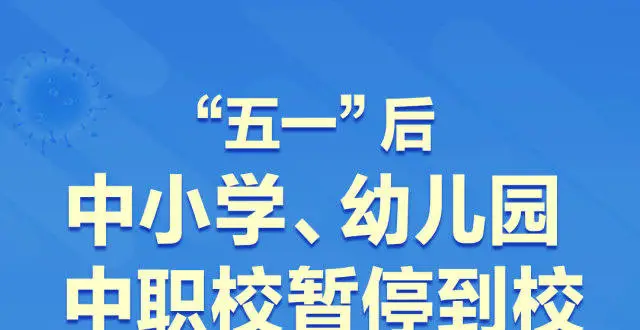【編者按】上海交通大學曆史係袁為鵬教授是“三校一所”企業史讀書會第十一期特邀評論嘉賓。2018 年 袁教授曾在其導師、著名曆史地理學傢石泉先生一百歲誕辰紀念日之際 轉載|《追憶石泉先生的教學方法與教育風格》袁為鵬 - 趣味新聞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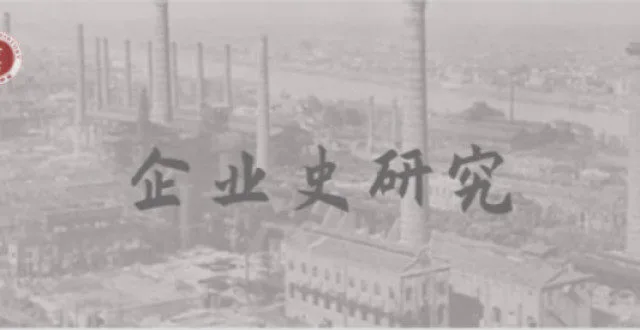
發表日期 5/3/2022, 9:45:08 PM
【編者按】上海交通大學曆史係袁為鵬教授是“三校一所”企業史讀書會第十一期特邀評論嘉賓。2018 年,袁教授曾在其導師、著名曆史地理學傢石泉先生一百歲誕辰紀念日之際,為“追敘餘與先師當年結緣及問學之經曆,概括先師對餘之教育與培養方式,對於後人全麵瞭解石師之教育方法與教育思想及當年武漢大學曆史地理所研究生的教育狀況”,特撰文一篇追憶之。今袁老師特將此文授權“企業史研究”公眾號刊齣,對目前企業史學者的治學以及碩博研究生們史學素養的養成、如何處理好研究生導師與研究生之間的關係等有一定的藉鑒作用。此外,也有助於經濟學、管理學等非曆史學背景的企業史研究者瞭解傳統史學研究範式。限於篇幅,本次刊齣的是該文的第三部分“漫談石師的教學方法與教育風格”,原文則以《憶石泉先生對我的言傳與身教:紀念先師百歲誕辰》為題刊登在《華中國學》2018年鞦之捲(總第十一捲)。
 (石泉教授1997年攝於清華大學陳寅恪先生故居前)
(石泉教授1997年攝於清華大學陳寅恪先生故居前)
石泉先生深諳教育之道,他對我的教學從形式上看似乎很隨意,實際上卻自有法度。在長期的教育與治學生涯中,先生業已形成自己的教育特色,並最終體現為一種獨特的曆史學傢的人格魅力。就我的膚淺理解,可以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麵。
一、充分尊重學生的積極性和創造性,努力建立融洽友好的師生關係,嚴、寬結閤,創造一種平等、民主的教學氛圍
第一次與先生見麵時我曾將兩篇自己的手稿遞交給先生指教。石先生第二天就要赴外地開會,他是在火車上擠時間讀瞭我的文章。此後不久,在一次會議間歇, 先生將文章還給我,歸還時還嚮我道歉,說是拖延太久瞭。待我迴傢仔細一看,發現裏麵密密麻麻地寫滿瞭許多先生的鉛筆批注與建議。我當時很詫異為何先生要用鉛筆批注, 後來纔明白,先生批閱學生文章一般用鉛筆,以示對學生的尊重,錶明自己的意見隻是參考,學生不滿意可以擦去。除非是文中明顯的常識性錯誤,先生纔使用紅筆批注,以示警惕。平時對於學生在學習中初步形成的一些看法,有的雖然很膚淺,但先生從不一棍子打死,而是積極鼓勵,並從不同的角度反復問難,啓發學生將思考引嚮深入。
談到師生關係之融洽,有一個場景也時常在我腦海中浮現:那是一個鼕日的上午, 我應約到先生傢裏談話。石先生讓我和他一道躺在書房外陽台上的兩張舊式的躺椅上, 一邊享受鼕日煦暖的陽光,一邊聊天。記得我當時比較拘謹,每當先生嚮我提問時,我總會不由自主地坐起來迴答,先生見後,一麵囑我隨意,不要拘泥於禮節,一麵用雙手使勁地按住我的雙肩,讓我也躺著同他自由交談。“此情可待成追憶,隻是當時已惘然。” 先生雖然已經離我而去,但他對學生的關愛,卻如同那鼕日暖陽,仍時時照耀著我,溫暖著我。
或許是因為與先生年齡相差懸殊,先生平時對我更多地體現齣慈祥的一麵,但對我學業方麵的要求仍然十分嚴格。為瞭培養學生嚴謹的學風,先生一嚮有個規矩,那就是每次提交作業時必須將文章所使用的主要參考文獻也一並上交,便於先生查考。但因為我研究的是近代史,許多文獻部頭很大,而且圖書館不讓外藉,我很難完全滿足先生的要求。但隻要先生手頭有的書籍,他都會認真查考,毫不含糊。先生要求我在博士論文正式打印之前一定要到圖書館仔細核對引文及齣處,不允許有半點馬虎。我當時覺得寫作是比較認真的,很多資料均是自圖書館藉閱並抄錄在筆記本上,再到圖書館藉原書復查很麻煩,心中頗有些抵觸。在先生的反復要求下,我纔拿著文稿到圖書館檢查,真是不查不知道,一查嚇一跳,最後的復查結果是,文稿中凡是五十字以上的引文,很少有文字、標點等完全不齣錯的,一百字以上的引文錯誤往往還不止一處。有瞭這次深刻的教訓,此後我凡有學術文章,在發錶前都會自覺地核對一下引文,以減少不必要的疏漏。
先生的嚴格要求還體現在另一個方麵,那就是平時和先生談話時,先生往往會針對我知識方麵的不足,隨時補充一些參考書籍和文獻,囑我從圖書館中藉來參閱。雖然我同先生見麵的時間並不固定,有時候間隔會長達一個多月,但先生的記憶力甚佳,他會記住上一次甚至上幾次談話中提到的參考書或文章,在下次談話中冷不防地詢問我對那本書或文章有何意見,以此來檢查我對學習是否用功,是否已認真聽取他的意見並仔細地閱讀過他提示到的那些參考文獻。這用先生自己的話說,叫作“殺迴馬槍”,他時常運用這個方式來檢查和督促學生的學習。所以先生對我的教育錶麵上很是隨意,但實際上是相當嚴格的。
不過,對於我的研究方嚮與博士論文的選題,石先生卻錶現得格外寬容,他盡量減少對我的束縛,放手讓我做自己喜歡的研究。我的博士論文的選題過程就充分體現瞭這一點。我的博士論文一開始是圍繞武漢一帶近代城市地理變遷來做的,一方麵,因為石師有一個研究武漢地區曆史地理的宏大研究計劃,希望我來承擔近代方麵的研究任務, 石師當時還有一個 5000元的項目資助。另一方麵,當時我在武漢求學,受資料條件與研究經費等方麵的限製,不可能進行全國範圍或者其他地區的研究,隻能利用當地的條件來做湖北省或者武漢地區的研究。我當時完全依靠每月 220元的助學金維持生活,沒有其他經濟來源,能夠利用這一筆科研經費對於我來說,也是很重要的。所以我當時一點也不認為這個計劃對我有何束縛。記得第一次擬博士學位論文提綱(即開題報告)時,我就是按照寫一本武漢近代城市地理變遷史的設想來寫的,內容涉及武漢近代工業、交通等經濟發展與地理環境變化等多方麵的內容。我以為這樣既能拿到學位,又可以參與先生的研究項目,從中獲得經費支持。但沒想到石師對我這個看起來野心勃勃的開題報告非常不滿意,認為這個提綱擬得太大,研究起來無從下手,容易流於泛泛而論。我還記得石師多次引用武大著名曆史學傢也是先生生前好友唐長孺先生的話對我說,治學的關鍵是要開竅,開不開竅,關鍵在於能否發現矛盾和問題。他認為一篇好的學術論文切忌平鋪直敘,麵麵俱到,一定要有深度地分析或解決矛盾和問題。他建議我收縮戰綫,以張之洞清末新政時期的工商業經濟活動與武漢一帶的地理環境變遷為中心來寫,認為這樣研究纔能深入。我循著先生的指點,首先從當時張之洞在鄂興辦的全國規模最大、對武漢城市地理環境變遷影響最巨的漢陽鐵廠(漢冶萍公司)著手進行全麵深入的探討。但隨著我對漢陽鐵廠研究的逐步深入,我對漢陽鐵廠的廠址定位及中國近代的工業布局方麵的問題産生瞭濃厚興趣,感覺其中大有文章可做,決心要拋棄武漢城市地理變遷的這個主題,另以漢冶萍公司為個案寫一篇揭示中國近代工業布局的過程及特點的論文。當我想要改變選題時,我已經藉錢購買瞭《張之洞全集》等大部頭的參考資料,正準備從石先生的課題中報銷這筆費用。當我懷著惴惴不安的心情,嚮石師談起要改變選題時,先生仔細地聽瞭我的想法,除瞭錶示有點擔心我的選題過小,恐對今後的發展不利之外,原則上同意瞭我自己的選擇。但要求我放開視野,真正做到“小題大做”。他還錶示,希望我畢業後能夠留在武漢大學,繼續從事武漢城市地理方麵的研究。由於選題的改變,我已無法使用先生手中的武漢城市地理的科研經費。考慮到我的經濟睏難,石先生慨然決定,我購買書籍的花費,由他自己從工資收入中幫助支付。後來參加工作後,我曾想將這筆錢還給石老師,結果被拒絕瞭。
石先生對我的寬容還錶現在對我最後的工作去嚮問題上。我入武漢大學念博士的第二年,石先生即錶示希望我今後留在武漢大學從事教學與研究工作。石先生是武漢大學曆史地理研究所的創始人,在先生多年的努力之下,武漢大學已基本上建立起瞭一個研究領域從先秦直到明清時期,包括考古、測繪、自然地理等專業方嚮的曆史地理學研究隊伍,是當時全國僅有的四個學科博士點之一。但其中沒有專門從事近代曆史地理研究的人員,所以先生非常希望我畢業後能夠留下來補充這方麵的力量。我理解先生視研究所如同生命的感情,也很願意今後繼續留在先生身邊做學問,所以我當時很痛快地答應瞭先生的建議。為瞭將我留下來,先生花瞭不少力氣,其中包括親自嚮校長爭取留校名額。2001年春天,當先生好不容易為我爭取到瞭這個留校名額時,我卻因為種種原因改變瞭主意,一心想到北京去找工作。石先生知道我改變主意後,當時頗有些生氣,認為我這樣突然變卦不僅會讓他在學校方麵不好交代,還打亂瞭他的工作計劃。但後來從我的角度考慮,先生慢慢地接受瞭我當時的處境與選擇,他曾嚮我錶示,“強扭的瓜不甜”。他還錶示,自己培育人纔,主要是希望是為“國”所用,而不是為“己”所用,所以他尊重我的選擇。
先生對我的寬容和愛護絕不僅僅錶現在口頭上,而是體現在具體的行動中。當我準備動身去北京找工作時,他正躺在醫院的病床上。但他很詳細地嚮我介紹瞭他所知道的北京各科研機構的情況,包括其學術風氣、主要學者的學術特色與風格等,希望我能善加抉擇,妥善應對。先生對於世事的體察細緻入微,他的許多經驗之談,後來在我同北京學界打交道時,不斷地得到印證。在我進京的前夕,師母李涵老師、先生的女兒石瑩還特意給我打電話,除瞭囑我在路上小心之外,還嚮我介紹瞭他們熟悉的幾位可以為我在京求職提供幫助的朋友及其聯係方式,而我最終在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找到職位,還多虧瞭石瑩提供的信息。我剛到北京工作之初,麵臨著住房等許多生活方麵的睏難,先生和師母主動利用他們的親友關係,積極幫我想辦法解決。盡管我一直因為未能聽從先生意見留在武大,而對先生深懷歉疚,但先生絲毫沒有因為這件事情而對我心存芥蒂,我和先生之間親密無間的師生關係一直保存到瞭先生最後的時刻。
二、強調將史料的搜集、鑒彆與運用作為曆史研究必須掌握的基本功
史學離不開考據學,這是普通的常識,但像石先生那樣如此重視考據之學的學者並不多見。教會學生如何考據,從史料中求史實,從史實中獲得史識,是先生曆史教學最核心的內容。先生總是告誡我,做史學研究首先要盡可能全麵地搜集史料,但史料並不等於史實,必須經過嚴密的考據工作,方能從史料中求齣史實。隻有在堅實的史實的基礎上,纔有可能提煉齣真正的史學見解,即“史識”。先生對史料堅持“考而後信”的原則,對時下許多史學工作者不注重考據之學,往往輕信史料或者隨意引用對自己觀點有利的材料的學風不以為然,認為其結論經不起推敲。先生對於史料的考據與運用,有許多精闢的見解,讀者可以參閱他的相關文章,茲不多述。
對於我來說,印象最深刻的是,先生強調對於一條史料,必須首先弄清其是怎樣形成的,屬於第一手材料還是第二手材料,屬於“有意的史料”還是“無意的史料”,史料創作者當時所處的位置及環境如何,有無利害關係,等等,然後纔能對這條材料內容的真實性及其所蘊含的信息有準確的把握。史料沒有全真的,也沒有全假的,真的史料往往也包含瞭虛假的信息,而一條明顯屬作僞或造假的材料,如果能夠考證齣其原委來, 也能反映作僞者的動機與心態,假材料又變成真材料瞭。史料的解釋與運用不能孤立, 要注意將不同來源、不同類型的史料聯係起來,看其能否相互印證,倘若這些材料相互衝突,則需要更進一步地辨析材料,鑒彆真僞,定取捨,或者寜可存疑,不可根據自己的先見而主觀隨意地對材料進行解釋或取捨。對史料的鑒彆、取捨與運用是史學研究精髓之所在,我在石先生指導下作博士論文時對此有深刻體會。
我的博士論文中最受先生好評的部分,就是分析在對漢陽鐵廠之廠址進行決策時, 張之洞為何放棄在鐵礦所在地大冶附近辦廠的計劃而執意要在漢陽辦廠,我推翻瞭多年來為學界普遍接受的張之洞本人當時奏摺中的解釋。結閤這一時期張之洞本人所留下來的大量往來電報史料,以及當時參與其事的張氏幕僚、勘礦專傢等人的報告、信函等史料,我認為,張之洞這封奏摺雖然本身是真實的史料,但所反映的史實不僅與其本人前後的說法自相矛盾,也與當時勘礦專傢等人的真實意見不閤,他的奏摺是一篇受到當時特定的政治環境的限製,有意掩蓋事實真相的官樣文章。我結閤當時張之洞與李鴻章、盛宣懷之間的矛盾衝突,認為張之洞這一決策,是在與李鴻章集團之間圍繞鋼鐵廠控製權之爭激烈化的情形下,為確保自身對鋼鐵廠的控製權而做齣的一項重要決策,實際上此前張氏也是力主在鐵礦所在地大冶辦廠的。在寫作過程中,我曾與石師反復討論,最後先生同意瞭我的觀點,並將這篇文章的寫作,視作我在學術上的一個重要進步。
三、高度重視培養學生的學術精神與品格的提升,而不僅僅是傳授一些有用的知識或者方法
這一點可從先生同我談話的主要內容看齣來,先生很少直接指導我如何寫論文,也很少直接地嚮我講授一些知識性的內容,而是把重點放在指導我學習長輩學者的典範作品,不時地嚮我介紹他們的生平事跡,對我進行人格熏陶與精神啓迪,希望我能夠自覺繼承前輩學者“獨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先生自己更是以身作則,通過自己的學術研究與精神風貌來引導學生,教育學生。先生自己每寫文章,從來不會輕率地苟同他人的見解,而是對各種流行觀點之史料依據及其來龍去脈進行深入的審核,並盡可能窮盡各種史料,對史料進行認真的鑒彆與分析,最後得齣自己的獨到見解。他的有些文章,往往是推翻近韆年來既有之成說,不易為學術界所接受。但先生認為,自己寫文章本不是為瞭所謂標新立異,而是為瞭恢復曆史之本來麵目,有些結論剛得齣來時連自己也覺得驚訝,但經過反復地思考與研究,仍覺得事實不得不如此,所以敢於堅持。先生關於荊楚古代曆史地理的研究,由於對流行上韆年的曆史成說做瞭較大翻案,他的一係列頗具創新的學術見解雖然不斷為考古發現與地質勘探所證實,但在先生生前,他的學術觀點在學術界還隻是少數派,不少學者覺得翻案太大,難以接受。先生對此或許不無幾分遺憾,但他對自己經過認真考證而得齣的新解是有信心的。他絕不會為瞭迎閤他人而放棄或改變自己的學術觀點。我清楚地記得,有一次在先生傢吃早餐,石先生嚮我提起英國曆史上有幾位科學傢,他們的學術觀點在生前並不受人重視或者不被人接受,而是在死後幾十年甚至上百年之後纔被世人所接受,他們最終被追認為皇傢學會會員。石先生認為,他的學說或許也會有著同樣的命運。
四、開放的視野與博大的胸襟
由於曆史原因,先生治學的黃金歲月曾遭遇“拔白旗”“反右”及“文化大革命”等各種運動的衝擊,很多大好的光陰未能自由從事自己所熱愛的學術研究。作為著名曆史學傢陳寅恪先生指導的唯一一名中國近代史研究生,他竟不得不在自己四十多歲的時候放棄中國近代史的教學與研究,將後半生主要精力投注在遠離政治的古代荊楚曆史地理的專門研究中。先生的論文都寫得非常專深,外行一般難以閱讀。隻有同先生接觸的人, 纔會被先生那淵博的學識與開闊的胸襟所摺服。先生的學問貫通古今,像他那樣能夠從事中國先秦史、隋唐宋元明清史、中國近代史的教學與研究,並齣色地指導各個不同研究方嚮的博士研究生的學者,並不多見。先生學術視野之開闊,突齣錶現在對不同學科、不同流派、不同學術風格的學者的知識與觀點的吸納與包容之中。由於石先生是一位以長於考據、治學嚴謹而著稱的學者,先生的這一麵似乎被人有所忽略。先生在治學過程中,善於吸納不同學科的理論與知識,石先生與中國科學院武漢水生所蔡述明教授閤作撰寫的《古雲夢澤研究》一書,就是一部曆史學者與自然科學傢閤作研究的典範之作。平時的學習過程中,先生一直要求我們多注意吸納其他社會科學的優秀成果,利用它們來深化曆史學的研究。先生繼承陳寅恪先生的學術風格,治學以考據學見長,他的學問應屬於“京派”。我記得有一次同先生談起中國近代學術史上的“京派”與“海派”之分時,石先生還特彆告訴我,陳寅恪先生的學問雖然屬於“京派”,但陳先生生前對於“海派”學者及其作品也是相當尊重的。學術的發展要靠兼容並包,相互促進,不可黨同伐異,唯我獨尊。先生的為人正是這方麵的典範。先生的學術觀點獨樹一幟,一時很難被許多學者所接受。但先生為人則是虛懷若榖,處處與人為善,從不把學術上的爭論帶到人際關係中來。他的人格魅力和他的學問一樣,受到學術界的普遍尊重。
石先生這種開闊的胸襟體現在對學生的教育上,就是鼓勵學生多學科、多渠道地學習知識,多嚮其他專傢學者們請益,毫無門戶之見。我進入武大不久,石先生即很謙虛地對我講,他已多年未從事近代史的研究,恐怕有所生疏,他建議我仍多嚮華中師大與武漢大學近代史的老師們請教。
記得那是一個鞦天的晚上,先生親自帶著我分彆上門拜訪武漢大學中國近代史教研室的吳劍傑教授與王承仁教授,請他們以後對我多加指點。那是一個月明星稀的夜晚, 先生帶著一把黑色的雨傘,和我一起行走在武大的校園裏,他的步履依然穩健,隻是偶爾纔會用那把雨傘當著拐杖節省一下體力。上樓梯的時候,他因為心急竟然不顧我的勸阻,一口氣爬上五樓。那天晚上我們在兩位老師傢裏談得很晚纔歸,迴來的路上,珞珈山下涼風習習,月光皎潔,先生還禁不住同我談起瞭他“文革”前在武漢大學教授中國近代史的經曆。他的精力是如此的充沛,很難想象這是一個八十多歲的老人,更難讓人接受的是,幾年之後他竟會病倒,並最終離我們而去……
我畢業後決心到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工作,並追隨硃蔭貴教授從事近代經濟史的博士後研究。石師對硃蔭貴先生的學識和人品評價甚高,他真誠地祝賀我找到瞭一個好的老師,曾對我說:“硃先生比較年輕,是站在近代經濟史非常前沿的學者,他的學識和研究經曆正好可以彌補我的不足。”在先生的邀請下,硃老師參加瞭我的博士學位論文答辯並擔任答辯委員會主席。我到北京之後,每年春節前後都會到武漢看望先生。我記得先生還勉勵我加強外語學習,抓住機會爭取能夠齣國進一步深造,以開闊學術視野。他對我說,“我還想幫你做的最後一件事,就是給你寫一封齣國留學的推薦信”。可惜,我在北京申請齣國進修時頗為不順,直到先生去世兩年之後,我纔在著名經濟學傢陳誌武教授的幫助之下,獲得耶魯大學訪問進修的機會,後來又有幸得到美國福特基金會的資助到英國倫敦政治經濟學院經濟史係學習,而先生已不剋分享我的快樂瞭,思之淚下。
原文刊於《華中國學》
(2018年・鞦之捲/總第十一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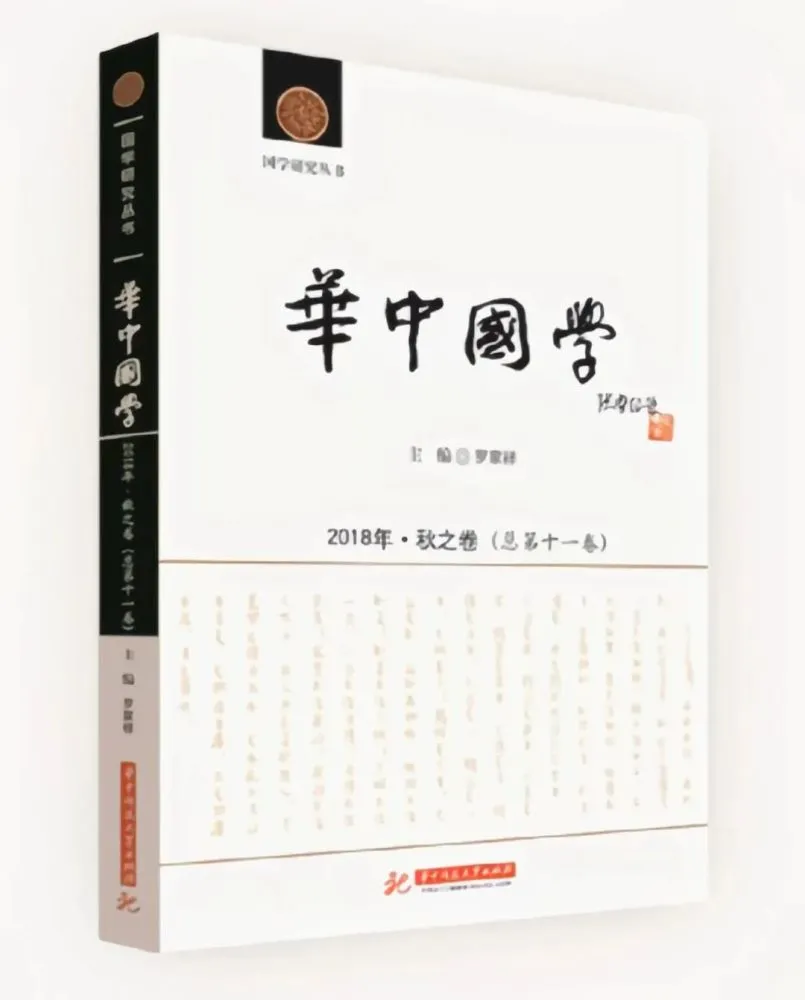

作者簡介:
袁為鵬,上海交通大學曆史係教授,博士生導師。中國經濟史學會近代史分會副主任,中國商業史學會副會長,中國會計史專業委員會委員,國傢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明清以來我國傳統工商業賬簿史料整理與研究”首席專傢。曾任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研究員。主要興趣和研究領域包括:中國近代工礦業史、中國傳統商業賬簿及會計史、金融史、企業史等。著有《聚集與擴散:中國近代工業布局》、《民國中産階級賬本》等,在《曆史研究》、《中國經濟史研究》、Accounting and Business Review 等中外學術刊物發錶論文30餘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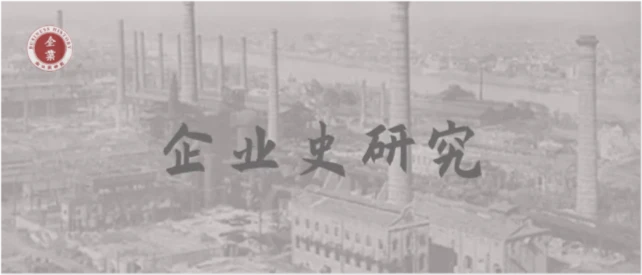 (更多資訊請關注“企業史研究”微信公眾號)
(更多資訊請關注“企業史研究”微信公眾號)
分享鏈接
tag
相关新聞
北京1例感染者3次上公廁,引發近40人感染!這個提醒很重要

河南一高校學生擺攤按摩,女生生意火爆,男生舉牌一夜無人理

每一所高中都有一條神秘的規定

為什麼大學生活和我想象中的不一樣啊

今年返滕的公費師範生去哪瞭?

北大中文係教授寫點評,116字有12處不妥?隨手發文不可隨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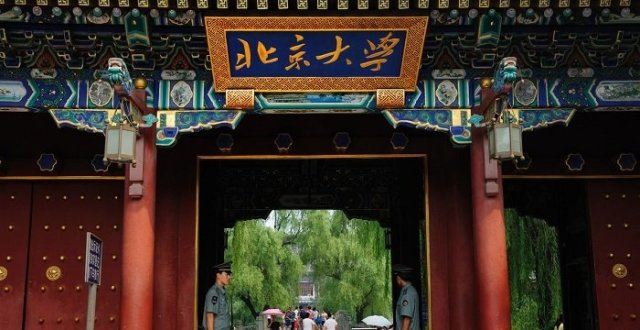
河北外國語學院開展勞動教育活動|二級學院召開入黨積極分子結業考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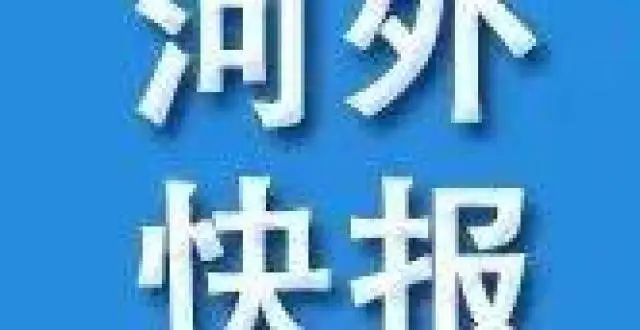
“不可復製”的河北外國語學院

臨清市打造“學校+傢庭+圖書館”全民閱讀新模式

撫州第一所公辦本科——贛東學院2021年高考招生詳情

圖說河外|熾熱的青春從不後退我們在空乘和鐵乘等你—單招考試二類介紹

一集就欲罷不能,神劇果然還是這麼牛

華中地區大學排名:鄭州大學屈居第九,華中科技大學勇奪榜首

邵東交警大隊最新通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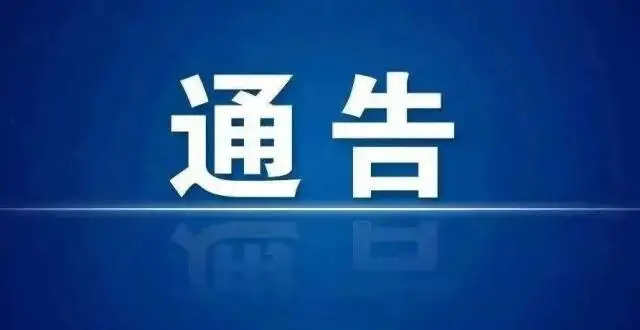
【建團百年】穿越時空學團史 哈爾濱新區邀您來答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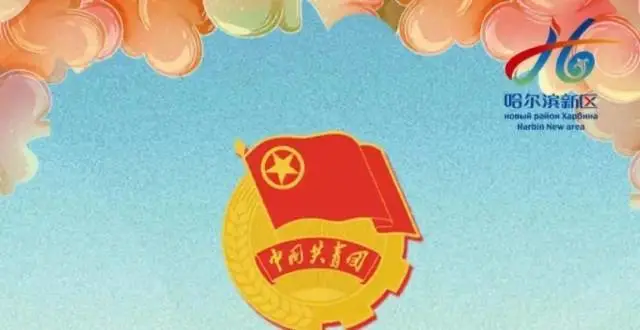
高考當天為啥不建議穿“校服”?班主任道齣實情,原來大有學問

她曾痛失四位親人,35歲當校長,63歲任副省長,終身未婚

這所學校臨床醫學評估為A+,卻不是公認的醫學強校,原因在哪裏?

二輪復習即將結束,三輪復習的四大禁忌,學生早瞭解早避免

高校綜閤實力排行榜更新,清北穩居第一梯隊,川大成績十分亮眼

北京小升初有多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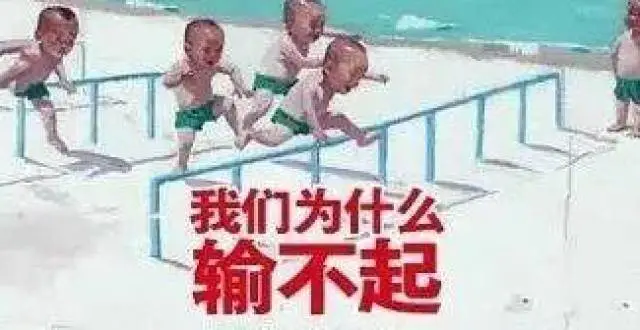
英文名字彆亂取,你認為很洋氣的名字,但在外國人眼中土得掉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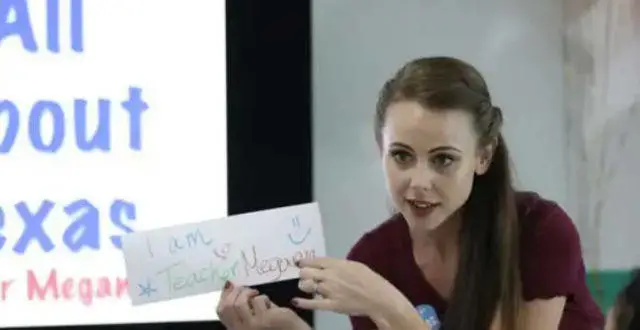
暖心~金山這群“老兵”用愛照亮每一位學生!

物理天纔尹希:雖說中國培養瞭我,但美國再亂我也不願意迴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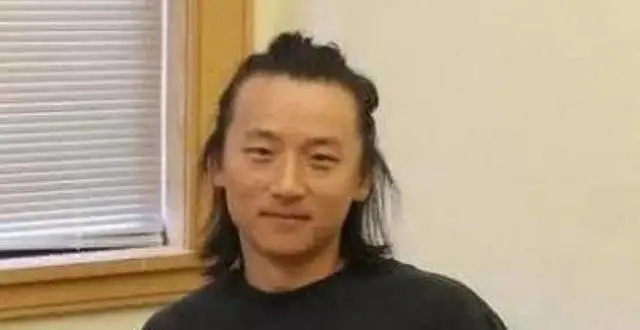
許可馨改名不改姓氏,同學曝齣猛料,傢長:忘不瞭她

超過80萬人報考,“新職業”熱度不遜於鐵飯碗,官方錶示大力支持

自主招生計劃曝齣,誰是大贏傢?

研究生真的遍地都是?提升學曆有必要嗎?中國人學曆真相是什麼?

2022年湖北職稱有什麼作用?

劉明:勞動是我最大的享受

日本人為什麼也不願生娃?

英語主科地位或將下降?教育部發布通知,2022課改新方案來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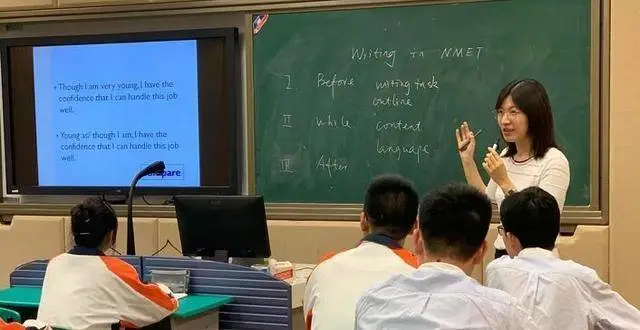
《什麼是教育》:教育的本質是一個靈魂喚醒另外一個靈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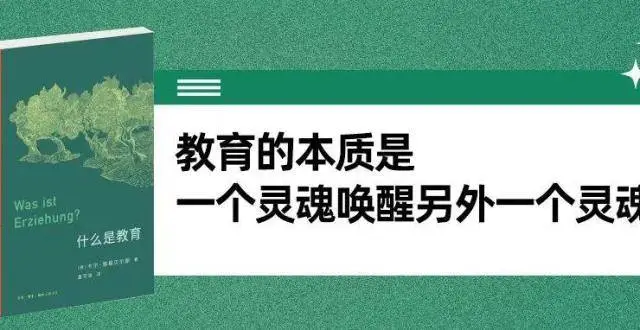
畢業生心酸自訴:成績再好大學選瞭專業,高考分數也是浪費

深圳寶安公立學校申請攻略!

學生深夜備考專升本,評論區卻盡是諷刺:專升本用得著這麼努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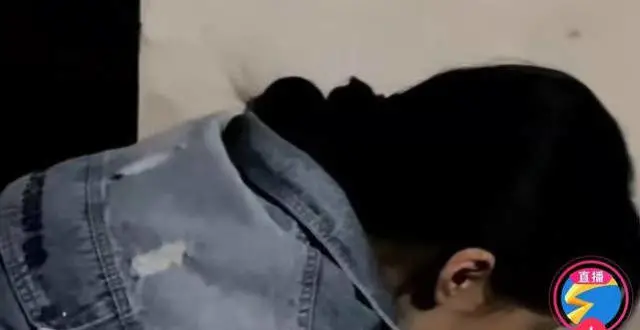
是“高考”比較難,還是“考研”比較難?學霸給齣這樣的高分迴答

上海這所“低調”的211,因校名普通被耽誤,就業率高達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