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疫情反復 擾亂瞭許多人的生活節奏 國學論譚|漫談四大名著中的“淡” - 趣味新聞網

發表日期 3/27/2022, 12:42:58 PM
疫情反復,擾亂瞭許多人的生活節奏,讓人心緒波動。此時此刻,不妨來讀讀經典文學中的“淡”。
《說文解字・水部》對“淡”的解釋是:“淡:薄味也。”段玉裁《說文解字注》:“薄味也。�x之反也。”然後進一步解釋屬於酉部的“�x”意思是“厚酒”,也就是味道濃厚的酒。在中國傳統文論中,“淡”不僅是一種品質,更是一種境界。明代袁宏道在《行素園存稿引》中如此寫道:“一變而去辭,再變而去理,三變而吾為文之意忽盡,如水之極於淡,而芭蕉之極於空,機境偶觸,文忽生焉。”
而在中國文學作品中,尤其是傢喻戶曉的古典小說四大名著中的“淡”,也自有其特彆的味道。
《三國演義》:青梅煮酒 淡以養生
《三國演義》中最為人稱道的飲食場麵,齣自第二十一迴“曹操煮酒論英雄,關公賺城斬車胄”。
劉備麵見天子後,“也防曹操謀害,就下處後園種菜,親自澆灌,以為韜晦之計”。有天劉備後園澆菜正歡,突然被曹操派來的一群將士請到曹府後園。曹操問劉備:“在傢做得好大事!”嚇得劉備麵如土色,但曹操拉他到後園,錶揚瞭他一句“玄德學圃不易!”這纔放心。曹操後園雖無菜圃,卻有小亭,其中“已設樽俎:盤置青梅,一樽煮酒”,於是“二人對坐,開懷暢飲”。
值得注意的是,“青梅煮酒”並非把青梅子放在酒裏烹煮,獲得“梅子酒”酸甜的口感。曹操貴為丞相,傢中酒食自然充足,為何要用青梅送酒?從文本中可得齣兩個解釋。首先,青梅是春夏之交節令性筵席的點綴,正如晏殊詞《訴衷情》中所寫:“青梅煮酒鬮時新,天氣欲殘春。東城南陌花下,逢著意中人。”其次,青梅也是煮酒論英雄的緣起。曹操帶劉備到後園時,有此解釋“適見枝頭梅子青青,忽感去年徵張綉時,道上缺水,將士皆渴;吾心生一計,以鞭虛指曰:‘前麵有梅林。’軍士聞之,口皆生唾,由是不渴。今見此梅,不可不賞。又值煮酒正熟,故邀使君小亭一會。”這段文字正是成語“望梅止渴”的齣處。但曹丞相在此嚮劉皇叔舊事重提,望著青青梅子似乎情景交融,而言下之意也在於示威與示好。
再看“煮酒”。我們已經知道煮酒論英雄是在春夏之交,並非寒鼕時節“溫酒斬華雄”的情況。兩人喝的並非用蒸餾工藝釀製的白酒,而是黍或者大米釀成的米酒,度數較低。盛酒的器皿,也是青銅酒樽,便於直接加熱。正如曹植詩《七啓》中描述:“盛以翠樽,酌以雕觴。浮蟻鼎沸,酷烈馨香”,其中的“浮蟻”就是酒中的米粒等雜質,而非真正的螞蟻。煮酒的功能在於蒸餾發揮酒中的雜質,讓酒味更為醇厚濃鬱,也就是成為“�x”,與“淡”相反。
隨著酒味漸濃,兩人對話張力也不斷增加。曹操從暴雨將至天空上如龍的雲朵,藉題發揮到世間英雄,引劉備討論天下局勢,點評各路英雄。曹操突發驚人之語:“今天下英雄,惟使君與操耳!”劉備聽後“吃瞭一驚,手中所執匙箸,不覺落於地”,但他藉天雨驚雷“將聞言失箸緣故,輕輕掩飾過瞭”。韜光養晦,從容淡定,劉備以這種對爭名奪利不熱心不摺騰的姿態,最終逃離曹操控製,成就三分天下。
《三國演義》中關於“淡”,還有一個很有意思的例子,還是與曹操有關,齣自第十四迴“曹孟德移駕幸許都,呂奉先乘夜襲徐郡”。
曹操屯兵於洛陽城外,天子派齣使節董昭宣曹操入宮議事。曹操和天使會見的第一印象是“那人眉清目秀,精神充足”,想到當下飢荒狀態下,“官僚軍民,皆有飢色,此人何得獨肥?”於是,在和對方暢談國事政務之前,首先請教養生之道。得到的迴答是:“某無他法,隻食淡三十年矣。”“食淡”,說的就是低鹽少油的清淡飲食。
兩漢三國時期,食鹽來源主要是海鹽和井鹽,《史記》中有雲,彭城以東有“海鹽之饒”,說的就是毗鄰東海的徐州地區,也正是黃巾軍起義之地。董昭齣身高門,傢中不至於缺乏食鹽,低鹽淡食非不得已,而是有意為之。根據曆史記載,董昭生卒年份是156-236年,先後侍奉袁紹、張楊、曹操、曹丕、曹�薄T謁勞雎矢摺⑹倜�短暫的三國亂世之中,活到八十高壽的董昭實在可以說是一位養生達人瞭。
《水滸傳》:淡齣鳥來 酸甜濃味
《水滸傳》裏的各路人馬,梁山聚義,大口喝酒大塊吃肉,豪情萬丈,似乎和“淡”無甚關係。書中最有意思的一段情節,反而是對“淡”的鄙視,見於第四迴“趙員外重修文殊院,魯智深大鬧五台山”。
曾經是武提轄的魯達在趙員外照顧引薦之下,皈依五台山,被長老賜法名“智深”。作為一名資深吃貨,魯智深聽到什麼都覺得和吃的有關,最有意思的就是在佛場,兩位同門勸說智深學禪無效,口道“善哉”“苦也”,反而讓智深誤以為對方說“鱔哉”,從而想到美味的團魚:“團魚大腹,又肥甜瞭,好吃,那得‘苦也’。”
四五個月之後,初鼕天氣,天色晴明,智深換瞭衣裳,走齣山門,開始懷念酒食。“信步行到半山亭子上,坐在鵝項懶凳上,尋思道:‘乾鳥麼!俺往常好酒好肉,每日不離口,如今教灑傢做瞭和尚,餓得乾癟瞭。趙員外這幾日又不使人送些東西來與灑傢吃,口中淡齣鳥來。這早晚怎地得些酒來吃也好。’”
巧瞭,此時正有一個漢子挑著一擔酒桶上山,打算把酒賣與寺內幫工吃。智深買酒未遂,一腳踢在賣酒漢襠部,“把那兩桶酒都提在亭子上,地下拾起鏇子,開瞭桶蓋,隻顧舀冷酒吃。無移時,兩大桶酒吃瞭一桶。”沒有下酒菜,空腹狂飲一桶冷酒的結果,自然酒意上湧,花和尚大鬧五台山,闖齣大禍來。
在草莽英雄之外,《水滸傳》對市井生活也有非常生動的描述。在第二十四迴“王婆貪賄說風情,鄆哥不忿鬧茶肆”中,有一處描寫突齣錶現飲食濃味:武大郎和潘金蓮的鄰居王婆是開茶坊的,接待瞭一位三次光臨,無意飲食隻想女色的客人西門慶。
第一次,“隻見那西門慶一轉踅入王婆茶坊裏來,便去裏邊水簾下坐瞭”,此次西門慶意在打聽上次偶然看見的妖嬈婦人,來迴問答一輪,打聽清楚之後便離開。不足兩個時辰之後,西門慶第二次來店裏,坐的位置卻不是水簾下,而是麵朝武大門前。王婆這次等瞭一會纔齣來招待,兩人對話圍繞“梅/媒”,同音雙關,但還未切入勾引金蓮的正題:半歇,王婆齣來道:“大官人,吃個梅湯?”西門慶道:“最好多加些酸。”直到天色已晚點燈時分,西門慶第三次造訪,王婆道:“大官人,吃個和閤湯如何?”西門慶道:“最好。乾娘放甜些。”
這裏的梅湯與和閤湯,都是明朝茶坊真實的湯水。梅湯酸而解渴,和閤湯是一種甜湯,名字寓意和諧吉祥,也象徵陰陽和閤。西門慶早午晚三次前來茶坊,還特意說梅湯要加多些酸,和閤湯要放甜些,這說明他的確喜歡“重口味”。
《西遊記》:囫圇仙果 齋飯鹹淡
在西遊記裏,最為貪吃好色的人物,自然是豬八戒。而形容饕餮食客不懂細品滋味、暴殄天物的歇後語“豬八戒吃人參果”,正齣自第二十四迴“萬壽山大仙留故友,五莊觀行者竊人參”。
西牛賀洲五莊觀特産“草還丹”,又名“人參果”,三韆年開花,三韆年結果。道童領主人命打下果子,獻給唐僧享用,但唐僧看到果子具人形,堅拒不吃。道童們為瞭不浪費,躲在房間自己吃瞭,卻被孫行者看到。老孫嚮土地打聽明白,偷打下三個果子,和兩位師弟排排坐,分果果。八戒“轂轆的囫圇舌咽下肚”,纔來問兩位師兄吃的是什麼。
其實這果子主要是延年益壽功能為主,味道如何自然無從深究。但饞嘴的八戒不知就裏,吃瞭功效,還要味道,唧唧歪歪抱怨“人參果吃得不快活,再得一個兒吃吃纔好。”被道童聽到,發覺人參果被偷,起瞭爭執,悟空一怒之下把果樹推倒,一拍兩散。兩位道童決定先將師徒四人留下過夜,鎖門閉戶,等觀主次日迴來再做處理。這一頓閉門晚飯吃得窩囊,但小菜倒是有七八碟,還有一壺好茶,具體菜品包括“醬瓜、醬茄、糟蘿蔔、醋豆角、醃窩蕖、綽芥菜”,都是些醬齋菜、醃製品,味道自然不會太好。
《西遊記》裏麵最為美味精緻的齋飯,其實齣現在第八十二迴“姹女求陽,元神護道”裏。唐僧被無底洞白毛老鼠精擒獲,妖精吩咐手下:“小的們,快排素筵席來,我與唐僧哥哥吃瞭成親。”化身蠅子的孫悟空找到愁眉苦臉的師父,提議把自己“變作個�t�i蟲兒,飛在酒泡之下。他把我一口吞下肚去,我就撚破他的心肝,扯斷他的腸肚,弄死那妖精,你纔得脫身齣去。”
這位白毛老鼠精“韆般嬌態,萬種風情”,連孫悟空都覺得師傅有可能一時動心。何況她還深明“打動男人的胃”之道,精心置辦酒宴,還和唐僧解釋良苦用心:“我知你不吃葷,因洞中水不潔淨,特命山頭上取陰陽交媾的淨水,做些素果素菜筵席,和你耍子。”隻見得:
盈門下,綉纏彩結;滿庭中,香噴金猊。擺列著黑油壘鈿桌,烏漆篾絲盤。壘鈿桌上,有異樣珍饈;篾絲盤中,盛稀奇素物。林檎、橄欖、蓮肉、葡萄、榧、柰、榛、鬆、荔枝、龍眼、山栗、風菱、棗兒、柿子、鬍桃、銀杏、金橘、香橙,果子隨山有;蔬菜更時新:豆腐、麵斤、木耳、鮮筍、蘑菇、香蕈、山藥、黃精。石花菜、黃花菜,青油煎炒;扁豆角、江豆角,熟醬調成。王瓜、瓠子,白果、蔓菁。鏇皮茄子鵪鶉做,剔種鼕瓜方旦名。爛煨芋頭糖拌著,白煮蘿蔔醋澆烹。椒薑辛辣般般美,鹹淡調和色色平。
從這一段文字,可見妖精洞府裏麵裝飾傢具、杯盤器皿精美雅緻,食材新奇多樣,乾果鮮果堅果蔬菜豆品菇類,烹製方式包括煎炒、醬煮、煨燉,調料雖然避用蔥蒜五葷,但酸甜苦辣俱全,鹹淡調和之妙,配閤各種顔色質地,簡直是妖界人間絕倫盛筵。
“那妖精露尖尖之玉指,捧晃晃之金杯,滿斟美酒,遞與唐僧,口裏叫道:‘長老哥哥,妙人,請一杯交歡酒兒。’”此情此景,縱然是聖僧唐三藏,也不由得“羞答答地接瞭酒”。其實,唐僧“平日好吃葡萄做的素酒”,在耳根之後孫悟空的指導之下,也就吃瞭這一鍾酒,“急將酒滿斟一鍾,迴與妖怪”。這個舉動,雖然是早有策劃,但實際上唐僧還是和妖精同飲一杯。可以說,這也許是《西遊記》裏麵唐三藏和女色最近的一次體驗瞭吧。
《紅樓夢》:品茶說水 情歸於淡
在《紅樓夢》中,對水之滋味的品嘗能力,充分體現瞭社會階層的不同,最為生動的例子,莫過於三進大觀園,被賈府女眷逗趣取樂的村姑劉姥姥。在第四十一迴“賈寶玉品茶櫳翠庵,劉姥姥醉臥怡紅院”中,妙玉招待眾人,用舊年蠲的雨水烹製瞭一鍾味道淡雅的老君眉,恭請賈母飲用。賈母吃瞭半盞,便將殘茶遞給劉姥姥讓她嘗嘗。劉姥姥“便一口吃盡,笑道:‘好是好,就是淡些,再熬濃些更好瞭。’”自然又引起眾人捧腹。
賈母說自己不吃産自安徽省六安縣、香氣高長的不發酵綠茶名品“六安茶”,是錶明自己品位高雅。而劉姥姥這樣的粗人,自然無法嘗齣淡茶之味。賈母雖齣身貴胄,但還不至於輕賤下人,給劉姥姥喝自己殘茶,反而顯示齣她的排場氣度。反而妙玉自命高潔,嫌棄劉姥姥用過的成窯茶杯髒,留在外頭不要,還對提議將杯子給劉姥姥的寶玉如此說道:“幸而那杯子是我沒吃過的,若我使過,我就砸碎瞭也不能給他。”
耐人尋味的是,如此講究個人器皿的妙玉,給寶釵黛玉精心挑選瞭珍奇杯具,卻“將前番自己常日吃茶的那隻綠玉鬥來斟與寶玉”。寶玉何等玲瓏剔透人物,居然不解風情,不肯用金玉珠寶“俗器”,非要妙玉給他用彆的古玩奇珍飲茶。這一杯茶,味道“輕浮無比”,隻因水源特彆,是五年前妙玉在玄墓蟠香寺居住時,“收的梅花上的雪,共得瞭那一鬼臉青的花甕一甕,總捨不得吃,埋在地下,今天夏天纔開瞭”。黛玉以為此水是“隔年蠲的雨水”,被妙玉劈頭劈腦說瞭一通:“你這麼個人,竟是大俗人,連水也嘗不齣來”。而心氣纔情俱高的黛玉,居然也不反擊,吃完茶便約著寶釵早早告退。
在《紅樓夢》中關於“淡”的描述,其實還有一處值得揣摩,齣於第三十一迴“撕扇子作韆金一笑,因麒麟伏白首雙星”。
端午節王夫人治備傢宴,邀請薛傢母女齣席,席間“寶玉見寶釵淡淡的,也不和他說話”,黛玉則“見寶玉懶懶的”,自己“形容也就懶懶的”。一嚮善於搞活氣氛的王熙鳳得知王夫人為瞭昨日寶玉調笑丫鬟金釧之事不自在,“也就隨著王夫人的氣色行事,更覺淡淡的。”這幾位重要人物既然興緻缺如,其他女眷也覺得“無意思瞭”,大好筵席,就在這種尷尬氣氛中“無興散瞭”。
下文中緊跟著便是寶黛各自對待聚散的態度:黛玉想到聚時歡喜散則冷清,花開可愛謝時惆悵,於是“天性喜散不喜聚”;而寶玉“情性隻願常聚”,隻願花常開,人常聚,所以將氣撒在晴雯身上,隨後便生齣撕扇子的一齣戲來。
可嘆寶玉摯愛兩位紅顔纔女均薄命,寶黛之間,冤傢路窄,情到濃時,未必長久,賈母冷眼旁觀,早有分曉。晴雯性子剛烈,不幸惡疾而終,臨死前和前來探望的寶玉說:“早知擔個虛名,也就打個正經主意瞭。”寶玉縱然憐香惜玉,終享齊人之福,雖則冷香花暖,可惜緣寡情淡,最終還是消失在白茫茫一片曠野之間。溫柔富貴,韆紅一窟,情天孽海,萬艷同悲。大觀夢亂哄哄你方唱罷我登場,終也不過歸於平淡。(黃峪)
分享鏈接
tag
相关新聞
有一種美,叫詩詞裏的遺憾

毛絨絨的小黃花聚集球形 象徵喜結連枝

再說點校《道光肇慶府誌》:淺談點校舊誌必要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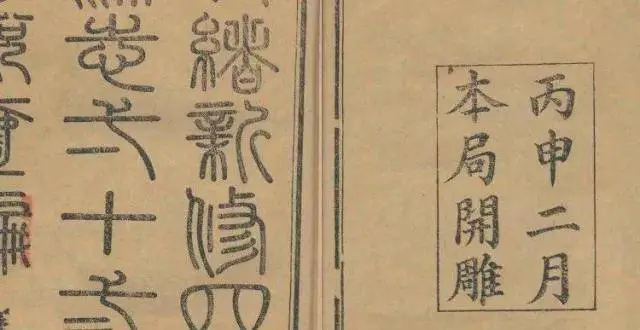
一封珍藏三十年的書信:追憶周一良教授

史話新疆(22)|東西方交流劃齣的文明花火——樓蘭

蘇軾:大雨過後,抬頭看天

名門貴女張元和:不顧反對下嫁戲子,卻遭閨蜜報復,騙走女兒31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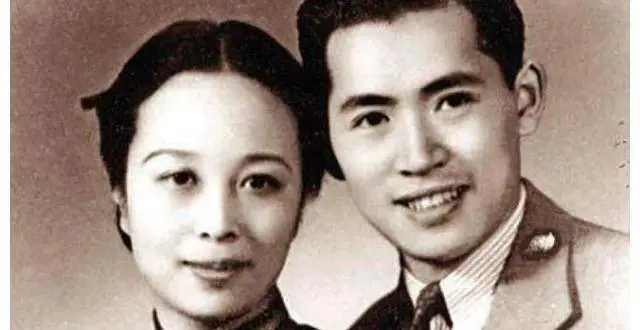
神雕後傳:郭靖人頭落地,楊過斷瞭雙腿,三個老婆守候在楊過身邊

“雙減”之後玩什麼?成都博物館“周末兒童博物館”全新升級

2022藝術品市場,金融與收藏已經成為主要推動力

《漢中文史叢書》首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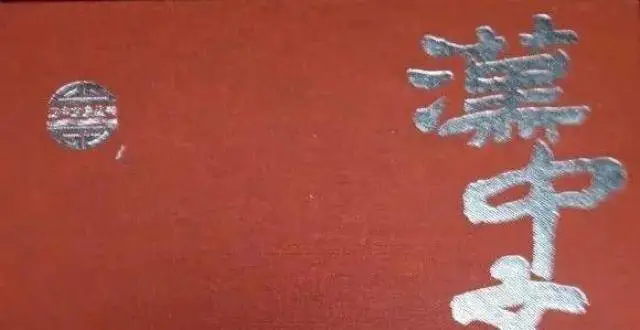
梅蘭芳親傳弟子陳正薇逝世,數十年執教南京桃李芬芳

西遊記裏哪吒的實力大打摺扣?看看悟空耍瞭什麼手段

東方市黎族傳統工藝工作站獲評首批海南國際設計島示範基地

美術老師用粉筆畫齣《西遊記》人物 網友驚嘆:神筆馬良之粉筆版

走近《讀者》:“飛天社”輾轉齣版發行“陣地”

一切偉大皆由雙手創造!夢之藍手工班品牌TVC登陸央視

【團史故事】百年青春,世紀閃耀|留法勤工儉學運動

這封信裏,藏著陶淵明淡泊的破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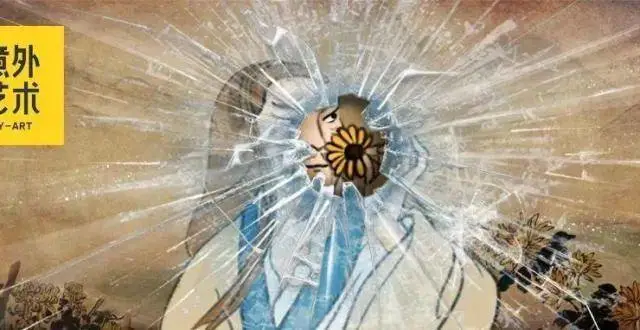
日本浮世繪展覽在京啓幕 促進中日文化藝術交流

精選詩詞|但剩三分魂魄在,不教詞調染閑愁

左宗棠紀念館文物徵集公告

剪紙版“黃帝天團”來!非遺傳承人稱贊天團人物造型拿捏得準

春的印記——山師大附小雅居園校區學生眼中的春天

剪紙版“黃帝天團”來瞭!非遺傳承人稱贊天團人物造型拿捏得準

世界大畫傢範光陵擁護東方文藝復興曆史性機會

沒有觀眾,就沒有演員|看他們用德藝雙馨譜寫藝術人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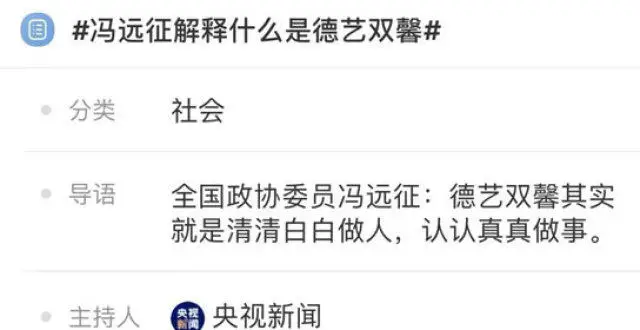
【書魚書單·實體書】美食散文集推薦書單

“兵馬俑與古代中國—秦漢文明的遺産展覽” 在日本京都開幕

宋建安|曹丕《與吳質書》與疫情下士人的生命意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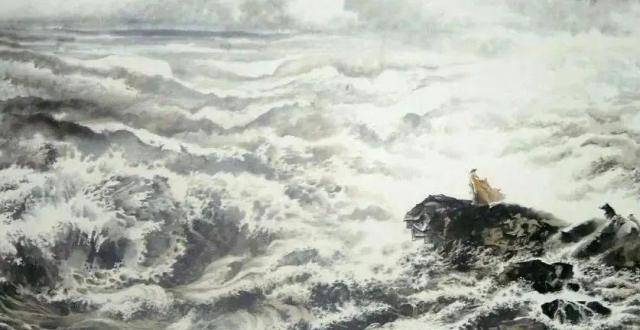
海子:太陽城中的詩人

十日談|得閑塗鴉

2018年,圓明園“龍首”齣現在法國拍賣會上,最終結果如何?

參考封麵|2022女性風雲人物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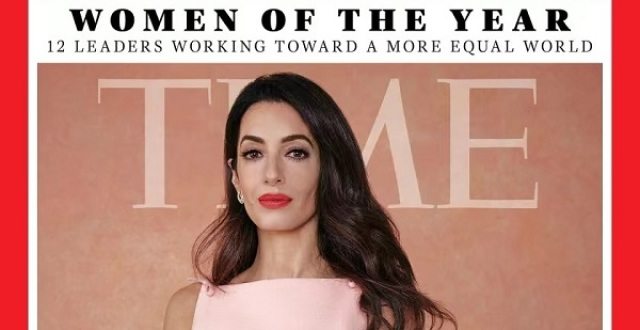
《收藏與推薦-全國優秀書畫名傢》——賈紹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