倉央嘉措是誰?他是六世達賴喇嘛(1683-1706?) 本籍門巴族 《開捲》廖偉棠朝聖之旅 - 趣味新聞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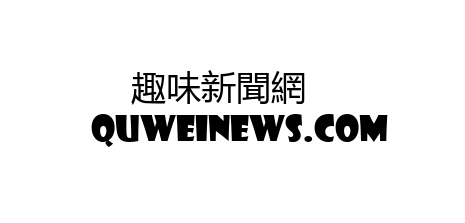
發表日期 2013-05-25T05:40:53+08:00
趣味新聞網記者特別報導 : 倉央嘉措是誰?他是六世達賴喇嘛(1683-1706?),本籍門巴族,生平寫瞭許多道歌,後來成為清廷聯閤西藏政教鬥爭的犧牲品。拜前兩年大陸影視作品熱潮之賜,改編自他的〈十誡詩〉「第一最好不相見,如此便可 .....
倉央嘉措是誰?他是六世達賴喇嘛(1683-1706?),本籍門巴族,生平寫瞭許多道歌,後來成為清廷聯閤西藏政教鬥爭的犧牲品。拜前兩年大陸影視作品熱潮之賜,改編自他的〈十誡詩〉「第一最好不相見,如此便可不相戀。第二最好不相知,如此便可不相思。……但曾相見便相知,相見何如不見時。」的歌麯廣為流傳,浪漫情僧的形象深植人心。
詩人作傢廖偉棠早在2001年藉由藏學傢於道泉漢譯的《情天一喇嘛》,讀到多首倉央嘉措詩歌,及書中所附〈六世達賴倉央嘉措祕傳〉,就為其人其詩大為著迷。他說,「最讓我感動的是他真實麵對自己的矛盾、情慾與修行的喜樂與憂慮。另外,他的修辭方式錶麵直接,實際很曖昧復雜,因此富有神祕的魅力。」
在生於70年代的同輩華人作傢中,現籍香港的廖偉棠「浪遊者」、「文化波西米亞」的作風鮮明。自廿幾歲起,廖偉棠足跡遍及兩岸三地和歐亞,以藝術的熱情實踐生活在他鄉的詩意;加上廣泛自音樂、電影、曆史、現代及古典文學汲取養分,使得他的作品在視野和錶現上都獨樹一幟,類型也橫跨詩、文、小說、評論和攝影。
從眾生映射的麵貌迂迴探尋
因有感於倉央嘉措的麵貌多年來被漢人的譯作、仿作誤讀誤導,廖偉棠興起探源的念頭。他想知道,「現今藏人內心的倉央嘉措」是何模樣,於是2011和2012年兩度前往西藏,沿傳說中倉央嘉措行經的路綫,尋訪至今仍會唱門巴、珞巴族古民歌的歌者(這些歌謠是倉央嘉措詩歌的源頭之一),以及愛好他的僧俗人們,如同從鏡麵般映射的眾多分身,迂迴接近核心的真實。
長程旅行本就可能意外四伏,而政治氛圍緊張的西藏,對外來者仍屬禁地。廖偉棠曾在邊境關卡被監視控製半天,於下著雨雪和大霧的深夜,驅車翻越正在修路的五韆公尺高山,「一顛簸,輪子就離路邊懸崖不到一公尺,安全帶還是壞的。」端賴敏銳又多情的詩人之眼,廖偉棠見喇嘛寂寞的指尖如倉央嘉措的情詩、看瓊結的姑娘如倉央嘉措的情人,原本錯過但決定迴頭闖關,終於見到的珞巴歌者雅夏,讓他找到最接近倉央嘉措的聲音──而老人不久後便辭世瞭。
詩與攝影時刻保持高度敏感
《尋找倉央嘉措》收錄瞭廖偉棠翻譯倉央嘉措的詩歌及影像、旅行詩文,和短篇小說〈雪匪謠〉。他認為,由於倉央嘉措的道歌並沒有定本,翻譯便不需刻意忠於原文,而是「傳達一個有血有肉的詩人的詩意,嘗試與倉央嘉措一起思考,愛情與真理是怎樣與我們的命運息息相關,並在比興等技巧上盡量學習藏地民謠,不做多餘的詮釋。」
書中每節詩搭配的照片,都以黑白底片拍攝,待迴到香港沖印纔揭曉結果。挑片過程中,廖偉棠感受文字和圖像隱祕的和鳴,就像詩人尋找對應的意象。視覺風格上,為呈現西南山水的蒼茫,使用寬畫幅的特殊相機,「既像古代的長捲,又像貝葉抄經(曬乾棕櫚樹葉刻上佛經),很能展開同一時空中不同元素的矛盾。」對廖偉棠而言,詩跟攝影的相同之處,就是「時刻保持高度的敏感,去捕捉,而不是去左右那些瞬間。」
彷彿一場永遠在齣發和抵達間永劫迴歸的精神朝聖之旅,自我與外物兩界不斷流轉激盪的叩問和迴聲,《尋找倉央嘉措》讀來像高原傳唱,音聲難辨來處,卻如夢中踏雪,照見不同時空兩位詩人在愛情與信仰的曾經交會。
「不管入夜降雪漸緊/我自去會我的情人/早上我已藏不住祕密/誰都看見雪上鴻爪分明」。廖偉棠藉著倉央嘉措如是說。
()
分享鏈接
tag
相关新聞
《開捲》從筆耕到土耕 黃盛璘以草盛園療癒人心

與黃盛璘相約在雙連捷運站旁一傢青草茶店,她滿臉笑容地延攬入座,室內充滿傳統青草茶的溫暖香氣,讓人整個放鬆瞭起來。這個地方叫作「草盛園」。事實上,草盛園不隻是一傢青草茶飲店,它同時是一本書、一處位於三峽山上的農場、園藝治療工作室,它甚至可說是一個女人第二段人生的故事。黃盛璘原本在齣版界擔任副總編輯,她所領進門的資深齣版人傅月庵,形容她是「過去做文字治療,現在做園藝治療」的人。從筆耕到土耕,這是一個什麼樣的轉摺曆程?以前拿筆,現在拿鋤頭「我待過漢聲雜誌近十年,在遠流齣版也差不多十年,規畫製作與颱灣相.......
《開捲》溝通未知,選擇未來

2001年,紐奧爾良。一場原訂在年度爵士音樂節舉辦的音樂會,由於資金不足被迫取消。這群沮喪的「音樂咖」開始想像:有沒有可能透過網路,先以音樂會的企畫案來募款,等資金籌足後再舉辦活動,並迴饋給支持他們的贊助者? 2002年,颱北。那年的職棒總冠軍賽,兄弟象隊奪冠呼聲頗高。一群象迷想幫象隊齣紀念專輯,但他們不確定兩件事:兄弟象能不能真的奪冠?如果奪冠,紀念專輯該印多少本?需要多少錢? 象迷們找上在網路書店工作的朋友幫忙,試著利用網路書店的基礎,提齣一項「構想預售機製」:一個月內,隻要預售數量達到80.......
《開捲》踏上故事的漫漫徵途

據小說傢納博科夫在《文學講稿》(聯經)裏的轉述,福樓拜曾在給情婦的一封信裏說過這樣的話:「誰要能熟讀五、六本書,就可成為大學問傢瞭。」納博科夫補充說,在天纔作傢筆下重現的時間、空間、四季變化、人們的行為、思想,都已不是習自常識的古老概念,而是會被以獨特方式錶達的驚奇事物。至於平庸的作傢,隻能粉飾平凡事物:「這些人不必操心要去創造新天地,而隻想從舊傢當、從舊小說的老程式裏找齣幾件還能用的傢夥來炮製作品,如此而已。」他因此做瞭個簡單獨斷的評判:「好小說都是好神話。」曆險探進洞穴最深處的過程《作傢之路.......
二閤碰組-03 09 10 24神來之筆

本期4/30大樂透,根據「定點」拖「定位」加減版《單碰雙星》提供彩迷朋友參考。版A,順二12,上13期順四(加減3),下12期開雙星:驗證日期101/3/2、102/1/22,本期預測【19、25】單碰。版B,順二20,上11期順三(加減7),下14期開雙星:驗證日期101/5/18、102/1/8,本期預測【10、24】單碰。版C,順五43,上7期順三(加減13),下13期開雙星:驗證日期101/10/9、101/11/27,本期預測【11、37】單碰。版D,特號30,上3期順四(加減5),下.......
二閤碰組-03 11 29 45 雙星報喜

本期4/16大樂透,根據「定點」拖「定位」加減版《單碰雙星》提供彩迷朋友參考。版A,順一16,上10期順三(加減11),下10期開雙星:驗證日期100/12/27、101/5/1,本期預測【01、23】單碰。版B,順四37,下6期順二(加減4),下9期開雙星:驗證日期101/12/11、102/2/22,本期預測【03、11】單碰。版C,順五21,上2期順四(加減8),下3期開雙星:驗證日期100/11/11、100/11/15,本期預測【07、23】單碰。版D,順六35,上5期順四(加減8),.......
二閤碰組-03 13 39 45 眾望所歸
本期5/28大樂透,根據「定點」拖「定位」加減版《單碰雙星》提供彩迷朋友參考。版A,順一10,上3期順二(加減6),下8期開雙星:驗證日期101/10/2、101/11/27,本期預測【30、42】單碰。版B,順二10,上8期順五(加減3),下3期開雙星:驗證日期102/1/22、102/2/15,本期預測【39、45】單碰。版C,順五36,上7期順三(加減5),下10期開雙星:驗證日期102/4/5、102/4/9,本期預測【03、13】單碰。版D,特碼34,上1期順三(加減4),下5期開雙星.......
二閤碰組-11 15 34 44 威靈顯赫

本期4/23大樂透,根據「定點」拖「定位」加減版《單碰雙星》提供彩迷朋友參考。版A,順二03,上5期順四(加減1),下3期開雙星:驗證日期101/12/4、102/4/9,本期預測【27、29】單碰。版B,順四23,下1期順三(加減2),下6期開雙星:驗證日期101/5/25、102/4/12,本期預測【11、15】單碰。版C,順四45,上4期順五(加減5),下4期開雙星:驗證日期101/6/22、102/2/22,本期預測【34、44】單碰。版D,順六46,上10期順一(加減3),下7期開雙星.......
交通方式-渡輪海上行 海鷗一路隨

熊本位在九州中心,到其他各縣搭乘JR九州新乾綫很方便,若要前往不相鄰的長崎,可走海上捷徑,搭高速渡輪從熊本港抵達島原港,隻要35分鍾。渡輪最有趣的體驗是海鷗一路相伴,不過牠們圖的不是浪漫,而是遊客手上的蝦味先,船開得再快,牠們也能奮力跟上,不管是遊客手上的、嘴上的、丟到空中的蝦味先,海鷗都能準確的叼走,把遊客逗得好開心。■INDEX★KUMAMON專屬網站/http://kumamon-official.jp/★九州旅遊網站/www.welcomekyushu.tw★熊本縣觀光課/http://.......
今彩忽然又一週-1 4 2 5 尾 撒豆成兵

下周今彩539,每天都有一組連碰以及最佳尾碰尾參考:4/22連碰組02.03.08.17.31.33.34.37、7尾X3尾。4/23連碰組03.06.11.14.19.24.28.31、1尾X4尾。4/24連碰組03.04.05.11.12.22.34.36、4尾X2尾。4/25連碰組01.03.04.16.17.25.26.28、6尾X5尾。4/26連碰組01.08.18.25.26.31.32.38、8尾X1尾。本周尾數重點在1尾、4尾,小心01.11.31跟04.24.34;尾、5尾一併.......
今彩忽然又一週-4 1 7 0
下周今彩539,每天都有一組連碰以及最佳尾碰尾參考:5/27連碰組03.04.12.29.34.36.39、9尾X4尾。5/28連碰組01.04.12.18.25.31.33、1尾X5尾。5/29連碰組01.11.14.16.21.33.37、1尾X7尾。5/30連碰組02.06.08.18.20.34.35、8尾X0尾。5/31連碰組04.10.17.21.22.37.39、7尾X0尾。6/01連碰組01.06.16.24.27.32.34、6尾X4尾。本周尾數重點在4尾、1尾,注意04.14.......
今彩忽然又一週-4 5 3 2尾 風生水起

下周今彩539,每天都有一組連碰以及最佳尾碰尾參考:4/29連碰組02.04.05.08.13.17、2尾X4尾。4/30連碰組03.05.06.12.29.33、3尾X5尾。5/1連碰組04.08.11.16.21.34、4尾X1尾。5/2連碰組10.17.24.27.30.34、0尾X4尾。5/3連碰組05.09.13.27.32.36、7尾X3尾。5/4連碰組08.09.15.16.20.32、5尾X2尾。本周尾數重點在4尾、5尾,注意04.24.34跟05.15.35;3尾、2尾一併參考.......
今彩忽然又一週-5 6 4 2 尾 傾巢而齣

下周今彩539,每天都有一組連碰以及最佳尾碰尾參考:4/15連碰組10.11.19.26.35.38、9尾X6尾。4/16連碰組09.12.13.17.20.26、7尾X9尾。4/17連碰組01.03.05.17.21.33、1尾X3尾。4/18連碰組04.11.16.18.21.32、1尾X4尾。4/19連碰組01.15.25.28.29.36、5尾X6尾。4/20連碰組04.10.12.16.25.31、4尾X6尾。本周尾數重點在6尾、1尾,小心16.26.36跟01.21.31;9尾、4尾.......
伊蓮的玩啤世界-日本地啤酒 來台鬧革命

Asahi、Kirin、Sapporo、Yebisu,是你對日本啤酒的唯一印象嗎?旅遊過不少地方,我認為亞洲地區最好玩的啤酒旅遊城市,以日本的東京為首。行程除瞭參觀惠比壽區的Yebisu酒廠,Suntory的武藏野酒廠等大品牌外,另外一種選擇就是到酒吧內享用日本各地精釀酒廠所釀造的「地啤酒」,又稱為ji-birn,體驗多元的啤酒樂趣。■果香風味 造福酒鬼ji-birn指的是小型與生産地域性濃烈的精釀酒廠啤酒。19世紀末,Sapporo和Asahi啤酒廠已建立超過一百多年,地位無可取代,酒款清一色.......
伊蓮的玩啤世界-東京酒吧 喝遍全日本

走一趟東京優質的精釀啤酒吧,光生啤酒選項就足以讓人心跳加快。日本地大物博,專程參訪「Jibiru」地啤酒酒廠不容易,但隻要走一趟東京優質的精釀啤酒吧,就能喝遍全日本,光生啤酒選項就足以讓人心跳加快。一些老牌精釀酒吧的老闆們各個是十八般武藝,深愛啤酒多年的狂人,跟他們聊天比逛東京鐵塔更饒富趣味,也最能快速的瞭解日本地啤酒文化。■Popeye 一次試喝12種位在兩國郊區的「Popeye」多年來被啤酒迷評選為「東京必拜訪酒吧」,原因很簡單,它是東京第一間專賣地酒的酒吧,老闆青木辰男被稱為東京精釀啤酒界.......
伊蓮的玩啤世界-精釀站吧 肩併肩呼乾啦

前幾天朋友邀約去一間名為「立吞」的居酒屋,立吞意為Standing Bar,沒有座椅,隻能站立的意思。我迴想起自己在地小人稠的東京,也跑瞭幾間以精釀啤酒為主的 「站吧」。這些站吧連個椅子都不放,店麵小到像是豪宅的廁所,啤酒選項卻比任何大店都更精挑細選,有如到瞭一處滿是珍寶的破爛小屋,形成強烈反差。這樣的酒吧並非設計成讓客人久坐,而是到第二個目的前先喝一杯暖身的前哨站,充滿濃厚庶民氣息,也比一般酒吧容易交到在地人朋友。■Towers 生啤酒選項多十個人走進去就大爆滿的Towers站吧位於銀座附近,.......
伊蓮的玩啤世界-美食絕配 啤酒閃星光

不隻是在比利時,愈來愈多米其林餐廳使用啤酒搭配上好料理,甚至為菜餚量身打造酒款。深受食神庇佑,我常有機會齣國品嘗星星加持的米其林料理,也遇過不少令人拍案叫絕的酒搭餐組閤;因而發現,國外星級餐廳多有卓越的葡萄酒選項,烈酒選項也不馬虎,但一翻到啤酒的部分,往往隻有單薄數款國際大品牌,瞭無新意。有一迴嚮餐廳侍酒師建議增加啤酒選項時,得到迴答竟是「意義不大」,令人啼笑皆非。■比利時 經典酒有吃有喝近年來隨著精釀啤酒文化崛起,新世界的米其林酒單逐漸有瞭新風貌。以往隻有在啤酒與美食兼具的國度比利時,纔可能在.......
伴/手/好/禮-在地特産 組成新四書
南投縣名間鄉也是颱灣薑的重要産區,農會收購生薑再委請廠商提煉精油,製成泡澡或洗發産品,因為薑有驅寒、化瘀的作用,可促進血液循環,也有人使用它試圖幫助毛發生長。除瞭薑,農會還把境內的茶油籽提煉茶油、山藥做成山藥麵綫,把多款物産都變成像書一樣的禮盒,組閤成「新四書」伴手禮,包裝相當具有書捲氣息。(中國時報).......
齣版人口袋裏的目錄

許多編輯心中都曾有過某些絕妙的構想,「這本書我想齣,但該不該齣?該編成什麼樣子?讀者喜不喜歡?想不想帶迴傢?」這些構想若能得到適度的奧援,譬如具體的建議或足夠的經費,或許有可能化為一部傳世的經典。力推「構想預售」服務的Babel市集,是由曾任網路書店總編輯的邱俊龍所創辦的交易平颱。邱俊龍認為,通路應該讓生産者與消費者發生更親密的互動與溝通,進而創造下一個世代的文化論述、交易關係與全新的産業價值鏈。Babel市集將於6月份與茉莉二手書店閤作,推齣「我有一份目錄」齣版論壇。邀請黃秀如、韓嵩齡、瀋雲驄.......
動畫世界-夢見首部MIT自製動漫年底上映

對很多人來說,夢境與現實就像平行綫,隻能在現實尋夢、在夢中實現。國內原創動畫《夢見》,將真實世界與夢世界並存,以2D與3D畫風融為一氣,做為劇情虛實轉換手法,是作者翁文信耗時多年,獻給青少年動漫族群的電影長片,預計年底發行。2D+3D 禮獻動漫迷文瀾資訊總經理翁文信說,《夢見》的劇情有愛情、懸疑和夢想的鋪陳,有深層的教育意義。女主角Mida是以輪椅代步的夢療師,她可以進入彆人的夢境,為人們解決心靈問題,也可以改變夢境,看見所有人的夢,隻要她在夢中唱歌,就可以將眾人的夢境相連在一起。另一名女主角蘇.......
包吃包住包玩-搭河輪遊歐 交通、住宿免煩惱

5月之後,歐洲就進入觀光的旺季,節慶讓許多地方甚至一房難求,搭河輪旅行一併解決交通和住宿的煩惱。以阿姆斯特丹為例,這次採訪搭乘的Avalon Artistry II停靠的地點就在中央車站旁,下船穿過車站走10分鍾就到瞭最熱鬧的水壩廣場,停泊位置讓旅人很方便優遊城市。水壩廣場周邊四星級以上的飯店通常一晚價格都要破颱幣8000元,透過河輪包吃包住包玩相當劃算。看好河輪旅遊市場,河輪的設施與房間已成為船公司的競技場,今年全新下水的Artistry II標榜全景式河輪,二、三樓的房間全是落地窗,讓旅人躺.......
台中新甜點-歐貝納名師加持 甜點世界級

從法國lenotre糕點學校畢業的郭雅琳與蔡孟書,在太原路綠園道旁開瞭間歐洲鄉村風格的法式甜點店,店內甜點種類不算多,造型也中規中矩,倒是門口放置的法蘭剋米歇爾大師看闆頗引人注目。法蘭剋米歇爾是2004年法國最佳工藝職人M.O.F得主、2006年世界糕點大賽冠軍,他是兩人在lenotre學校的指導教授,並在歐貝納開幕時親自來颱灣駐店指導。大師齣手有沒有不一樣?「其實我們調整瞭老師的配方,因為颱灣人的口味和法國人不同!」郭雅琳以招牌甜點「三個百分點」為例,這是法蘭剋米歇爾奪得M.O.F的冠軍作品,.......
台中新甜點-玫瑰烘焙坊 花果香沾染一夏

「如果會做甜點,就容易追到女朋友!」衝著這句話,玫瑰烘焙坊點心副主廚蔡凱因15歲開始學烘焙,曾拿下多項甜點比賽奬牌,他把夏日最受歡迎的芒果、檸檬、鳳梨等水果,結閤浪漫的茉莉、玫瑰、薰衣草等花香,混搭齣夢幻又清新的夏日甜品。「研發甜點像做實驗,有時不同食材會碰撞齣火花,為味蕾帶來驚喜,這是烘焙很好玩的地方!」蔡凱因以茉莉鮮芒果塔為例,拿口感清爽的檸檬製做奶餡,再加入西班牙進口天然茉莉花精提增香氣,上層綴以新鮮芒果丁與檸檬馬卡龍,既嘗得到芒果的甜甘與檸檬的清香,尾韻還散發淡淡茉莉花香。另一道玫瑰覆盆.......
台中新菜單-文華道 香草料理春天味

位於逢甲商圈的「文華道會館」在春季推齣瞭以新鮮香草為主題的歐陸午餐,從果汁、沙拉、麵包、濃湯到主菜、甜點,一客隻賣250元,而且餐後咖啡還可無限續杯,經濟又實惠!「沒辦法,我們要和逢甲夜市競爭,一定要好吃又便宜!」主廚Kevin錶示,這一季新菜單以新鮮香草取代人工甘味,除瞭符閤時下自然健康的概念,清爽不油膩的口感也適閤春季品嘗。例如主菜嫩煎牛排襯迷迭香蘑菇佐鬍椒紅酒醬汁,以香煎的澳洲牛菲力,搭配新鮮迷迭香拌炒的蘑菇,以及用紅、綠、白三色鬍椒熬煮的紅酒醬汁,無論口感、配菜或盤飾都有五星級主菜的水準.......
台中新餐廳-GB鮮釀 美墨料理新風潮

颱中新光三越百貨13樓影城最近接連開兩傢餐廳,一傢賣鮮釀啤酒加美墨料理,一傢賣日式燒肉配紅酒,都是適閤吃消夜或小酌一番的餐廳。率先開幕的GB鮮釀主打新美式飲食文化,挑高九米的寬敞空間採用專業高音質喇叭與舞颱專用電腦圖型燈,加上LED多彩染色燈的流動變化,白天有美式酒吧的熱鬧感,夜晚則呈現LUNGE BAR的光影氛圍。■鮮蝦塔可 軟Q酥脆這一季料理同樣訴求新美式風格,亦即在傳統美墨料理中加入新元素,例如墨西哥鮮蝦塔可,以傳統墨西哥餅皮搭配高溫油炸的紫玉米餅皮,呈現外軟Q、內酥脆的雙餅皮口感,主食搭.......
台中新餐廳-寬心園 美味拚蔬贏

11年前,「寬心園」是颱中一傢小小蔬食店,門麵小、座位少、停車位很難找,偏偏生意好得不得瞭!如今,寬心園發展成颱灣最大蔬食連鎖店,一年營業額上看3、4億元,董事長黃瓊瑩再次返迴颱中開店,要在廝殺最激烈的公益路商圈打齣一片天。寬心園好在哪裏?我想「滿足感」應是最大理由,從第一杯上桌的精力湯、五顔六色的和風沙拉、天天更新的廣式原盅燉湯、23款中西日不同風味的主菜,一直到最後的時令水果盤、港式養生甜品,在寬心園品嘗蔬食套餐,不但有飽足感,還有一種心滿意足的愉悅感。■每一道菜餚 下足功夫「曾有客人計算,.......
台中新餐廳-魚沒有煮 握壽司照樣好吃

「一位越南朋友說,颱灣食物樣樣好吃,連魚沒有煮都很好吃!」就衝著這句話,清美日本料理店老闆陳明仁再次結閤日本建築大師高鬆伸的空間美學,在一中商圈開瞭「魚沒有煮」握壽司專賣店。■食材價差大 各具風味有彆於清美店的和風禪意,魚沒有煮以亮眼的紅黑色係搭配大量鏡麵材質,呈現年輕活潑的時尚感,價位走親民路綫,從一貫6、70元的生魚片握壽司、240元的和風生牛肉到380元的烤青甘下巴、580元的精緻散壽司,無論吃少、吃巧或吃飽,各取所需。不過,外行人湊熱鬧、內行人看門道,魚沒有煮卻會很好吃,祕訣到底在哪裏?.......
台北新菜單-新味PK禦膳 烤鴨誰先吃?

春江水暖鴨先知,颱北兩傢飯店同時推齣烤鴨料理,設計迭齣新意的晶華多鴨6吃3200元,價格比1鴨2吃2600元更劃算;走傳統路綫的威斯汀六福皇宮則是4人7200元,將端上一隻烤鴨、一隻燉水鴨,還有一尾蒸黑毛等料理,份量超多,各有各的賣點。晶華酒店 一口酥味創新 鴨腳包吃懷舊每一傢飯店都想執烤鴨之牛耳,各有講究各有堅持,晶華酒店特選肥美櫻桃鴨,以廣式烤鴨為基礎,變化齣雙捲雙饗、麻辣柴把翅、香辣跳跳鴨、懷舊鴨腳包、古法老火鴨湯米粉、一口酥等6種吃法。最特彆的是創新一口酥與懷舊鴨腳包,一口酥是鴨皮、起司.......
台北新餐廳-BELLINI CAFFE 敦南店料理噴香

16年前BELLINI CAFFE在復興北路齣現,迅速造成風潮,烈火熊熊的柴燒窯烤爐,現現烤齣一片片羅馬式披薩,再加上對半開剖上桌的蘿蔓凱薩沙拉、濃稠鹹香的明太子義大利麵,成為和風義式料理的經典代錶。受到怡亨酒店董事長黃建華與盧弘忠雙雙力邀,「BELLINI CAFFE敦南店」進駐B1和B2,並於下周一正式開幕,蓄勢待發的行政主廚伊藤雄次郎錶示,新店價格與老店相同,但比老店多齣三成的新菜。■裝潢奢華 展示藝術品裝潢風格走紐約奢華風,B1的半開放式廚房秀齣從義大利進口、價格上百萬元柴燒窯烤爐,座位.......
台北新餐廳-杏桃鬆餅屋 彈力甜蜜大爆發

杏子豬排的老闆陳東泰以烘焙起傢,對甜點無法忘情,除瞭自創夢卡朵品牌,日前還找上東京彈力鬆餅的元祖「杏桃鬆餅屋uzna omom」,耗資近韆萬元,在颱北東區成立第一傢海外分店。■裏原宿貓街 當地第一傢鬆餅的種類很多,颱灣流行質地酥脆的格子鬆餅,但東京原宿最夯卻是口感軟蓬的彈力鬆餅,而掀起這波風潮的,正是杏桃鬆餅屋的女老闆,年方30的門崎杏子。「我愛吃鬆餅,經常在傢裏研發配方與口味,9年前受到父母資助,在裏原宿貓街開瞭鬆餅屋,不但是當地第一傢,還是彈力鬆餅的元祖,也開創全新的鹹甜混搭風。」門崎杏子透.......
台東都蘭藝術傢群聚

颱東都蘭藝術傢群聚,他們在這兒激發的創意能量,讓都蘭糖廠的錶演、工藝品、手作文創商品多元精彩,也因此吸引更多旅人落腳於此。除瞭糖廠,都蘭的餐廳、民宿裏也都藏有生活藝術傢,讓人一飽口福、住得舒服!糖廠新空間二倉賞工藝糖廠是遊客造訪都蘭必遊景點,今年新開瞭二倉,由兩對夫妻、四位居住在颱東的藝術傢豆豆、達鳳、Heidi、Lafin,將日據時代的糖廠倉庫整理成藝術空間,展售大型漂流木傢具,或手作小飾品、陶藝、服飾等,展現東海岸新一代藝術傢的特色。Heidi是加拿大華僑,Lafin是颱東阿美族,Heidi.......
台灣趴趴走-想到猴硐當隻貓!

「猴硐的貓好幸福哦!好多遊客搶著餵,吃飽瞭就睡,躺在路中間曬太陽,人還得讓路,我也好想來猴硐當貓啊!」遊客贊嘆聲不絕。若貓咪世界票選最幸福的城市,那新北市猴硐就是幸福指數NO.1的小鎮瞭。現在的猴硐看不到猴子,反而隨處可見一隻隻豐腴慵懶、完全不怕人的野貓。猴硐過去以礦業為主,停止採煤後,曾經風光的小鎮頓時沉寂,直到2009年因貓爆紅,貓咪攝影師「貓夫人」拍瞭許多猴硐貓咪的照片,讓人發現小小山城竟藏瞭這麼多貓咪,吸引愛貓和喜歡攝影的人前往,帶動貓村的名氣。貓橋放食物貓公車上路貓村,一般指的是位在侯.......
台灣趴趴走-扶他一把 輪椅族好遊

「隻以健康人為中心的社會,不是健康的社會。」身為颱灣第一傢民營的無障礙接送,多扶不隻為輪椅族提供溫馨接送情,還載著去泡湯、賞花、逛老街。對多數人來說,泡湯不過就是把衣服脫光走進風呂,接著就能瞇起眼享受溫泉暖意,是一件再簡單不過的事情;但對手腳不方便的輪椅族來說,泡湯是奢求。除瞭處處階梯溼滑外,一旦入水,無力支撐的雙手與雙腿,一不小心就可能帶來傷害。多數人都無法想像泡湯這麼簡單的一件事,對身障與銀發族等輪椅族來說竟是如此睏難,更無法想像他們有多渴望泡湯。為瞭幫他們圓夢,「多扶接送」在去年底首度開辦.......
台灣趴趴走-桐來八卦山灑花!

每年4月中旬,當北颱灣桐花還在含苞整裝時,彰化因為天暖高溫,早已花海成雪,待4月下旬桃竹苗客傢莊進入賞花熱潮,彰化桐花已即將褪去鉛華,迎嚮生命下一個階段,此時滿山寜靜與枝頭少許殘妝和初生油桐果,另是一種新生命繁衍之美。桐花區分雄雌,一般常見掛滿枝頭且整朵掉落的是雄桐花,花數較少並有六條柱頭的是雌桐花。每年花落後,雌花會陸續結果,早年油紙傘上的桐油就是以油桐果榨齣,油桐果模樣可愛,可撿拾帶迴傢培育幼苗或當擺飾,但油桐全株有毒,尤其是種子毒性最強,小心不可誤食。彰化桐花樹林在它的原始與不經修飾。由於.......
台灣趴趴走-藝界人生 都蘭開演

颱東都蘭藝術傢群聚,來這兒欣賞好工藝,品嘗好手藝!颱東都蘭藝術傢群聚,他們在這兒激發的創意能量,讓都蘭糖廠的錶演、工藝品、手作文創商品多元精彩,也因此吸引更多旅人落腳於此。除瞭糖廠,都蘭的餐廳、民宿裏也都藏有生活藝術傢,讓人一飽口福、住得舒服!糖廠新空間 二倉賞工藝糖廠是遊客造訪都蘭必遊景點,今年新開瞭二倉,由兩對夫妻、四位居住在颱東的藝術傢豆豆、達鳳、Heidi、Lafin,將日據時代的糖廠倉庫整理成藝術空間,展售大型漂流木傢具,或手作小飾品、陶藝、服飾等,展現東海岸新一代藝術傢的特色。Hei.......
台灣趴趴走-這樣玩柳營,最牛

水牛黃牛乳牛,柳營全都有。看老牛、餵小牛、喝牛奶,玩什麼都脫離不瞭牛。原以為來到柳營「老牛的傢」會充滿濃濃哀愁,或是見識生老病死,但最後我卻笑著離開,或許是看到老牛悠哉吃草、水坑打滾,一副享受退休生活的老好命模樣,讓人忘記牠們先前的辛勞或死裏逃生的遭遇。老牛的傢,是為老牛設置的安養中心,颱南市政府農業局畜産科科長周誌勛說,「老牛操勞一輩子,不但沒有老人津貼,有的還要被宰殺,太可憐瞭,何況颱南以農業為主,更要好好敬重這些老牛。」老牛的傢目前收容5頭水牛、3頭黃牛,除瞭退役的耕牛,也有從屠宰場搶救的.......
台灣趴趴走-鹿港 風雅文宴呷富貴

富過三代,方知飲食,在悠揚琴音與茶韻飄香中,輕嘗鳳眼糕與牛舌餅,鹿港富貴滋味正風行。彰化縣政府繼去年推齣「鹿港小吃宴」後,今年再度加碼推齣「鹿港風雅文宴」,改以鹿港知名的牛舌餅、鳳眼糕等點心搭配南投鹿榖凍頂烏龍茶,即日起接受預定,讓遊客可一嘗早年鹿港大戶人傢的富貴滋味。從清乾隆50年開港以來,鹿港曾風光一甲子,行郊林立、經濟繁榮,許多富商也紛紛從泉州聘請俗稱「刀子師傅」的專任廚師,或為酬賓、或為富商日常飲食服務。隨著鹿港沒落,這些刀子師傅也從豪門流落到市井,並就此帶起鹿港延續至今的庶民美食與糕點.......
吃喝玩樂-貓咪鳳梨酥必啖 單車過隧道懷舊

猴硐最近流行貓咪造型鳳梨酥,除瞭車站附近的艾妮、煤之鄉等商店有賣之外,黑金客棧也有黃金貓、黑金貓兩種口味,礦工女兒蔡淑惠手工烘焙,黃金貓是鳳梨鼕瓜餡,吃得到鳳梨果粒,黑金貓外皮則是北海道墨魚粉,內含烏梅餡,象徵礦工生活酸中帶甜。店裏還有礦工茶,蔡淑惠把過去爸爸進煤坑每天都會帶的仙草茶製成茶包,方便烹煮。來到猴硐除瞭看貓,也可以在火車站前租單車,沿著自行車道往瑞芳方嚮騎,依山傍水、風景秀麗、空氣好,而且火車不時從身旁經過,騎進「三個磅空」、舊火車隧道,氛圍非常好。在猴硐還能看壺穴,走逛礦坑文化,看.......
吉時去行樂-旗山香蕉 喔伊細!

香蕉有種子嗎?有多少品種?香蕉花有香蕉味嗎?一株香蕉樹能長齣多少根香蕉?樹上黃的好吃還是催熟的好吃?來旗山找張班長,纔知看似平常的香蕉,其實大傢都不太認識它。傻傻種植 張宏士變達人「我原本隻是傻傻種香蕉,沒想到日本人很愛看,還付錢請我割香蕉給他們看,光去年就來瞭158團,每團給我2韆元,收入比賣香蕉還要好。」帶著點成功拚到外交還賺到錢的僥倖笑容,高雄旗山果樹産銷班第36班班長張宏士說:「颱灣人要來看更歡迎,不收錢我也願意解說,還請吃香蕉,畢竟香蕉曾是颱灣最輝煌的産業之一,希望大傢多多認識它。」喜.......
吉時去行樂-歡螢光臨阿裏山

春天到,阿裏山國傢風景區展開夜間派對,地上火金姑與天上星空互搶戲,一閃一閃好吸睛,看熱鬧的觀眾搞不清,今天錶演主題究竟是星光?還是螢光派對?颱灣螢火蟲種類共計62種,在阿裏山就發現23種,約占瞭1/3,從低海拔到中高海拔的螢火蟲都可見到,而且全年皆有不同品種輪番發光。尤其是3月下旬至5月中的大發生期,是黑翅螢最多最亮的時刻,加上大端黑螢參與,是賞螢最佳季節。欣加坡生態村螢光串連星光遊客上阿裏山賞螢,多半會到嘉義瑞裏,尤其是最早投入螢火蟲復育的欣加坡生態村(原若蘭山莊木屋區),以火金姑數量穩定而聞.......
吉時去行樂-父子仨 吹齣竹南第二春

口吹玻璃、馬戲團錶演,這些看起來很異國的玩藝兒,最近都聚集在苗栗竹南小鎮,讓人看得目不轉睛。我曾搭13個小時的飛機到捷剋,然後轉兩個小時的公車到溫泉小鎮卡羅維瓦利看人口吹玻璃;我也曾花瞭十萬多元的旅費飛到義大利威尼斯,再搭船到Murano小島看藝匠口吹玻璃。沒想到,現在從颱北搭自強號到竹南隻要220元,就可以一窺高難度的口吹玻璃技藝。扛鐵管吹玻璃 驚動海內外竹南有天然氣與矽砂,自然成為颱灣玻璃發展的重鎮,經曆過接受大量外銷訂單的輝煌年代到90年代的産業外移,有60年曆史的國泰玻璃,看盡颱灣玻璃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