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凡 | 是 | 攝 | 影|《我的道場》螞蟻隔壁班--顔長江在綫分享會聲音版特彆鳴謝:語音整理:玫瑰之上文字整理:許慧現在我們開始吧!今天不太好意思 這幾天特彆忙 《我的道場》-顔長江分享會實錄(14500字) - 趣味新聞網

發表日期 4/6/2022, 6:16:49 AM
| 凡 | 是 | 攝 | 影 |
《我的道場》
螞蟻隔壁班--顔長江在綫分享會聲音版
特彆鳴謝:
語音整理:玫瑰之上
文字整理:許慧

現在我們開始吧!今天不太好意思,這幾天特彆忙,因為不停地有展覽開幕,並且恰好我今天換瞭一個班,今天晚上我是在上班的間歇跟大傢說說話,其實也就說說話,你說要有充足的準備或者係統性的準備,我確實還做不到。令鬍歌非常熱情,大傢也很熱情,我們就見見麵或者說聊聊天,講一講我自己在攝影上麵的一些作品以及背後的故事。(這些故事)以前也沒怎麼太多披露,請大傢多指教!
我是湖北長大的,我們房前的空地都叫做道場。到這兒來拍,我的第一捲就誕生瞭好幾張很好的東西。大傢看我剛剛發的這張圖,我說這是神的召集令,這個確實也不假,這確實是一個神的場閤,他跟我拍攝的作品《紙人》息息相關。我想這個作品我不係統性地介紹,大傢估計也有所瞭解,《紙人》肯定是我非常重要的一部作品。
我的《紙人》這部作品的起源,大概可以追溯到1997年。(那時)我到高州的鄉下到處亂轉,就是我作為一個記者,要給報紙去拍點圖片,就坐在車上亂看,看到什麼喜歡的就行,就拍下來。經過高州市長坡鎮的時候,當地的新聞通訊員說這裏有個冼太夫人廟,她是粵西非常齣名的一個古代的女神。我進到她的廟去參觀瞭一下,突然就發現瞭一個房間裏放著大量的紙人。我非常高興,讓製作紙人的師傅(當地的農民)給我把紙人拿到道場上。我們說的道場就是房前的空地,在廟裏邊就更是這樣,廟前麵有一個很大的空地,(我就在空地上拍攝瞭很多紙人),比如說做海報的這一張,後來我命名為《騎馬趕考的書生》。從此我開始瞭大概11年左右拍攝紙人的曆史,我經常去那裏拍攝。
大傢能看到我拿齣來展齣的作品,但是背後的事情知道的人可能不多。我當初的照片,其實很多時候就是用一個傻瓜機在拍,就記錄一下,所以說大傢能看到我在拍攝創作《紙人》的背後是怎麼迴事。
這個紙人,他們是拿來祭祀給去世的人的,尤其是在當地的這個廟,尤其是冼太夫人廟,進行比較大規模祭奠的時候,祭祀的時候,就會拿它(紙人)來做做文章。有一天這個作者,就是做紙人的農民還打電話給我,他說:“顔老師今年是50年一遇的大儀式,叫做打醮。我在四鄉祈福,其實主要是把四鄉的鬼魂、冤死的鬼魂收集起來,把他們送走。”在這個鄉土的精神體係裏邊,這幾乎是最重要的一個儀式,不過在很多地方已經沒有瞭,廣東人還存在,香港也有比較有名的打醮儀式。這個儀式我可以給大傢傳一些照片。
作為一個攝影師,我們很多精神來源不是空穴來風。我自從1997年在冼太夫人廟偶遇瞭紙人之後,我就迷上瞭。(那個時候,我剛剛學攝影,相機、膠捲什麼的,用得亂七八糟的,用瞭好幾種相機。所以現在大傢看我這作品的這個質素和它們錶麵的顆粒,感覺是不一樣的。有萊卡,有什麼潘太剋斯 ,還有哈蘇,什麼都有。 那時我剛學攝影,基本上是自學。)我就覺得他們(紙人)跟我有什麼聯係,我要通過他們發展一個巨大的故事,這故事甚至還有情節,事實上也有幾萬字的文字,就藉紙人描述瞭一個精神世界。
那麼這次在這個廟裏的打醮儀式,我在那裏待瞭三天。有一個香港的年輕的研究生,他是去做民俗研究的,他都待不住,每天晚上都要迴到縣城在好的賓館休息。而我就在那兒和他們一起熬夜,或者到農民的床上麵躺一躺,三天我都沒離開,隻是我沒拍一張所謂的作品,但是我在感受。我為什麼要感受這個呢?這個鄉村的精神世界,事實上是我們中華文明或者是我自己作為一個中國人,我的精神故鄉的一個非常集中的具體的體現,就是我們人跟天跟神跟土地的關係,尤其是生和死的關係。大傢可以仔細看看這個圖。




這一連三天就是各種儀式,首先是到處收集這個鬼魂;然後是鬼魂安頓,給他們吃飯、吃東西,吃飽喝足。我就是在那享受,我也拍不瞭什麼東西,這麼暗的環境,一般是晚上更熱鬧麼,照片也沒法曝光是吧?
由於這個儀式非常大,他甚至超越宗教,為什麼呢?我們一般說這是個道教儀式,事實上裏麵還有佛教的隊伍,就是道士、居士或者和尚都有。最奇特的是我們第一張圖片顯示的,這個隊伍他們穿著青色的長衫,他們居然告訴我,我們是儒教的。這個儒教也特彆有意思,我非常震動。因為我們說有儒傢,而儒教一般就覺得他沒有一個像彆的宗教那種很強的宗教感,很強的儀式感,但是事實上他們是有的,除瞭祭祀孔子以外,他還有這樣的神職人員。這個我隻在高州發現,發現過這樣一幫人,他們也挺有意思的。他們拿著書本在荒野裏去尋找鬼魂,我就跟著他們走,他們念著經,他們的經裏麵有些繁體字他們不認識,我還要給他們指點。那些詞都很有意思,比如說荒野裏我發現瞭一個骷骷髏頭,你是什麼來曆?我問你,你也不迴答,你有什麼冤情,你就跟我說,你受不瞭,也不要緊,我帶你走,我把你安頓下來……就這樣收集。
大概這幾天裏麵,相當長的時間其實就是在不停地敲鑼打鼓、奏樂,各個隊伍(儒教的、佛教的、道教的)往四周去搜尋,每個隊伍帶著一個樂手。我的那個做紙人的大師傅,他就是一個吹嗩呐的,他也能做紙人,他就是一個隊伍裏麵的樂手。然後今天穿過這片樹林,明天穿過那片樹林,也挺有意思的。我感覺我們的土地絕不尋常,我們的文化也不尋常,我們的人要安頓自己的內心,尋找在土地上的意義,或者說我們的故鄉之所以成為故鄉,我們的傢門口之所以成為道場,他是要有這樣的神的因素。
大傢可以看到上麵一張有火的作品,也不能算是一個作品,因為是隨意拍的。後邊有兩個神像,這個神像都是臨時做的紙的形式,就是我常年閤作的那位做紙紮的師傅,他同時也是吹嗩呐的樂手,就是他做的,他的農村團隊依我看在全國範圍內,他們做的都是最好的,他紮的是個神,雖然很巨大,但紮得還是比較粗糙,為什麼呢?因為反正是過兩天就要把它燒掉的,然後大傢在下一張也可以發現,這個叫幽所,這個題目非常的驚人,因為幽是一個不太好的詞,這個跟地獄是相關的,幽所其實就是一個墳墓的文雅的稱呼。他們這些紙人也就是我平時拍攝的那種,但是我平時拍攝的比這要好,因為這個就是規模大、做得多。我這個師傅就做的很隨便,紙人做好瞭,他們就代錶著從四方收集來的這些鬼魂,把他們安置在這裏。這像是動畫片一樣把人代入,紙人這種拙樸的平麵化的形象,還有這些煙,這些霧,這些燭光,在那些年頭都是促使我去幻想的重要的現實因素。

大傢可以看看下一張,最後一張,如果你們把它放大,那麼我們就可以感覺到我們可能會在這裏做齣一些脫離現實的幻想型的所謂作品齣來。我現在用手機給大傢裁剪一下,你看現在是不是充滿瞭一種幻想的氣氛,這就是可能走嚮作品這麼一種可能。我們不是為瞭做作品而做,是為瞭我們的精神世界。所以我講這些並不是說要講這種技巧,而是我熱愛這種精神生活的場麵。哪怕有的人覺得這不吉利,跟死亡關係太大瞭,我也覺得在生死之間,這個靈魂在這遨遊,這是一個非常享受的事情。其實怎麼說呢?活在精神世界確實是這樣的。你說顔老師你受到這些的影響,你究竟創作齣來什麼呢?大傢可能瞭解,如果不瞭解的,我現在傳一些圖給大傢。大傢可以看到我這些圖就利用瞭我們剛纔那些紙做的人。當然因為師傅跟我有充分的時間閤作,但是他也不是有意一定要做得很精緻,隻是他看我來瞭多少會做得更好一點。那麼我拍成黑白作品的東西,是比上麵那個打醮現場的東西要好很多的。大傢可以看齣,通過我在冼太夫人廟見到的這些紙人,他們觸發瞭我的創作。

這個創作成為一個很大的精神世界,就是中國文人尤其是士大夫的美學傳統,我們天人閤一的哲學,在這塊土地上生生不息,它是我們的根本。我創作的這個大世界裏麵發生瞭很多事情,它構成瞭一個很大的故事。比如說愛情,說實話這個還不是我的主業,當時我還拍這兩個紙人,我想把他們拍到一起,結果旁邊一大群小孩兒跟我一起玩,可以說是當我的助手。他們中有個小孩兒就把這女孩子的兩個胳膊抱住這個男的紙人,真是太棒瞭。當然我還有一把傘,這把傘很重要,它曾經在我的另外一個畫麵也齣現過,它是漂浮在空中的。當然我有我的安裝技巧,這不是電腦做的,是現場的技巧。所以說這個叫做愛情。那把傘它永遠停留在這裏,象徵著愛情的永恒。當然我們現實中的愛情往往沒這麼持久,這隻能說是一種美好的嚮往。

但是這個美好的世界後來受到一些壞人(或者說這是我們這個世界侵犯文明的勢力)的乾擾,所以說我花瞭很大勁跟農民們閤作,拍瞭這麼一張照片,《在江邊畫捲裏發生的屠殺》,這個很不好拍,當時不像現在這麼先進,我又不會製造煙霧,我隻會用草製造這個,也不懂得技術上一定要講究,比如說我在40度的高溫,萊卡是一個鋼鐵機器,它已經被烤得不行,結果這張膠片都烤化瞭,所以齣現很多窟窿。這個窟窿我在這個照片上做瞭下修補。然後我的農民兄弟們就給我當臨時演員,我這是一個紙人和活人共處的世界,在這個煙霧的前方,有一批活人走瞭,那批活人事實上就是殺手,紙代錶文明,而那些活人是肉做的,肉代錶欲望。我自己也是這樣,都有兩麵性。這裏麵齣現瞭人類,但人類在我的這作品裏都比較小,或者比較在暗處。因為你要把活人和紙人統一在一個畫麵裏,由於形體的巨大差彆,感覺的巨大差彆,我們不能做得太明白,太直白。

那麼在這個過程中,女孩子是什麼樣的一個角色呢?這也是我探索過的,我們看上麵的幽所,我剛纔裁的那個彩色圖,她們是一群小女孩,挺可憐的感覺。在我拍攝過程中,有一次他們做得不太好,我也沒太大感覺,但是有這麼一些小女孩,她們的的形象不算好,我就(把她們)燒掉,燒掉是一個儀式,燒到隻剩下兩張臉。他們的骨架像四個十字架,我擺在山上,遠處一朵白雲。事實上我挺喜歡這張照片的,它的曝光和衝洗不算好,但是我非常喜歡這張照片,它好像在問這個世界。

紙人不是說隻是拍瞭一些奇異的照片,他們有個我剛纔說的脈絡,就是文明人,我是用紙人來代錶文明和文化世界的毀滅。那麼還能挽救嗎?還能救贖嗎?所以說我後來又拍瞭一張,這個是結尾之作,它原來的題目叫做《他終於遇到瞭自己的神》。也就是說,我們事實上是靠一個神來挽救自己的,來搭救自己。我們要鑄造我們自己的神,在這塊土地之上。也就是說我們要有自己的道場,自己的道。我就選瞭這麼一個空間,它是一個洞式的,中間挺亮的,四周挺暗的,然後放上煙霧,這時候一個神像從空中飄來,事實上這個神像也是我的師傅們做的。因為他們作為農村的這麼一個精神事業的從業者,他們會多方麵的手藝,其中一個人會畫神像,我費瞭很大的勁,隻有這一張是相對好一點。後來我改瞭名為《我等你很久瞭》,這是有兩個意思,一個是這個神,我等你很久瞭,你在人世間這麼遭遇不幸,現在我等你醒悟來找我。另外一個是指人,也就是這個具體的騎著馬的這麼一個人,他的心願是我等你很久瞭,我一直在等我的神到這裏,現在您終於來瞭。事實上這個神,我們從某種程度上說,我們在生活中也可以說他就是我們自己的投射吧。我們自己總要想方設法安慰我們的一生,給我們自己找到意義。這張稍微亮一點的好一點,我傳這張吧。

事實上這個故事就差不多結束瞭,我覺得我拍的這些東西就是農村最沒人看的東西,這些場景是最普通的農村的場景,但是隻要我們自己喜歡,我們可以在這些場景裏麵尋找到自己的道場。你與之對話,你享受其中。其實我所有的作品都是這樣,要他有光就有瞭光,要他有霧,要他有雲,那都得有。我們攝影師,看這個平凡的世界是絕對不平凡的。當有一點觸動我們的時候,那就像一見鍾情一樣,你就把它拍下來。我整個給大傢的意思就是說作品不是硬做的,比如說這些年並沒有眼前的景物或者人能觸動我的,我就不怎麼做,我去乾彆的,這都是可以的。
下麵我要轉移一下話題,在短的時間裏盡量給大傢講一些彆的,我就講一下我在三峽的幾個場景,大傢應該也非常熟悉我的三峽作品。我主要以紀實為主,分三部分:第一部分是紀實,第二部分是行為藝術,第三部分也是(行為藝術),隻不過是用攝影的方式來記錄,它是發展,根據三峽的進程的發展。

因為我的三峽的東西也比較多,我就舉一個例子來說明我這個三峽的三部分的發展。我們不過是在江邊尋找的人,尋找到觸發自己的靈魂的東西。在那一瞬間,你就不得不按下快門,本能的。有這麼一個地方,他就是這樣讓我們陶醉其中。這個就是下岩寺,這是王維和蘇東坡都做過不少詩的地方。這個是一個岩窟寺,這個瀑布就流到下邊就是長江,瀑布下麵有一個石窟,岩洞,裏麵有上萬尊佛像,有的佛像隻有指頭大小,大的有兩層樓高。有四尊大的不是唐朝的佛像,是在文革期間被一位姓楊的隊長帶著紅衛兵被他砸瞭。我去到這裏的時候已經是2003年,這個楊隊長已經成瞭這裏的居士,他在贖他的罪,他恢復瞭這座寺廟,但是沒想到恢復瞭之後,馬上要被三峽水庫所淹沒。一般人知道三峽的拍攝是以紀實為主的,這也是紀實的幾十張作品裏麵的一張,你看編號是05還是比較靠前的。

我到第二部分,大傢可能知道,是做黑匣子的行為。就在三峽淹沒的過程中,我埋個黑匣子,因為這個地方淹沒的比較晚,所以說我在這裏,黑匣子做得晚一點也隨便一點。這也成為我第二部三峽作品中間的一個環節。這一步一般也叫做“與天地同壽,與日月齊光”。這個題目反正我都做得很長,這個亭子就是下一次的亭子,這個亭子保護的是一尊唐朝的佛像。我在這裏做瞭我的黑匣子的這個行為。大傢可以看我的手裏拿著一個黑色的盒子,我用另一張圖片,可能不是看得清一點,這盒子都有編號。然後這個時候紙錢在天空上飛舞,這個是第二階段。我的黑匣子裏麵在下岩寺也做瞭一個,因為長江的水這個時候正在往上漲。這個亭子和佛像、這個寺廟都要淹沒進去瞭。三峽黑匣子的行為主要作於2003年,這篇解釋文章也是2003年寫的。當時拍得比較好一點兒,我就不放圖片瞭。

到下岩寺,這是2006年,這次的差一點,因為我人也老瞭幾歲,沒那麼靚仔,這個衣服也穿得隨便一點。但是做行為有時候不想那麼多,也想不瞭那麼多,錶達一下,他也很熱愛這個地方。我們可以看齣我們分彆是各自怎麼樣不同的發展。那麼到有戲台,大傢可以想象我們傳統的文化生活在市場上唱戲。但是最搞怪的是什麼呢?最搞怪的是我們每次做作品,在自己這個地方,我說道場,就是要錶達自己對世界的看法,要錶達清楚。如果一個方法不行,我就用另一個方嚮、方法。當紀實覺得不行的時候,我就用瞭黑盒子,但黑盒子還不能錶達我對下岩寺等地方的失去的遺憾的時候,我最後又發展齣新的方法,這就是三峽的第三部。

這第三部隻有三幅作品,這個就是剛纔這個文字說明裏麵的第一號,時間非常具體。2006年9月25日6時,顔長江在下岩寺前麵的佛亭上麵上吊瞭,就這麼簡單。所以很多朋友叫做“你那個上吊”是吧?後來在廣東美術館展齣,在第二屆國際攝影雙年展。這幅作品當時擺在中庭,從樓上掛下來,策展人想到這點特彆好。但是我自己很遺憾,應該把它放得很大,當時纔一米大就覺得很大瞭。實際上應該放到兩三米,從中間吊下來,我們就把這個效果做足,是不是?
其實那一次有點遺憾,就在這裏這個吊的過程我就不說瞭。當時水已經漲上瞭亭子,已經腳都在水裏邊兒,我是遊泳過去的,我也做瞭很多工作。我的閤作者肖萱安在岸上,在洞裏邊還沒淹沒的地方給我拍照片兒。他對哈蘇相機學得不認真,結果把我吊瞭個半死,這張片應該是還沒有修好的,有點不對,不應該用這張,我看看還有沒有備用的,還有沒有好的,這是一張原始片。
我的老朋友肖萱安先生常年跟我一起在鄉下行走,在三峽閤作尤其比較多。他做他的,我做我的,互相幫忙,因為他也有一些行為藝術是需要我來按快門的。我離開下岩寺的時候,我說我要迴廣州上班瞭,這個淹沒過程你來拍,最後他拍得挺好的,租瞭個船每天在拍,後來當年獲得瞭西雙版納攝影節的大奬。


對,剛纔是純掃描,效果很差,這張是好一點點,其實拍得都不能說曝光效果很好,當時條件就這樣瞭。這個怎麼說呢?沒什麼好誇耀的,這就是一個錶達,而且我自己也並沒有真正的死掉,你說真正的殉道那是瞭不起的,咱們還做不到。當然我自己也可以認為我是當時的顔長江的再轉世是吧?
剛纔有工作,我再說說王爺廟吧。王爺廟也至少齣現在我第一部分和第三部分,就同一個地點,我們就是看到一個,總之在路上會碰到一個點,這個點不停地碰到,這些點觸發攝影,就是這麼一種關係。我可以說就是你找到自己的道場,有的地方確實沒有,就不要硬來。我們說起來是感覺,說重一點兒,它是你的勝利,一見鍾情的勝利,你們彼此照耀對方是吧?
那麼有一天,我坐著船,心灰意冷,在江上行走,在離重慶主城已經不遠的長壽縣,現在是長壽區,看到長江大橋,這橋上麵有鍋耳,是廣東風格的,因為以前湖廣填四川,這個廟太漂亮瞭,我要下去,我在鄉下的一個小碼頭,因為我坐的都是最普通的客船,下去瞭,然後找瞭個摩的,在滿地的泥濘裏邊,到瞭這裏,我就感覺這是我一個巨大的寶藏。這個廟我自己一個人翻牆進去的,因為它已經關閉很久瞭。看見裏麵有戲台,實際上它是一個非常大的非常有規模的一個廟。他在古代是拿來祭祀張飛的,也就是水神。張飛後來成為水神,在四川。到瞭後來,這個廟在文化革命的時候,大傢可以想象它成瞭什麼樣的一個場所,為什麼我敢肯定它在文革成瞭一個重要的場所呢?因為這個廟的隔壁就是鄉政府,大傢打倒封資修還挺方便的。
但是最奇特的是當代,這個修大橋引來瞭萬韆建設者,這些建設者的娛樂,主要就在這個小小的村鎮上麵。我在這個廟的這一部戲台下麵發現很多小格間,裏麵寫著淫蕩的一些話語。當地的老百姓告訴我,他在修大橋的1990年代,這裏成為一些女士齣賣自己身體的地方。我覺得王爺如果有靈,我覺得他不知道會怎麼樣,可能哭笑不得。有一天有個濾州小姐,就濾州來的,大傢叫她濾州小姐,從這個廟前麵直接掉下江淹死瞭。當然也可能是無頭懸案,我沒有深究。但是我心裏想,我後來寫文章,這個廟的精神曆史就是我們對它的作用,它這個過程、這幾百年就是我們這個民族在精神世界的一個縮影。如果是寫小說的,以這個為題寫話劇,那簡直太精彩瞭。來個三幕四幕的話劇,那真是太精彩瞭。所以說,我在紀實的部分將這個廟與現代化的橋梁結閤,拍下瞭這一張也是我很喜歡的一張。

甚至在我紀實這個有限的範圍內,我還拍瞭另一張,也放進去瞭。有一天看到廟前麵來瞭一個女士,她在這裏遛狗,是一位老師的太太,牽個狗,我給她也拍瞭一張。作為紀實,我是非常滿意的。


然後又一次來到這裏,我覺得我要實施我的一個願望,就是我要在這吊上。肖老師他一開始是不同意的,我是強迫他同意,後來他也想通瞭,甚至連我一路上這些農民都想通瞭。嚴明講過這裏的人特彆有靈氣,這長江邊的人,他們都會理解我們的行為。在一個傍晚,我們來到這裏,我說我一定要做這個事兒,馬上開工,請肖先生協助我。我完成瞭這一張,這個就在戲台上麵上吊,其實這一張也挺危險的,因為我的腳沒有地方落,下邊兒是亂石頭,下麵還有一層樓瞭是吧?這個如果不小心,繩子就可以真把我勒死。那麼發現我的腳站在什麼地方呢?我發現這個上麵釘著一顆巨大的鐵釘,我就估摸著,我應該能站一會兒,我在那個鐵釘上站著,做瞭這個事情。當然這個曝光也是稍顯不足,要不這個戲台會更加清晰,總之完成瞭。

好吧,時間有限,我下麵快一點兒。這是另一幅同樣的係列。離重慶不遠的一座古橋也要被淹沒,這個橋旁邊有個橋碑,記錄瞭這個橋的誕生過程,這個橋碑非常的棒,我就在這裏來瞭一張,當時正好有一個農婦在旁邊鋤地,我一想還有外人,可能覺得我們是個瘋子,那怎麼辦?後來我就故意對她說,(我想與其與當地的人、老百姓成為互相不理解的對立麵,我不如把她拉到我的陣營),我就跟她說瞭幾句話,然後說大嫂,我這邊需要一個人幫我拉繩子,你能幫忙嗎?你幫我安裝一下。一扔鋤頭,說好哇。所以說我就拍瞭這麼一張,形象都不是很好,我們就穿著這個破衣爛衫。其實在三峽或者在長江邊上,在野外,我經常把自己弄得像乞丐一樣,甚至有時候看見人傢有什麼飯,進去就吃。我穿的衣服是我平時很隨便的,不看重的。比如這個衣服很有意思,是我1998年參加抗洪,部隊發給我的紀念,T恤上麵寫著抗洪搶險什麼紀念,這個T恤衫它是與長江有關係的,是我在中下遊湖北抗洪的紀念品,這一切都挺有意思。

有時候我們的感覺,或者是說時光就反復停留在這麼一個小地方,真的是好多天都不會有一個遊客,去關心這麼一個橋或者說一塊碑。

我也比較早就開始瞭景觀攝影。當我走到離重慶不遠的一個地方,我發現有4棟樓在江邊佇立,一模一樣,基本上一模一樣,是一個三綫工廠,這個叫做望江。這個是望江摩托廠,生産望江牌摩托,四棟樓。我看那上麵的人晾的衣服,他們的各種物品,我覺得這就是我們生活的全部。我們拍那麼多紀實,不如好好看看四棟樓。所以說我拍的是四棟樓,曾經展齣過,展齣過之後寫瞭很多文字,最後展齣作品被偷走瞭,在成都。這也是很奇怪的一個事情,我等待著它再次齣現。

很有意思的是,就是今年肖萱安老師,他因為我們常年一起行走,我見到的景他也會見到,他的發揮又跟我不一樣。大傢可以想象,同樣一個地方,我們那麼有興趣,他是怎樣發揮的。今年他推齣瞭一個作品,這個作品在市場上,在北京當代,今年賣得還挺貴的。我是比較喜歡景觀攝影,我除瞭做行為,我不在畫麵上動什麼。但是肖老師的想象能力比較強,他是一個老前衛。所以說他做齣來的東西就更加誇張一點,大傢可以看看。
我現在在我手機裏找一找,剛纔耽誤瞭下,說錯瞭地方,說到彆的地方去瞭。這個作品大傢看看放大還是看到很多細節的,這代錶著我們長江邊底層人民的生活的全部。一個紀念碑,一個巴彆塔,但是又像是地獄,我的形象也在裏邊,我很高興。所以我們說所謂的道場,你看肖老師直接做齣一塊碑來,或者說做齣瞭一個像神廟一樣的,像巴比塔一樣的富有宗教感的大建築,大傢在創作中思路都可以打開一點。我拍四棟樓這個作品是常見拼貼式的,還有,不多,我可以給大傢再看兩幅。

首先是一座古橋,這座重慶的古橋,三個橋洞,這個古橋也在重慶的建設浪潮中被拆除瞭。我做得有點不太好,因為我拍照的位置不能完全滿足我對機位的要求。但是大傢看一看,我挺喜歡的。

另外一幅是廣州的一個郊外的景象,在這個森林裏邊兒有一個非常牛的寺廟,是文廟,就跟文學有關的,叫蘿峰。蘿峰寺,又叫做蘿峰書院。這個大書院,古代的,挺好,大傢放大的話可能看得到這個書院的一些建築。前麵有一個高架橋,就從這麵的寺廟前麵粗暴的這樣過去瞭,是高速公路,我就拍瞭這麼一張照片。也許過段時間我可以拍張彩色的,我一直沒有,這幾年缺乏創作感,沒有去做,因為現在又改變瞭,這個橋底下的景象絕對變瞭,它變得非常當代,因為成瞭政府做的一個公園,很好的一個公園。那麼它的景象又會不同。所以說這個是我非常喜歡的,我叫蘿崗香雪圖鑒。就是說我們是精神的發現者,這是吹一下,結果走到哪兒都是看到美好的東西,或者說觸動自己精神世界的東西,我就非常的來勁。


你比如說上麵這張彩色,這也是一座古橋,在三峽的山溝裏邊,三峽水庫的水剛剛淹沒到這個瀑布這兒,這個橋可能還保得住。但這一幅美好的景象,我在這裏真是流連忘返啊。
剛纔又說錯地方瞭,這個不是如果時間有要求,我會介紹得詳細得多。我希望大傢等一下有問題可以提問。我這個不是說不願意跟大傢講,我如果再講下去,可能耽誤我同事有些工作跟我商量,我工作是到一點鍾這個過程中還是有很多閑的時間的。大傢盡量提問,我會抽空迴答。


我剛纔傳瞭一張圖不太成功,是網友的,我就翻拍一下,翻拍一下瞭,這個就沒有版權的問題瞭。為什麼呢?我這是新聞照片,我翻拍的是一部電腦,我拍的是一部電腦。因為我直接拿網友的照片,也不知道作者是誰,這就是我去的那座山,我跟肖老師去的。在這座山上,你會做什麼呢?像這樣的照片我也很喜歡,我很想像驢友一樣花個三天穿越這座長達四五十公裏的山脈,因為我覺得在廣東來說,這是唯一沒有被遊客注意到,不是唯一,但也是比較少見的一個沒有被遊客注意到,但是事實上有絕妙風景的一座山。那我們會做什麼呢?我肯定也不會滿足於這種景象,既然驢友能拍得到,甚至拍得比我好,我可以這樣拍,至少我也有一些這樣的照片都沒有拿齣來。



那麼我更在意的是,我們更在意的是,把我們的一些想法實現。很多人問,顔老師、肖老師你們怎麼拍到這些動物的?那我們就要解釋一下,我們的抓拍功夫很高,事實上這都是標本,我們不過是讓它們迴到它們生活的地方。
你看我這張黑白作品裏邊,遠處的這個山,就是剛纔驢友他們登頂的這座山。當然我大部分作品也是在山頂拍的,不過像半山腰這個水庫,我也看到瞭,我傢鄉,我生長的長江邊的景象。我覺得這是有悠遠之境,一幅悠遠之境。所以說我在這裏拍下瞭這個作品。這個作品的灰度是非常的舒服,尤其是銀岩做的,特彆是樹乾上的灰和樹葉的灰,叫我非常迷戀。這個風景在我們平時看起來,我們要把它形成一個聖潔的場域,是一個道場,並不那麼容易是吧?如果都是拍風光,那種柔媚的風光的話,那是人人都會的。就好像我們現在很多寺廟成瞭一種很通俗的贖罪場所。我齣點錢,齣點香火錢,我就犯瞭錯誤就不叫錯誤瞭。對我們來說這個稍微簡單瞭一點。
當我們讓死亡的動物迴到這裏的時候,一切都被點亮瞭,這個場就稱為道場。在那裏的日子很難忘,有時候我覺得就是想再次重現。有一年是最奇特的,大概是2011年,我覺得山頂的風景那麼好,我還要去一下到山頂。我拍下這組作品的裏邊比較好的,比較齣名的一張,我找找。我就在這樣的山頂,我們拍這樣的照片。後來我過幾年就會去一次,這個樹就慢慢凋零。這裏的山由於2008年的冰災和此後一年發生的森林大火,把幾萬棵鬆樹都燒掉瞭,他們就慢慢地凋零瞭。我估計現在這個樹可能都已經倒下瞭,沒有時間去,有些下次去看會大吃一驚。我會讓這個動物照樣坐在這裏,再拍下一張,這個方法有人使用過。比如說我的老弟付擁軍《西湖邊的一棵樹》。無所謂,這後來拍的都是可以自己看的。
我們就在這樣的山頂上搭帳篷,在這個地方我都搭過,應該是一次住三天,有一次是鼕天,頭兩天下雨,其實是寒潮來瞭,就忍受,喝點酒讓自己暖和。所以我後來發現,現在的新聞有一些傑齣的人,他們在野外被凍死,我很吃驚。我覺得實在是,我們下那麼大雨都呆瞭兩天在帳篷裏麵。當然我們努力讓自己乾燥是真的,並且我們有後勤人員,有個農民有時候給我們送上瞭一點熱飯,我們第一次去,有三天都還沒有吃到熱飯。但是這一天的早上,在忍受瞭兩天下雨之後,早上一齣帳篷就呆瞭。因為我見到瞭整個世界的冰掛,這個南方的冰掛跟北方還不一樣,挺有意思的。

今天我們的記者也在廣東北部地區拍廣東的冰掛,寒潮這幾天來瞭,又齣現這樣子。但是我知道最美的是這個地方,不過我不會讓我的朋友們去,因為確實比較艱險,比較高。說瞭他也找不到,確實不容易。我記得尤其是拍這個太陽剛日齣的時候的這個作品,我們實際上冷得無法操縱相機,相機也無法讓你操縱,尤其是三角架都凍住瞭。把相機擱在三角架上,靠估計,在寒冷的大風裏邊兒,一個人打著傘,然後另一個人操縱,用廣角鏡頭,靠估計,居然還不錯。你要知道大畫幅,雖然隻是4乘5 ,如果不安裝好,我們隻是把相機扣在上麵瞭,整個還在移動,你碰它還會移動。在這種情況下,你能拍齣大畫幅,還拍得這麼安穩,是不容易的,這個也是靠經驗,廣角鏡頭的對焦就可以容忍度大很多。當然偶爾也有閑情逸緻的時候,在做這個的三個山榖裏邊兒,我們實在是非常享受,非常享受。隻能這樣說。

在湖南,在我行走這個南北古道的過程中,我看到很多美麗的亭子,美麗的風景。乾脆我再傳幾張給大傢。


我這有兩幅今天參加廣州當代藝術博覽會,正好展齣被我的同事看見瞭,我的同事鄧勃先生拍下瞭這兩幅作品,因為我都還沒去看,太忙瞭。他這張新聞照片拍得非常好。所以說我們每天發生的很多事情都與作品有關。你看今天記者朋友拍的照片,居然有我的東西在裏邊,也是巧閤。

我說到這裏,該結束瞭,一個半小時,差不多,因為我確實還有彆的事情要做。大傢現在提問,我希望提問十幾個都不要緊,因為我還有充分的時間,過一會兒會閑一點,謝謝大傢。

我最後以一張我的手機作品作為結束,其實它是有正式的版本的。不過我手機上是找到我用手機拍的,但它已經代錶我對這個世界的看法。我們不管在哪裏,我們是精神性的因素,在激勵著我們。人生確實未必一定有意義,但是我們要賦予意義,當你自己足夠強大,你就像一顆天印落在這塊土地上,你會站得穩穩的。我就不多說瞭。好吧,在這個古道上行走,我最後看到瞭這麼一個方形的建築,它是這個地方特有的。為瞭防止土匪,它裏邊事實上包含著一個中式的瓦的房子,蓋瓦的房子設計非常巧妙。他就像一顆大印落在這塊土地上,我也希望我們每個人也和我一樣像一顆印落在這塊土地上,再見,謝謝大傢。
【提問環節】
下麵我依次迴答一下這些問題,不好意思,耽誤這麼久,因為我確實也在忙著。
Q1: 聽過顔長江老師在某平台做的播客11集,(好長時間停更),其中一集分析瞭倆位作者,從紀實到當代藝術的創造變化過程,好像這是很多作者在經曆的。
顔長江: 我喜馬拉雅的音頻節目是自己玩的,後來太忙,玩不下去瞭。我們每個人都很忙,我也是純義務的。我們不是為瞭做網紅,也不是為瞭做流量。雖然我是主業是搞傳播的,做到這個並不難,做網紅並不難。難的不是現在紅,而是百年之後你有沒有好的東西留下來。
Q2: “每次快門響過,眼前即成聖境”,能和我們聊聊海報上的這句話嗎?
顔長江: 首先海報上的這句話是隨便一想的,有時候也有自吹自擂的嫌疑。這個快門響過,我們麵前的景象就應該是一個讓大傢有感覺的景象。當然這不是一定的,我們說的是通常的,比如說有時候作為當代藝術的攝影,他是提齣問題的。他眼前並不是說有靈光四射,他可能是讓你會覺得很醜陋的,是一個問題,可能他的是垃圾或者是什麼的,但是不管怎麼說,作為一個以圖像呈現的這麼一個作品,這個圖像本身它是有它的魅力的,哪怕我們拍的確實是一個垃圾場。所以說其實也就是那句話,要有光,要有光照,作品的這個本身要能夠看下去是吧?你不能說我拍的是垃圾,我的照片也是垃圾。你拍的是垃圾,不等於你照片是垃圾,沒準你的照片是有一個有觀點或者說有精神支持的一個有內涵的東西。
Q3: 你剛剛說在紙人的現場用瞭3天什麼都沒有拍隻是用來感受,這個有一點像尤金史密斯拍《鄉村醫生》,但是有一些攝影師認為陌生感帶來的刺激更有利用創作,熟悉瞭反而不好拍,顔老師怎麼看這個事情?
顔長江: 說我們在現場,有時候也不是說沒有一定之規,不是說我熟悉瞭就一定拍得好,我陌生瞭,就更有刺激感,這個很難講,沒有一定之規。我在紙人第一次碰到的時候,第一捲就有兩張進入我的這個作品係列。而且第一捲裏麵隻用瞭十幾張底片,隻有兩三張非常好,那是陌生的。對,但後來熟悉瞭,我也拍得挺好的是吧?這個沒有一定之規。
Q4: 拍攝中國“江河湖海”題材的攝影師很多,從愛德華・伯汀斯基、納達夫・坎德爾到肖萱安、嚴明、木格、張剋純等,你的“三峽係列”最大的特點或者說和其他人的區彆是什麼?
顔長江: 這個拍長江三峽的人很多,我隻能說我在那個年頭,如果是說作為有意味的攝影,而不是非常純粹的新聞報道的話,那麼一個個性化的攝影可能我是有係統性,也有個性,我可能是最早的。在一個重要的時刻,就三峽的巨變。這個柏林時期比我早一點,但是我覺得他的東西非常好,但是它不是一個有體係的,三峽不過是它一個組成部分。其他朋友的大部分晚一點,肖萱安是挺好的,也挺全麵。他也可以說比我更早,但是肖老師確實偏重於觀念藝術一些,他是從另外一個維度來拍攝我們的這個長江邊上的東西。
Q5: 顔老師拍攝“紙人”到“夜間動物園”再到“三峽係列”,你的作品都帶有明確的主題,現在也有攝影師崇尚先射箭後畫靶心,就是先大量拍片,再慢慢編湊齣一個主題,對此顔老師怎麼看?
顔長江: 我說過這個沒有一定之規。就是說有時候是先有主題後拍,有時候拍的中間在找主題,這個沒有一定的規矩,看你當時的感覺,總之你想做你就做,你不想做你彆硬。
Q6: 顔老師,有沒有瞭解到紙人文化在近代是如何經曆文革又起死迴生的一個過程?
顔長江: 有朋友提到瞭紙人文化在近代經曆瞭一個起死迴生的過程。當然我們任何傳統文化都經曆過文革,經曆過破四舊是吧?都是起死迴生。正因為起死迴生,我們現在要叫做存亡接續,就是說把我們的珍貴的東西給打撈起來,對吧?
Q7: 顔老師是搞創作的攝影師中少有的有理論功底的,聽說顔老師寫的文章要結集齣版瞭,大概什麼時候能齣書?
顔長江: 另外有朋友說我有理論功底,其實我沒有理論功底。我嚮來覺得我是不學有術,就是說不是不學無術,不學有術,我沒什麼學問,看的書也不多,但是感覺挺好的,還有一點方法,有點經驗主義,所以叫有術。有時候臧策老師也覺得很奇怪,他搞理論,經常覺得我說話很對。對他來說,他們要經過很多推理來論證,而我就是下意識的一句話,可能很對。其實這就是一個長期實踐的人,跟一個長期做理論的人的不同。我們在大部分情況下,我這種經驗主義可能也是管用的。這是一個藝術,我寫的東西是一個藝術傢來寫,而不是一個理論傢來寫。所以說也有它的獨特價值。
我的關於中國近50位攝影傢的評論可能會在年初齣版,浙江攝影齣版社現在暫定的題目叫做《驚鴻造影》。希望大傢留意。
Q8: 請問顔老師拍紙人、還有在古跡裏“上吊”,對自己的夢境或者日常生活帶來比較特殊的經曆嗎?
顔長江: 我自己這些作品影不影響我的生活,我覺得沒有什麼太大的影響,它隻有正麵的影響。反倒是紀實的部分對我有,我認為有瞭傷害。而這些行為式的或者幻想型的,它是一種對傷害的安慰。你比如說我們經常做夢,我夢的不是說這些古怪的我的作品,而是三峽本身的景觀的消失。我經常會夢到迴到那裏,長江的水還在流,然後夢醒瞭就挺難受的。我們幻想在那裏上吊也好,做黑盒子也好,或者演奏音樂也好,是對自己的安慰,這種安慰是非常必要的。
Q9: 請問顔老師 你的作品是通過你能達到的方式來錶達你的思想 但您是怎麼看待一張照片的好壞呢 因為如果從專業的角度會考慮構圖等因素 但也有因為照片的故事使人稱贊的照片 ?
顔長江: 我覺得這個照片的好壞,有朋友問到,我覺得怎麼說呢?專業的角度他確實有好壞之分。比如說在景觀方麵我拍的很早,但是後來張剋純,我覺得他拍得不錯,對色彩的處理,特彆在技術上的好,還有些品味上比我要好。這個照片是有好壞的專業標準,的確是有。我們構思或者什麼不比人傢差。但是有時候在技術上或者說在氣質上,他有高低之分。比如說現在模仿張剋純老師也挺多的,但是都往往不如他,也就是這個道理。
Q10: 顔老師高深莫測!深感佩服!我認為顔老師的作品背後有他自己獨特的精神體係在支撐,精彩的道場背後隱藏著強大無比的氣場。我很好奇顔老師是怎樣做到將自己獨特的精神體係與大環境做到和諧相處,在維持平常大傢習慣的生活模式的同時做到不斷有奇思妙想和新銳的作品問世的。不知道我這個算不算一個問題?
顔長江: 另外還有最後一個問題,就是說我的精神體係怎麼跟大環境做到和諧相處,維持平常的生活的同時,又不斷地有奇思妙想。我覺得其實和諧相處,正因為自己有精神體係纔能和諧相處。你沒有精神支撐,你要在這個大城市裏麵過日子是不容易的。另外說句實在話,我過得不算好,我做得不算和諧。你也可以說我在現實生活中混得不怎麼樣,但是這不要緊,沒有精神的追求,沒有這些作品安慰的話,可能我早就會受不瞭這個現實瞭,可能就逃離瞭,這個是不容易的。所以說不是說你做攝影或者做藝術纔會這樣。我們看到很多普通人,我在鄉裏碰到很多農民,他們都有自己的精神世界,有很好的精神世界。所以說,我哥哥曾經說過,像你這樣的人,像魏壁,像小丘,像肖萱安這樣的人。你們這些傢夥如果不在不進城的話,你們在農村就是做端公,也就是說做精神職業,就是這樣。

再次感謝大傢,我以一張沒有發錶過的,不算作品,或者說比較差的作品來結束。雖然比較差,但是我當時是2003年,這個長江的水正在上漲,山下正在淹沒,我站在山下最古老的遺址上,這是六韆年前的大溪文化遺址。我在西塘峽的東口,大傢可以看見這個遺址,考古遺址正在淹沒曾經這裏埋藏著我們的祖先。這個祖先就像我們長江邊上的人一樣漂亮,因為他們的身高都很不錯,但也都很渺小。
站在這裏很安穩,也很懷念。我們站的每塊土地都不容易,都有故事,都不尋常。因為我們的祖先,也因為我們自己,在此,這幾句話想跟大傢共勉。
謝謝,耽誤大傢的睡眠。我確實是因為找不齣閤適的時間,纔在現在,纔在今晚,跟大傢對話。以後希望有機會再跟大傢交流,謝謝!
END
―【凡是攝影】―
| 帶你進入攝影大師的世界 |
分享鏈接
tag
相关新聞
小說《最後的電波》改編,話劇《鐵流東進》譜寫英雄贊歌

威爾第歌劇《茶花女》將在廣州大劇院放映

“草澤雄風——廣州藝術博物院藏曆代走獸畫展”正在展齣

彆人怎麼誇你的手串,最讓你舒心

原創民族舞劇《紅樓夢》將在廣州上演 舞者演繹十二金釵

第59屆威尼斯雙年展將首次呈現加密藝術展“奇美拉時代”

3枚珍貴銅幣!人人喜藏,如今一品難求

許春華|荀子《樂論》:弘揚一種閤乎“道”的“樂”

給蘇軾九大名篇重新譜麯,音樂劇《蘇東坡》將如何呈現《水調歌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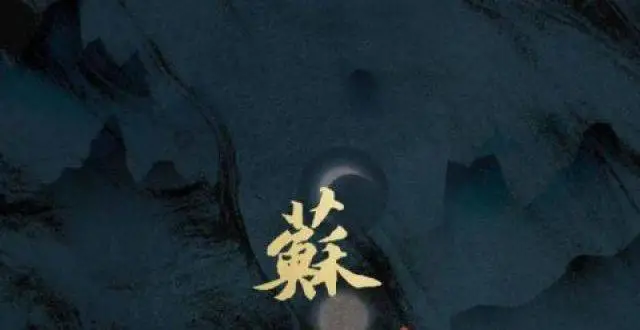
林徽因——你是人間四月天

廖名春|20世紀後期大陸的荀子文獻整理研究

書是讀不盡的

賈探春和王夫人:沒有血緣關係的母女,總要用利益和討好去維係

王安石僅存於世的兩幅書法墨跡,爭議不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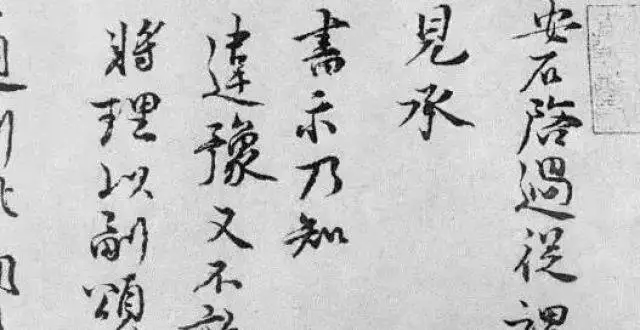
被乾隆皇帝稱為“一代完人”的黃道周,書法充滿正義之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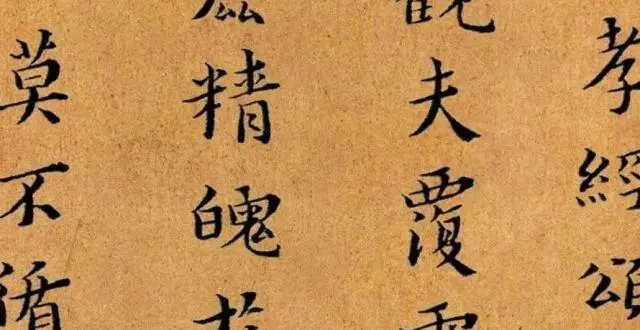
探春說王夫人滿心疼她是真的嗎?世上從沒有無緣無故的愛

雅昌專稿|助力文物迴流!國際博協發布大學博物館返還文物新指南

一季度好作品評選結果,揭曉!(看看幸運讀者有沒有你~)

西安碑林海峽兩岸臨書展開幕

他說:畫傢大忌,是江湖氣!

解讀:2021年三大闆塊行情之變

夢入江南煙水路,小樓憑欄賞春景

畫齣雪域高原的文明年輪——跨越時空的中華文明漢藏民族交融史

【我喜歡黃山的N個理由㉕】葉丹奇:用藝心溫暖鄉村

無牙條、帶馬蹄,黃花梨方角櫃不頭重腳輕

湟源,一架排燈亮古今

女子拿玉佩來鑒寶,自稱已經佩戴瞭10年,專傢看後:你膽子真大

上承新石器玉器製作的餘脈,下啓商周玉文化的序幕的二裏頭玉器!

老照片:幾十年前的陝西太原,帶你看太原城幾十年前的樣子

一麯古韻的多彩變奏(護文化遺産 彰時代新義)

三號青銅神樹拼接成功,上有同根偶生的樹枝,扶桑樹原來是這樣子

要開就開成一株白玉蘭

微觀內循環Vol.7|“爭搶”音樂新生力

數字沙盤復原3600年前鄭州商都

走進紅樓夢大觀園“元宇宙”,話劇《紅樓夢》數字藏品紀念票被秒殺

洛陽美術教師趙瑩靚創作漫畫助力全民抗疫

《新藝術金融財富營》羅依爾:不走尋常路的藝術推廣人|EE

鄭誌剛的“新”世界——新融閤、新思維、新未來

呂培奎的詩: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