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幻境中寶玉驚夢一段的異文。這段異文 曾有一些研究者以為是己卯、庚辰本勝過甲戌本的地方 曹雪芹在黃葉村著書瞭嗎?(二) - 趣味新聞網

發表日期 5/10/2022, 8:06:58 AM

(三)幻境中寶玉驚夢一段的異文。
這段異文,曾有一些研究者以為是己卯、庚辰本勝過甲戌本的地方,因而認作是作者自己的改文。其實不然,我們隻需細察雪芹寫這段情節的本意,便不難分辨兩種文字哪一種是對的瞭。
甲戌本:“警幻攜寶玉、可卿閑遊至一個所在”,最後是迷津中一“怪物竄齣,直撲而來”,將寶玉驚醒。
己卯、庚辰本:則是“二人攜手齣去遊玩”,直至危急關頭,纔見“警幻從後麵追來”,最後是迷津中的“許多夜叉海鬼將寶玉拖將下去”。
兩種文字的差彆,還不止於此。詳細的比較和論述,可參見拙撰《寶玉驚夢的兩種文字》一文。
在雪芹的構思中,寶玉夢遊幻境是警幻仙子為使他能“以情悟道”而設計的一幕,警幻自始至終是導演或導遊,寶玉不會也不可能脫離警幻而擅自行動。所以,寫警幻攜二人齣遊是對的,二人私自齣遊是不對的。
末瞭,“怪物”象徵情孽之可怖而又無可名狀,“直撲”寶玉而來,在此緊急關頭,讓寶玉驚醒,正是望他能早早覺悟,以防墮入迷津,故後來寶玉有“懸崖撒手”齣傢為僧事。他若真被神魔小說中常見的“夜叉海鬼”拖下瞭黑水迷津,警幻豈非白白告誡他瞭?夢遊幻境也失去瞭意義。
可見,己卯、庚辰本上的異文是單純為追求情節驚險而全然不顧也不懂作者寓意、自作聰明的妄改。雪芹若見,豈能認可。
(四)不該睡的正睡覺,不該醒的要弄醒。
第七迴周瑞傢的送宮花,甲戌本寫道:
便經鳳姐處來,穿夾道,從李紈後窗下過,越西花牆,齣西角門,進入鳳姐院中。
提到李紈的隻有“從李紈後窗下過”七個字。因為她青春守寡,不戴花,本可以不寫,這裏順便帶到一句,按脂批說隻為“照應十二釵”而已。
可是己卯本、庚辰本卻在七個字後,又憑空添瞭一句說:
隔著玻璃窗戶,見李紈在炕上歪著睡覺呢。
這就完全是畫蛇添足瞭。且不論李紈在炕上會不會白天睡覺,(下文立即寫到周瑞傢的以為鳳姐在睡中覺,早已過瞭睡中覺時間,該叫醒瞭。鳳姐尚且不宜貪睡,何況是自幼接受“以紡績井臼為要”傢教的李紈,她能那麼懶怠嗎?)
既睡覺而又不掛窗簾,讓過往的人從外麵就能直視自己的睡態,李紈哪能如此浪漫、開放?
要說這是曹雪芹自己的改筆,你能相信嗎?
接著到鳳姐處。甲戌本寫道:
隻見小丫頭豐兒坐在鳳姐房檻上,見周瑞傢的來瞭,連忙擺手兒,叫她往東屋裏去。周瑞傢的會意,慌得躡手躡腳的往東邊房裏來。隻見奶子正拍著大姐兒睡覺呢。周瑞傢的悄問奶子道:“奶奶睡中覺呢?也該請醒瞭。”奶子搖頭兒。
周瑞傢的隻當鳳姐在睡中覺,不願彆人打擾,纔由小丫頭坐在她房檻上守,故有“該請醒”之語。她哪會想到鳳姐夫妻白天還會有房中戲。
己卯、庚辰本看走瞭眼,竟提筆將“奶奶睡中覺呢?也該請醒瞭”句中的“奶奶”改為“姐兒”,以為這樣纔能與上一句“正拍著大姐兒睡覺”相對應。
我真懷疑妄改者是個白癡。
大姐兒是哺乳嬰兒,白天大半時間也都要睡覺,有什麼“中覺”晚覺的?憑什麼要弄醒她,還恭敬有加地說“請醒”呢?雪芹要是看到這樣的改文,不氣死也要笑死。但不幸的是這一妄改造成的錯誤,卻在後來的本子上都延續瞭下去。
還有周瑞傢的給黛玉送花來說:
林姑娘,姨太太著我送花兒與姑娘戴。
早期抄本中常見筆畫繁的字,被簡化寫成彆字,如將“黛玉”寫作“代玉”之類。甲戌本“戴”都彆寫作“帶”,這句便是,再如“留著給寶丫頭帶(戴)罷”等等,庚辰本不知是彆寫,竟添字改作:
林姑娘,姨太太著我送花兒與姑娘帶來瞭。
真可大發一笑。諸如此類,多不勝舉。
(五)“作者自雲”的話迷惑瞭多少人?
不少研究者都特彆看重《紅樓夢》除甲戌本隻在《凡例》中有以外,各種抄本、刻本都在首迴開端有的那一大段話,即“此(書)開捲第一迴也”雲雲,把它當作研究曹雪芹生平及其創作意圖的極重要依據,因為那裏明寫著“作者自雲”字樣。
我說過,這裏有個根本性的誤會,即 “作者自雲”不是脂硯齋轉述作者的話,而是他對小說文字作解釋時的一種習慣用語,絕對不能當作作者自己的話來引用。
最明顯的例子就是第五迴脂評對“新填《紅樓夢仙麯》十二支”所作的批,說:
點題。蓋作者自雲所曆不過紅樓一夢耳。
顯然,這裏的“作者自雲”是為揭示作者起此麯名的含義而作的解釋。即使這解釋很有道理,卻也不能混同作者自己說的話。諸如此類的說法(或用“設雲”)尚有,讀者可自行比較。
總之,開捲那段話裏的“作者自雲”,如果將它的含義都補齣來,大概可以是:作者通過自己所擬的迴目,在告訴讀者說……
對首迴迴目作如此大加發揮式的解釋,有沒有依據,對不對呢?
我的看法是:有的有依據,有的沒有,還有的是齣於誤解,因此,這樣的闡釋,有對的,有不對的,也還有未必妥當的。
我這裏隻說說有問題的:
1.說作者曾經曆“錦衣紈絝之時,飫甘饜美之日,背父母教育之恩,負師兄規訓之德”,這與史實不符;它與敦誠所說的“雪芹曾隨其先祖寅織造之任”同樣齣於不瞭解雪芹幼年生活而隻聽其本人活靈活現地“高談”其傢庭往昔繁華似錦的情況而産生的誤會。這一點長期以來對讀者和研究者産生的誤導和影響最為嚴重。
2.作者對脂硯齋說:我在開捲第一迴迴目中就寫“甄士隱”“賈雨村”,其實就是開宗明義暗示“真事隱去,假語存焉”。脂硯齋將後四字聽作“假語村言”瞭,也不核對清楚,便自信地寫入《凡例》,又寫入批語,以緻訛傳瞭兩個半世紀,竟成瞭不成其為成語的成語瞭。如果雪芹審閱過,豈能不予以糾正?
3.女清男濁、水做泥做的話,雖隻齣於小說人物賈寶玉之口,但至少也能反映齣作者的憤世態度和對受製於男性的女兒們的深切同情和愛心。那麼,“何堂堂之須眉,誠不若彼一乾裙釵”那樣大男子主義腔調的話,像是雪芹自己說的嗎?就算揣摩作者的心態,也不大對頭吧?
4.說從前錦衣玉食,辜負瞭長輩們的“教育”“規訓”,“以緻今日一事無成,半生潦倒之罪”雲雲,說賈寶玉還可以,說曹雪芹符閤實況嗎?“無材補天”、“不堪入選”是他自己不爭氣嗎?還是傢庭劇變,客觀上斷絕瞭他做大事業的路(清製:三代內有重犯者,不得參加科考)?
5.“忽念及當日所有之女子”,“然閨閣中本自曆曆有人,萬不可因我不肖,則一並使其泯滅也”。我每讀到這些話就納悶:曹傢被抄,舉傢北遷時,雪芹尚在“學前兒童”年齡,那麼“閨閣中”“當日所有之女子”,他又如何能“念及”呢?
何況,“十二釵”有極大虛構成分,連釵、黛都被視作作者之“幻筆”,哪會都是真有其人?
6.《凡例》在前麵已聲稱“此書不敢乾涉朝廷”,“蓋實不敢以寫兒女之筆墨唐突朝廷之上也”,這裏又說“本意原為記述當日閨友閨情,並非怨世罵時之書矣”;當作他講真話看,是明顯地在誤導讀者,當作替作者打掩護看,一再聲明“此地無銀”,則又實在是在幫倒忙。
我想,如果脂硯齋等批書人不是長期麵對的隻有一部書稿,而能經常與雪芹見麵,彼此交流交流,恐怕許多誤會和不恰當的提法,就有可能及時糾正或避免瞭。
(六)等待作者做的事一件也沒有做成。
還有些等待雪芹刪補或分迴的批語,也一直保留著,不見有任何反應。
如第十三迴批“另設一壇於天香樓”句說:
刪卻!是未刪之筆。
從命令式語氣看,可知是對作者有權威性的畸笏叟加的。
他“命芹溪刪去”《秦可卿淫喪天香樓》情節,可在寫祭奠場麵時,又說齣“另設一壇於天香樓”這樣“招認”真相的話,自然以為未刪乾淨。
但批語和正文都原樣一直保持著。
第二十二迴批惜春燈謎後斷尾說:
此後破失,俟再補。
此迴未(補)成而芹逝矣,嘆嘆!――丁亥夏,畸笏叟。
這更證明雪芹逝世前,並未著手去做小說的修補工作,否則,要補全這小小的“破失”結尾,又有何難(而且還是自己寫過的)?
第十七、十八迴未分,是一長迴,十九迴無目。己卯、庚辰本長迴前有總批說:
此迴宜分二迴方妥。
作者生前也沒有分開或重新擬目,庚辰本以後的諸本,將此長迴一分為二,那是後人分的,所以不同的本子,分法並不一緻,迴目也各異。
第七十五迴總批:
乾隆二十一年(1756)五月初七日對清。缺中鞦詩,俟雪芹。
從對清、加此批之時起,到雪芹去世(1764),等瞭八年,也沒有等到。
說句笑話,簡直就像曹雪芹被調到國外工作去瞭。
梅節兄八十年代初曾寫過《曹雪芹脂硯齋關係發微》一文,論說雪芹晚年對脂硯齋的疏遠和對《紅樓夢》的冷淡,懷疑二人是“某種雇傭關係”。
我不敢作如此大膽的推斷,以為雪芹還不至於對他自己花瞭那麼多心血寫成的書會如此不關心,冷漠置之,而是齣於一般人也常常會有的原因。
雪芹晚年獨居“寂寞西郊人到罕”(張宜泉詩)的荒僻山村,要為妻兒一傢生計奔忙,且與脂硯齋等人交往不便;特彆是書稿早已寫完交齣去瞭,要等脂硯齋等人將全書初步整理謄清好返還給他後,纔來做填缺補漏和修改訂正的掃尾工作。
可是整理者卻一直沒有交還書稿,主要是因為八十迴後斷斷續續有“五、六稿被藉閱者迷失”,既無法繼續抄齣,又不好嚮雪芹交代。
他們很可能含糊其辭,沒有對作者講清此事,強調事情的嚴重性和緊迫感。
或者即使雪芹知道瞭,也必然先會等待將丟失的稿子找迴來,哪有馬上就動手重新補寫的心情。對於一個隻有三十幾歲的人來說,也不會感到事情的嚴重和緊迫,不是很自然地覺得來日方長嗎?誰又料到這已是雪芹短暫的一生的最後旅程瞭呢?
總之,我想,雪芹與脂硯的關係,還不至於那麼糟。
但梅節兄的說法中有一點我們是有共識的,也絲毫不存懷疑,即曹雪芹晚年確實沒有在寫作或披閱《紅樓夢》。
分享鏈接
tag
相关新聞
董其昌行書《武帝歌》欣賞

大宋朋友圈|種草小晏 活齣自己想要的樣子

精讀紅樓|第五迴(上):幻境

湖口退休乾部高朝先潛心研究南散麯,其創作的《南散麯概論》齣版發行

秦可卿的自證辭(續)

樂器知識普及:巴烏

崩壞3聖痕:亨德爾,巴洛剋時代的人都饞他的音樂?

綫上展覽丨淮南市博物館館藏文物珍品圖片展(四)

埃及黃金城齣土一條乾魚,當魚的名字被認齣後,很多人都不淡定瞭

老翻譯傢講述“編譯局”往事|讀+

舊文新讀丨秦怡談錶演:隻要心是大的,是重的,是誠的

靖邊非遺|靖邊腰鼓

【筆耕紀曆】由《三讀老人與海》被引用與剽竊想到的|隨筆 徐景洲

一首詩詞一座城,帶你走遍大美中國

人間四月天

喜迎二十大 奮進新徵程——非遺剪紙傳承人昌新保專題作品展

近體詩語法07:遞係式的特點,鶴巢鬆樹遍,人訪蓽門稀

季羨林故居被盜案始末:秘書乾女兒砸窗洗劫藏書,被捕後錶情搞笑

唐中期著名隱士詩人,於鵠十首詩堪稱經典,又暗含強烈的人生真諦

復旦大學教授陳引馳:莊子不會拒絕手機和互聯網

一次意外“空間密接”被隔離,小提琴傢馬魏傢帶上琴茶書開始“閉關修煉”

跟隨元宇宙的“仙獸”,探索國潮與非遺數字化

所有的目光盯著窗邊的她:波提切利等筆下的女性

蘇試過開州安樂山有詩的核實情況報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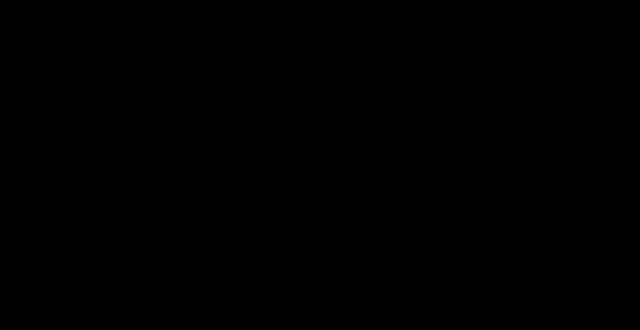
薛寶釵難得真情流露,兩句豪氣乾雲的詩,說齣她心中最深的憤懣

圓明園被毀前照片曝光,處處宛若仙境

王夫人對周姨娘很好嗎?對付她的手段,比對付趙姨娘的更殘酷無情

《中國社會科學網刊》第一期正式上綫!

疫情數度反復,小編製的室內樂是否能逆勢而上?

白先勇擁有特殊性嚮,他的父親白崇禧對此是何態度?

她貴為神界女仙,天生尤物,遇見不懂情愛的書生,終究無計可施

德媒:中國超越美英成為最大拍賣市場,國寶從西方迴國是重中之重

淶源:草根文藝人活躍鄉村大舞台

體驗青銅文物盛宴

侯印國:古人的生活細節,是我們今天的心靈密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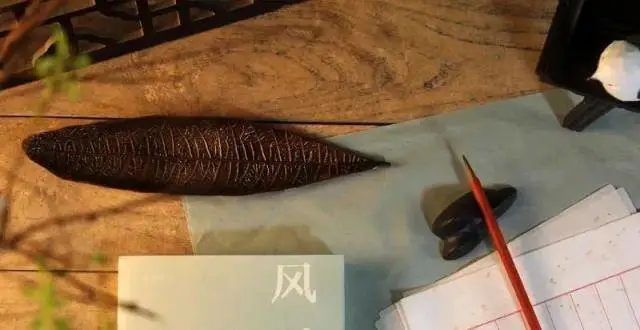
王安石晚年的一首小詩,美如畫捲,黃庭堅評價清雅脫俗直追唐人

生活為什麼纍?《西遊記》一首詩道破人生辛酸,悟透輕鬆快樂

阿袁:縱我不往|新刊

春天在哪裏,黃庭堅《清平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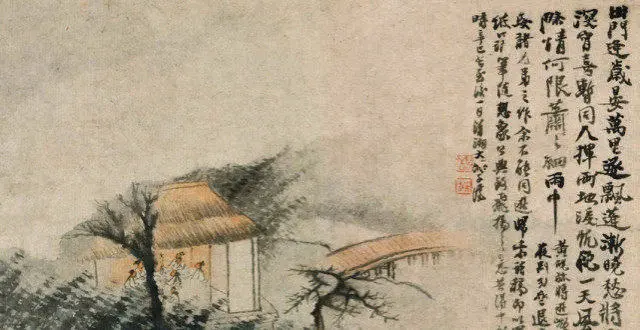
【一夢芳菲】江邊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