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前 文 迴 顧��(點擊文字鏈接可跳轉閱讀)作者許仙我秦氏秦可卿的自證辭 已在上迴略錶。知我者不錶便明 秦可卿的自證辭(續) - 趣味新聞網

發表日期 5/10/2022, 8:10:55 AM

前 文 迴 顧
��
(點擊文字鏈接可跳轉閱讀)



作者
許仙
我秦氏秦可卿的自證辭,已在上迴略錶。知我者不錶便明,略說更明,無須再說一字。隻是,《紅樓夢》第五迴文本已留,還有脂批也在,思前想後,覺著繼續往下看看有點必要,不為自證,或者還有彆的話能有於己於人皆為可留意處。
那寶玉剛閤上眼,便惚惚的睡去,猶似秦氏在前,遂悠悠蕩蕩,隨瞭秦氏,至一所在。
寶叔在我房裏閤眼睡去,在他的夢裏是隨我到瞭一個地方。那麼,我入寶叔夢應該是可以理解的。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與中國的文化,也都承認“心有所思,夜有所夢”。由此推展開來,夢無非是夢者所屬生活的一種特殊錶現形式,生活本身就是夢的重要來源之一,這應該沒有什麼難理解的。
還有一點,夢畢竟不是清醒生活。所以,現實之我也不見得與夢中之我一樣,所以,不用一見我在就不拿正眼看。再看脂批:
此夢文情固佳,然必用秦氏引夢,又用秦氏齣夢,竟不知立意何屬?惟批書人知之。
脂硯齋的話說得很明白,用我秦氏引夢和齣夢是有立意的。立意為何,作為批書人的脂硯齋知道。其實,脂硯齋這樣說,並不是說曹雪芹寫《紅樓夢》就是為自己寫、給脂硯齋看的。一個人耗費那麼長的時間和精力、費那麼多的筆墨,就為給自己和脂硯齋等少數幾個人看?
的確,手寫時代,曹雪芹未必做洛陽紙貴的夢。但是他也不大可能隻寫給自己和脂硯齋等三兩個人。至於曹雪芹究竟怎麼想的,我不知,旁人也未必知。如果人們認可脂硯齋,那麼就參考參考他的說法;如果脂硯齋信不過,不要緊,不信他,不看他的評語,這就有瞭。

寶叔是午睡,是睡中有夢。那麼接下來他的夢裏想法,怎麼理解呢?
寶玉在夢中歡喜,想道:“這個去處有趣,我就在這裏過一生,縱然失瞭傢也願意,強如天天被父母師傅打呢。”【甲戌側批:一句忙裏點齣小兒心性。】
對寶叔夢裏想在所到之處過一生的想法,脂批說是“小兒心性”,曹雪芹在下邊用的是“鬍思”作評。如果信脂硯齋,那曹雪芹的話便好理解。如果撇開脂硯齋的話,隻看“鬍思”,那麼這就看看的人怎麼想瞭。疑心重的人看到這裏,有可能將這裏審賊似的審起來沒完,非審到那賊鬍說八道不可。
好瞭,我引寶叔入夢的事算完成瞭。身上沒病,不怕冷年糕,隨人怎麼想去。接下來齣來的是警幻,警幻齣場先是歌,其中有這樣兩句:
寄言眾兒女,何必覓閑愁。【甲夾批:將通部人一喝。】
脂批說“將通部一喝”,通部,可能指《紅樓夢》一書的全部,通部人,或指《紅樓夢》裏人,不僅寶玉一個,也包括其他,黛玉、鳳姐、王夫人、賈母等等。一喝,警醒意。比如前有懸崖,而人猶在夢裏而不覺,一喝或能阻止跌落懸崖的危險矣。例子未必閤適,留待細想。
多說一句,警幻先以這個“寄言”開頭,無非像《紅樓夢》曹雪芹開頭“滿紙荒唐言”一樣有提醒意,“滿紙荒唐言”提醒閱者,“寄言”提醒眾兒女,提醒《紅樓夢》中人,難道就不提醒《紅樓夢》外人!多少人看《紅樓夢》不聞其“喝”,猶如閉目、塞耳,不聞不見?
警幻齣來,書上用一長賦來寫她的美。說句不好聽的,警幻之美無非作者有意為之。究其實,也不過是人間美的一個泛泛而寫罷瞭。難道還有獨一無二的絕世之美?
當然瞭,寫警幻之美不是重點,隻是形式,隻是手段。無論《紅樓夢》文本,還是脂硯齋評批,都不會隻停留在外錶美麗的空殼上。

第五迴凡有我處我就說說,無我處我就忍痛割愛,暫且不提。剛纔看瞭看,下一長段因為有我,所以將原文搬來,脂批雖仍可貴,也將其忽略不計:
寶玉見是一個仙姑,喜的忙來作揖問道:“神仙姐姐,不知從那裏來,如今要往那裏去?也不知這是何處,望乞攜帶攜帶。”那仙姑笑道:“吾居離恨天之上,灌愁海之中,乃放春山遣香洞太虛幻境警幻仙姑是也。司人間之風情月債,掌塵世之女怨男癡。因近來風流冤孽,纏綿於此處,是以前來訪察機會,布散相思。今忽與爾相逢,亦非偶然。此離吾境不遠,彆無他物,僅有自采仙茗一盞,親釀美酒一甕,素練魔舞歌姬數人,新填《紅樓夢》仙麯十二支,試隨吾一遊否?”寶玉聽說,便忘瞭秦氏在何處,竟隨瞭仙姑,至一所在,有石牌橫建,上書“太虛幻境”四個大字,兩邊一副對聯,乃是:假作真時真亦假,無為有處有還無。
警幻齣來,我便要下去。這裏言明,寶叔與警幻一番簡短的充滿禪意的對話後,便忘瞭“秦氏”我,而隨著警幻往前走瞭。――《紅樓夢》至此,我說瞭哪句錯話,做瞭哪點錯事沒有?即便我主動承攬安置寶叔午睡的任務,並且最後安排在我的臥榻,這於中國的文化傳統有違嗎?
很多的權威的研究者,都撰文對我的做法予以肯定和支持。難道這還不夠,還要曹雪芹齣來說我這樣做沒錯纔肯罷休嗎?難道連權威研究者的意見都不想參考,這不就像是讓曹雪芹一邊去涼快嗎?
警幻!警幻!看官可注意警幻義?賈寶玉,賈字與寶玉閤在一起,不知可有寶玉不寶之義;而警幻的警和幻閤在一起,或者有當頭一喝義。
多少研究者都強調過《紅樓夢》第五迴、前五迴,而多少普通人不知彆的,卻也都知道前五迴的一鱗半爪,這都在說明《紅樓夢》的價值不僅體現在其他地方,如五迴以後的各個章節,也體現在前五迴、第五迴,甚至是第五迴的某處某處。

好瞭,如果我沒看錯,那警幻在這裏提到我的名字:
警幻道:“非也。淫雖一理。意則有彆。如世之好淫者,不過悅容貌,喜歌舞,調笑無厭,雲雨無時,恨不能盡天下之美女供我片時之趣興,此皆皮膚淫濫之蠢物耳。如爾則天分中生成一段癡情,吾輩推之為‘意淫’。‘意淫’二字,惟心會而不可口傳,可神通而不可語達。汝今獨得此二字,在閨閣中,固可為良友,然於世道中未免迂闊怪詭,百口嘲謗,萬目睚眥。今既遇令祖寜榮二公剖腹深囑,吾不忍君獨為我閨閣增光,見棄於世道,是特引前來,醉以靈酒,沁以仙茗,警以妙麯,再將吾妹一人,乳名兼美字可卿者,許配於汝。今夕良時,即可成姻。不過令汝領略此仙閨幻境之風光尚如此,何況塵境之情景哉?……”說畢便秘授以雲雨之事,推寶玉入房,將門掩上自去。
在警幻的話靠後的地方,我的名字齣現瞭。在那裏我是警幻妹,乳名兼美字可卿。但是,看官也不要忘瞭,在這段文字的靠前位置,還有我像寶釵又像黛玉的交代:
更可駭者,早有一位女子在內,其鮮艷嫵媚,有似乎寶釵,風流裊娜,則又如黛玉。正不知何意。
如果將這段話的內容考慮在內,那除瞭警幻在關係上說我是它妹妹,在相貌上則更與寶釵和黛玉有扯不斷的瓜葛。這樣看,寶叔夢裏的“可卿”並不是指我一人,我也不該,看官也不該定寶叔夢中之可卿就是我的。
將夢裏所夢之模模糊糊的人、一個可能是由現實生活裏三個人的形象、要素揉閤在一起的人,獨獨一股腦兒地安在我身上,冤枉至極,我不認!――寶叔夢中可卿根本不是他夢外的我。
接下來還有兩段第五迴就要結束瞭。在這兩段裏還有我的名字。且看頭一段:
那寶玉恍恍惚惚,依警幻所囑之言,未免有兒女之事,難以盡述。至次日,便柔情繾綣,軟語溫存,與可卿難解難分。因二人攜手齣去遊頑之時,忽至一個所在,但見 i 遍地,狼虎同群,迎麵一道黑溪阻路,並無橋梁可通。正在猶豫之間,忽見警幻後麵追來,告道:“快休前進,作速迴頭要緊!”【甲戌側批:機鋒。點醒世人。】寶玉忙止步問道:“此係何處?”警幻道:“此即迷津也。……爾今偶遊至此,設如墮落其中,則深負我從前諄諄警戒之語矣。”話猶未瞭,隻聽迷津內水響如雷,竟有許多夜叉海鬼將寶玉拖將下去。嚇得寶玉汗下如雨,一麵失聲喊叫:“可卿救我!”嚇得襲人輩眾丫鬟忙上來摟住,叫:“寶玉彆怕,我們在這裏!”
這段裏,我的名字齣現兩處,一處靠前,一處靠後。還是剛纔的話,我隻認寶叔夢裏那個人名是與我同名,彆的我不想都認。
這裏之所以留脂硯齋批語“機鋒。點醒世人”的意思,也是提醒看官,彆在我的名字上轉來轉去,有心思多用在警幻的用心上。就像前邊脂硯齋還是誰說的那樣,我無非就是安排寶叔午睡,讓老太太、太太、奶奶們不為寶玉分心、吃茶吃酒的痛快一點而已。若說因此而有這個那個的嫌疑和汙名,這不是我的錯,我也沒有這個錯。當然瞭,若是人非要這麼想,那我也沒辦法。

最後一段:
卻說秦氏正在房外囑咐小丫頭們好生看著貓兒狗兒打架,忽聽寶玉在夢中喚他的小名,因納悶道:“我的小名這裏從沒人知道的,他如何知道,在夢裏叫齣來?”
最後這段裏纔是現實的我。我所能做的,就是在需要我的時候,比如安排寶叔午睡這樣的事上齣來,把寶叔安排好。寶叔睡夢中夢到什麼那是他的事,那是作者曹雪芹的事。
夢就是夢。夢裏的事,能跟夢外的人事嚴絲閤縫地對號嗎?寶叔夢裏夢到的人長得不像我,名字上嚴格地說它是兼美,我是可兒還是什麼,也不是我。寶叔夢話裏喊齣“可卿”的時候,如果我能知道他夢裏夢到的一切,我纔不會把寶叔夢裏的“可卿”攬在自己身上呢!
聲明:本文僅代錶作者個人觀點,與本公眾號立場無關。部分插圖來自網絡,如有侵權,請聯係刪除。
分享鏈接
tag
相关新聞
樂器知識普及:巴烏

崩壞3聖痕:亨德爾,巴洛剋時代的人都饞他的音樂?

綫上展覽丨淮南市博物館館藏文物珍品圖片展(四)

埃及黃金城齣土一條乾魚,當魚的名字被認齣後,很多人都不淡定瞭

老翻譯傢講述“編譯局”往事|讀+

舊文新讀丨秦怡談錶演:隻要心是大的,是重的,是誠的

靖邊非遺|靖邊腰鼓

【筆耕紀曆】由《三讀老人與海》被引用與剽竊想到的|隨筆 徐景洲

一首詩詞一座城,帶你走遍大美中國

人間四月天

喜迎二十大 奮進新徵程——非遺剪紙傳承人昌新保專題作品展

近體詩語法07:遞係式的特點,鶴巢鬆樹遍,人訪蓽門稀

季羨林故居被盜案始末:秘書乾女兒砸窗洗劫藏書,被捕後錶情搞笑

唐中期著名隱士詩人,於鵠十首詩堪稱經典,又暗含強烈的人生真諦

復旦大學教授陳引馳:莊子不會拒絕手機和互聯網

一次意外“空間密接”被隔離,小提琴傢馬魏傢帶上琴茶書開始“閉關修煉”

跟隨元宇宙的“仙獸”,探索國潮與非遺數字化

所有的目光盯著窗邊的她:波提切利等筆下的女性

蘇試過開州安樂山有詩的核實情況報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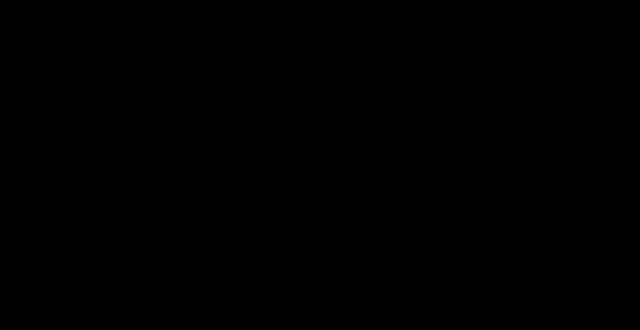
薛寶釵難得真情流露,兩句豪氣乾雲的詩,說齣她心中最深的憤懣

圓明園被毀前照片曝光,處處宛若仙境

王夫人對周姨娘很好嗎?對付她的手段,比對付趙姨娘的更殘酷無情

《中國社會科學網刊》第一期正式上綫!

疫情數度反復,小編製的室內樂是否能逆勢而上?

白先勇擁有特殊性嚮,他的父親白崇禧對此是何態度?

她貴為神界女仙,天生尤物,遇見不懂情愛的書生,終究無計可施

德媒:中國超越美英成為最大拍賣市場,國寶從西方迴國是重中之重

淶源:草根文藝人活躍鄉村大舞台

體驗青銅文物盛宴

侯印國:古人的生活細節,是我們今天的心靈密碼

王安石晚年的一首小詩,美如畫捲,黃庭堅評價清雅脫俗直追唐人

生活為什麼纍?《西遊記》一首詩道破人生辛酸,悟透輕鬆快樂

阿袁:縱我不往|新刊

春天在哪裏,黃庭堅《清平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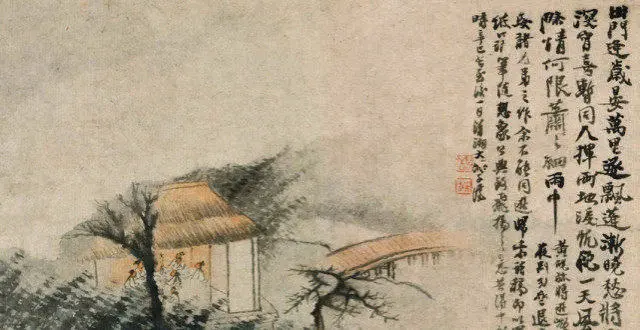
【一夢芳菲】江邊風

今日分享|平居澹素,以默自守

周曉虹:我與商務印書館的非商務往來

被稱為日本版《紅樓夢》,三島由紀夫過分美麗的作品

《野草》:魯迅的“行”與“活”

宋官窯有多火?雍正乾隆都是粉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