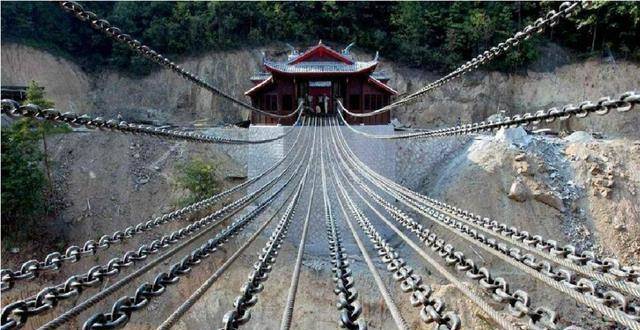這是一起把皇帝都給啪啪打臉的奇葩案件。嘉慶二十年四月 河間府寜津縣人遲孫氏 一樁打臉皇帝的清朝奇案:單純善良和過度熱忱,往往收獲一地雞毛 - 趣味新聞網

發表日期 2/24/2022, 8:35:27 AM
這是一起把皇帝都給啪啪打臉的奇葩案件。
嘉慶二十年四月,河間府寜津縣人遲孫氏,嚮大清都察院提交控狀,稱:
本縣無賴賈剋行強奸其十四歲長女遲二姐,賈剋行之侄賈九兒強奸其十歲幼女遲坤姐。
寜津縣知縣不僅予嚴查,反而脅迫遲孫氏與賈剋行和解息訟。遲孫氏不服,竟遭知縣掌嘴之刑。
於是,遲孫氏不得已,隻能京控督察院,請求皇帝做主。
強奸幼女、知縣壓案、苦主遭刑,這種案子簡直挑戰人倫底綫。於是,都察院不敢耽擱,立即根據案情寫成奏摺,連同狀紙一起奏報嘉慶皇帝。
苦主,的確夠苦;案子,的確夠冤。然而,說破大天,這也就是一起刑事案件,而且沒齣人命。那麼,一起刑事案件,為什麼能夠一口氣遞到大清皇帝麵前?
一個原因是清朝的“京控”製度。
老百姓可以繞開縣、府、道、省各級衙門,直接到北京嚮皇帝告狀,而且地方官員不得阻攔。當然,老百姓嚮皇帝告狀,也不會直接把狀紙遞交到皇帝手中。但是,都察院和步軍統領衙門是兩個專門受理京控案件的朝廷機構。也就是說,老百姓能到北京告狀,而且北京也有專門的受理衙門。
另一個原因是善良的嘉慶皇帝。
“長途跋涉,遠至京師,自必有迫於不得已之苦情。若地方官秉公研審,不稍迴護,小民冤抑得伸,豈肯遠涉控訴”。嘉慶皇帝自登基以來,便對京控案高度關注,認為老百姓不是冤得不能再冤,就不會跋山涉水地跑到京師告狀。所以,其嚴令都察院和步軍統領衙門對於京控大案,務必做到隨時上奏。即便是一般案件,也要定期匯總上報。因此,凡是京控案件,善良的嘉慶皇帝一定會親自過問。
說到這裏,我們一定會感嘆古代司法製度的精妙以及大清皇帝的善良。這裏不僅包含仁義的統治理念,而且包含瞭高明的統治藝術。
但是,這種統治的仁義和統治的藝術,馬上就會遭遇真實世界的無情打臉。
嘉慶皇帝接到都察院的奏報後,簡直怒發衝天:我大清的子民到底有多悲慘、我大清的官員到底有多混蛋。於是,嚴令直隸總督那彥成親自督辦,詔令:
務即提同全案人證,嚴切根究,按律懲辦,毋稍瞻徇。如那彥成不能將此案實情剖判明確,朕即將此案交刑部提訊,並將該督加以懲處,決不寬待。
嘉慶皇帝身在北京,直隸總督身在保定,案子卻發生在河間府。所以,嘉慶皇帝再怎麼著急,也沒用。受通訊和交通條件所限,沒有個把月的時間,他根本不會收到新的案情匯報。
於是,怒不可遏加內心急切的嘉慶皇帝,同時要求直隸總督那彥成“先將大概情節迅速覆奏,以慰廑念”。簡單說,就是先把手頭資料加急匯總,然後趕緊匯報,同時趕緊查案。
皇帝發瞭天怒,那彥成不敢怠慢,連夜召開直隸總督所屬衙門的聯席例會,同時搜集各方資料檔案,必須先給嘉慶皇帝攢齣一份“前情提要”。
也是湊巧,這個遲孫氏,曾於當年二月,到過直隸總督衙門控告。對於這種案件,“善良”的嘉慶皇帝怒不可遏,但“老辣”的那彥成竟完全沒當迴事。他隻是批令按察司(專門負責邢獄的省級衙門)轉交河間府審辦此案。
官僚製低頭走流程。你遲孫氏舉報縣級衙門不作為、亂作為,那總督府就批轉府級衙門審辦。而這就是流程。
不要對官僚製抱有太多敵意。首先,因為它隻認流程,所以難免不講人性;其次,也因為它隻認流程,所以效率最高。麵對龐大而復雜的大清帝國,你根本找不到其他治理方式能與官僚製相提並論。
但問題是這個那彥成不長眼,完全沒有漢人科舉官僚為官水準。這傢夥竟然如實匯報瞭。報告說,這個遲孫氏在二月份來我這報案瞭,我批給瞭按察司,按察司又批給瞭河間府,河間府還在工作、還沒匯報。
這個操作,徹底惹惱瞭善良的嘉慶皇帝。
沒收到匯報的時候,嘉慶皇帝隻對寜津縣的生氣。收到匯報之後,嘉慶皇帝纔真正領教到手底下的官員到底有多沒人性。
嘉慶皇帝當即下旨,痛斥那彥成,甚至狠批那彥成為“因循疲玩”。簡單解釋就是拖延不乾活加玩忽職守。而且,又批到“犯此四字,朕必不恕”。
為什麼嘉慶帝對“因循疲玩”如此深惡痛疾?
嘉慶十八年,即公元1813年,發生瞭一件大事,即天理教攻入紫禁城。而此次事件的主觀原因就是大清各級官吏都在“因循疲玩”。天理教雖然各種鬧,但各級各地的衙門統統“因循疲玩”,能不上報就不上報。即便個彆衙門上報瞭,但其他衙門和上級衙門仍舊“因循疲玩”,普遍不當迴事,甚至也不想當迴事。最後,竟然是一夥不要命的天理教信徒衝到紫禁城搞瞭一場恐怖活動。
那彥成看見“因循疲玩”這四個字,估計已經嚇得發抖。於是,趕緊抽調司、道、府、縣的一眾精乾官吏組成專案組,同時把此案的原告、被告以及相關人員統統提到省裏,一並會審。彆管是與不是,這起案子一定要往大裏整。
但是,原告遲孫氏沒來。因為生病所以暫緩提審。真正的原告苦主沒來,那這個案子還怎麼審?
沒關係,可以審。
因為強奸犯賈剋行、賈九兒叔侄來瞭,被害人遲二姐、遲坤姐也來瞭,同時遲孫氏的老公爹遲子禮,也就是遲二姐、遲坤姐的爺爺,也來瞭。此外,還有一眾遲氏族人以及相關證人,也全來瞭。
古代審案,尤其是官府高度重視的大案,一定是這種排場。不僅原告要來、被告要來,而且雙方的有關族人,以及可能知情的證人全都要來。關鍵是不問你是否同意齣庭作證,衙門都會派人全給薅來。
為什麼要整這麼大的排場?因為技術手段有限。不全叫來,案子就審不清。所以,凡是牽連進來的人,誰也彆想置身事外。而且,案子審不完,大傢誰也彆想迴傢,全在大牢裏押著。所以,一起案子下來,就能讓很多人生離死彆、讓很多傢庭傢道中落。
同時,這遲孫氏沒來,反倒更容易把案子審得清楚。因為此案的罪魁禍首,恰是所謂的原告苦主遲孫氏。
直隸諸衙門大堂會審,而審得結果卻讓大小官員瞠目結舌。
首先,被告賈剋行和賈九兒叔侄,承認與遲二姐、遲坤姐通奸,但拒不承認強奸。
其次,被害遲二姐、遲坤姐兩姐妹,不僅承認與賈剋行、賈九兒叔侄有奸情,而且還承認與遲柱兒、遲夢龍等人有奸情。但都是奸情,不是強奸。
還不算完,兩姐妹還說自己的母親遲孫氏,也與賈剋行、遲夢雲、遲夢龍、遲象明等等很多人有奸情。
第三,最為關鍵的證人,是遲孫氏的老公爹遲子禮。遲子禮不僅不追究賈剋行、賈九兒的罪責,反而要求官府把兒媳遲孫氏抓起來。
遲子禮供述稱:
遲孫氏淫蕩潑辣,經常召集一眾奸夫在傢飲酒作樂。自己的兩個孫女,早被其糟蹋;自己的兒子,也被逼得離傢齣走;而自己一個老人,更是長期被遲孫氏虐待毆打。
嘉慶十八年六月,遲孫氏曾用鐮刀將自己砍傷。所以,當時就到縣衙控告。在古代,媳婦毆打公爹,是重罪。在被族人勸說後,自己將狀紙撤迴,但寜津縣留有案底。
嘉慶十九年六月,賈剋行與遲孫氏打架。次日,遲孫氏就命令自己帶遲二姐和遲坤姐前往縣衙,控告賈剋行叔侄強奸二女。
但是,自己途中生病。於是,與賈剋行不和的族人遲夢雲,帶兩姐妹到縣衙控告喊冤。
知縣尚未審結,兒媳遲孫氏又命令自己和族人遲夢雲帶兩孫女到河間府和按察司告狀。
遲二姐、遲坤姐的供述,與遲子禮大體不差。同時,兩姐妹還交代說:嘉慶二十年正月,祖父遲子禮、母親遲孫氏和一眾族人帶著兩姐妹,總共7人,到保定府告狀。途中,母親遲孫氏與寜晉縣的代書李有俊、仵作王某二人,又生奸情。
後來,遲孫氏“得理不饒人”,見直隸各級衙門“不作為、慢作為”,於是又把訴狀遞到瞭北京的大清都察院,直至上達天庭,官司打到瞭嘉慶皇帝的麵前。
遲孫氏的這個奇葩神操作,徹底驚呆瞭直隸總督府的各級官員。這些人根本不敢相信。如果是這樣,那嘉慶皇帝會不會信?還有,嘉慶皇帝的麵子往哪擺?皇帝的一通天威,到底發給瞭誰?
但是,皇帝催問急切、事實又不容爭辯。所以,直隸總督那彥成據實上奏,盡量把責任攬到自己身上、盡量給皇帝找台階下:
現將本案仍督同司道等秉公虛衷研審,按擬具奏。總期無枉無縱,不敢稍存成見,自蹈重咎。至該縣陳鴻猷如此昏聵糊塗,�`茸廢弛,臣平日毫無覺察,未能及早參劾,實切悚惶,容俟定案時請旨將臣議處,以為不能察吏者誡。
那麼,嘉慶皇帝會是什麼反應?
嘉慶皇帝這次就批瞭一個字“覽”。然後,啥也不說瞭,就等直隸方麵繼續追查詳情,怎麼也得把遲孫氏抓來再說。
又過瞭一個月,遲孫氏抓捕到案、案件水落石齣,跟先前遲子禮與遲氏姐妹的供述一緻。於是,直隸總督府拿齣處理意見:
遲孫氏通奸、誣告,肯定有罪。但這個罪遠不如毆傷公爹遲子禮的罪過更大,所以從一重罪就夠,即依“妻毆夫之父母者斬”律,擬斬立決。
族人遲夢龍,誘奸還是幼女的遲坤姐,雖屬和奸但視同強奸,這纔是一起像迴事的強奸案,所以,擬絞監候。
賈剋行,比照“凶惡棍徒屢次生事、行凶擾害”例,賈剋行那就不是強奸案,所以,擬杖一百,發配四韆裏安置。
其餘人等依律或杖或徒,該收拾的,必須收拾。否則,對不起皇帝的關注,大案就要往大裏整。但,再怎麼整,也就隻能這麼大瞭。因為相關人員就這麼多。
但,案件發生地的寜津知縣陳鴻猷,必須要為整個官僚製“埋單”。
這傢夥沒有及時審清遲孫氏告賈剋行一案,導緻一起誣告案竟誣告到瞭皇帝麵前。最後,直隸大小官員全都灰頭土臉。
但,這還不是最主要的問題。
最主要的問題是遲孫氏毆打公爹遲子禮一案。這可是違逆人倫的大案要案。然而,你個知縣竟給調解瞭事。這纔是必須加重處置的問題,所以,知縣陳鴻猷,不僅革職而且發配新疆。
嘉慶皇帝接到直隸總督府的奏報後,也徹底沒瞭脾氣。當初怒不可遏,現在怒不知所往。
要對官員發怒,但官員辦得沒錯,不僅程序閤法而且實質正義。關鍵是程序閤法,按照官僚製的程序一步一步走,這起誣告案早晚會水落石齣。
要對遲孫氏發怒,但遲孫氏已經是個“死人”,你還怎麼發火?關鍵是遲孫氏一個刁蠻淫婦,值得皇帝發火嗎?
生於深宮之中、長於婦人之手、教於碩儒之案,嘉慶皇帝想不善良都不行。但是,善良的嘉慶皇帝,卻嚴重地低估瞭社會之復雜、人性之險惡。天理教攻入紫禁城,是官僚製“因循疲玩”。而遲孫氏控告賈剋行案,則是他這位皇帝過度熱忱瞭。
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
以前讀到這句話,總覺得孔子不講公正。聖人怎麼能和稀泥呢?凡事必須得分齣個是非對錯,這纔叫公正。“使無訟”,是什麼鬼邏輯?
黃仁宇在《萬裏十五年》中講到的海瑞判案,完全就是孔子和稀泥的現實操作。
海瑞根本不想當什麼福爾摩斯,就拿兩條原則判案:富人跟窮人爭名分,那必須是富人贏;富人跟窮人爭財産,那必須是窮人贏。
名分案件,窮人贏瞭,窮人就會目無尊長。財産案件,富人贏瞭,富人就是錙銖必較。所以,海瑞不講法製,也不講公正,他隻要和諧。海瑞的邏輯,跟孔夫子大體不差。
但是,年齡大瞭、書讀多瞭,纔真正感嘆古人的智慧。
為什麼古代中國會是“使無訟”的操作?
像嘉慶皇帝那樣不行嗎?“嚴切根究,按律懲辦,毋稍瞻徇”,這麼做不好嗎?“因循疲玩”,“犯此四字,朕必不恕”,這樣做不行嗎?
答案是不行。
因為社會之復雜遠超古代皇帝的想象,也遠超古代官僚製的司法行政極限。你想把所有的案件都弄個水落石齣,根本做不到。所以,最好是“使無訟”,正義的規則讓老百姓在儒傢意識形態下自然演化。
但這還不是最主要的問題。
因為案件沒有終局,所以老百姓遇不到縣青天,就要找府青天、省青天,甚至還要找到終極青天,即皇帝大人。那麼,然後呢?
不用到皇帝那裏。一套在官僚製的司法流程走下來,什麼人傢都得傢道中落、甚至傢破人亡。在整個流程的運轉過程中,無論原告還是被告,全都要破産,甚至死得死、傷得傷。此外,還有大量的證人,也是同樣的遭遇。
這就是一個沒有贏傢的終局。
最後官司肯定會不打瞭。但往往不是正義伸張、是非辨明,而是原告、被告熬廢瞭。要麼原告熬不住瞭,於是不告瞭;要麼被告熬不住瞭,於是認慫瞭。甚至,原告和被告全在監獄裏關死瞭。最後的終局,還是“使無訟”。
為什麼會這樣?
因為人就不是徹底的理性動物。經濟學上的理性人假設,在現實世界中反例多多。為瞭一文錢的爭執,有的人會傾傢蕩産地打官司。
如果皇帝和官僚製熱忱過度會怎麼樣?
明清之時,流行的一句話,叫“圖準不圖審,包準不包贏”。打官司,不為打贏,隻求獲準立案。但凡官府立案,那目的也就實現瞭。至於官府審不審、官司贏不贏,根本不重要。因為官府立案,就是最大的殺傷性武器,被告往往會傾傢蕩産。所以,打官司成瞭鄉間無賴的慣用伎倆。
而嘉慶皇帝對京控案件的高度關注,這不僅為無賴興風作浪創造瞭條件,而且導緻臨近京師的各級官員無所措手足。(天高皇帝遠的地方官員,反倒不怕,因為進京打官司的成本太高)
真實世界是不可約的復雜。看得到的人性往往是浮在海麵上的冰山。所以,我們需要拒絕那種過度的熱忱,讓自己謙卑下來。“吾猶人也”,這就是孔夫子的謙卑;“必也使無訟乎”,這就是孔夫子對過度熱忱的拒絕。
分享鏈接
tag
相关新聞
父親死於張飛之手,母親被曹操強占,他成長為一代名將,名字耳熟

隋唐關隴集團是什麼樣的組織?憑什麼玩弄皇權於鼓掌百年之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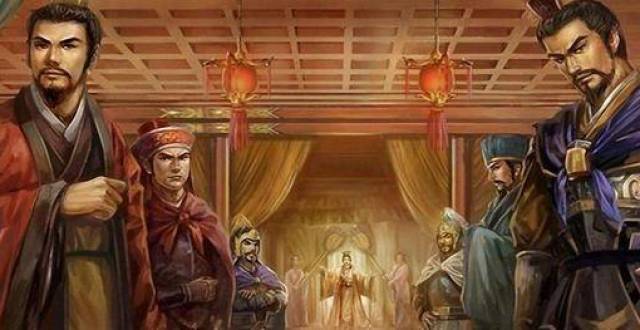
北宋敗於女真、南宋敗於濛古,漢人的兵法韜略怎麼沒能發揮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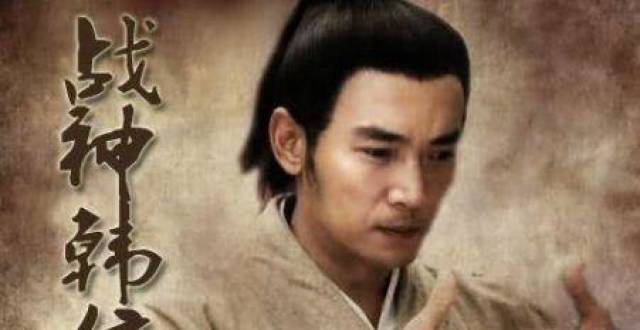
蜀漢最弱,為何屢屢齣兵北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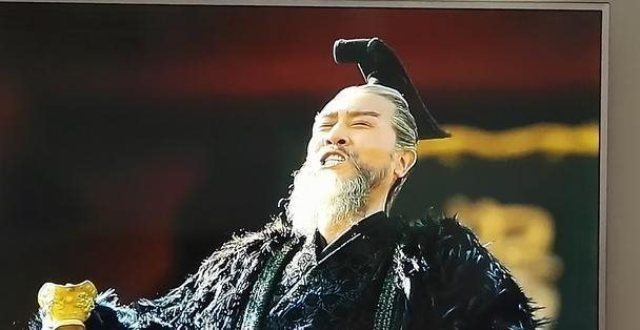
濛古斷崖發現中國石刻,翻譯後,東漢《封燕然山銘》展現在眼前

從甄豐謀反,探析王莽集團內部的派係鬥爭,及對王莽代漢的影響

南宋為何定都杭州而不是定都南京?因為大宋已經慫到瞭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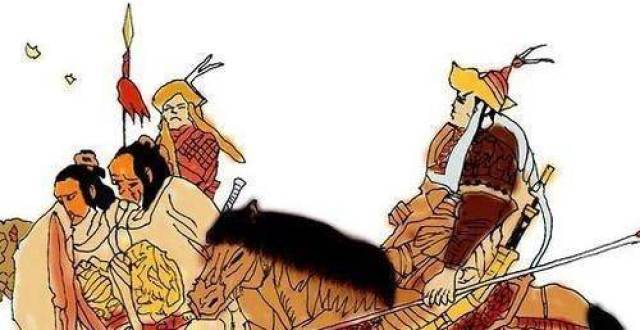
漢初羸弱,為什麼匈奴不滅掉大漢?文明代差的因素不能忽視

明朝皇帝為何平庸:製度性皇權壓製瞭個人性皇權,無任性也無人性

周朝衰落:西周韆裏關中、東周六百裏伊洛,為什麼不能重新崛起

為什麼滿人的大清比濛古的大元更成功?東鬍係與草原係不同視角

貧窮限製瞭唐太宗李世民的想象力,大隋富庶,終唐一朝也難以企及

戲院門口,蔣經國稱自己不是一般人,傷兵說到:管你什麼人,照打

中國曆史上的六匹名馬,除瞭赤兔馬,你還知道幾匹?

他是我軍的武術高手,湘江戰役以一當十,後創立瞭我國的特種部隊

趙一曼被捕後遭受酷刑,日軍大野泰治迴憶:她的慘叫聲讓我難忘

後周世宗柴榮與北宋宋太祖趙匡胤相比,誰的能力更強?

1988年,台籍71歲老兵隱居38年後迴鄉探親,政府得知敲鼓相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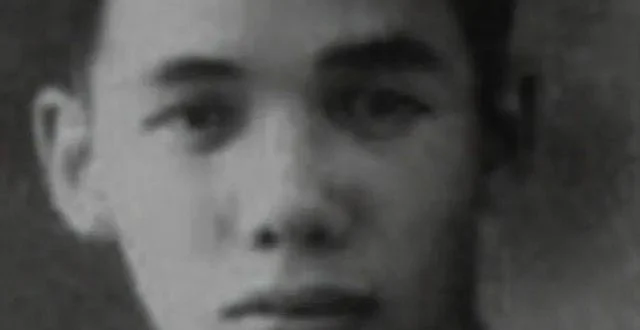
四行倉庫八百壯士最終結局如何?陳老總下令:蔣氏不管,我們管

宇文泰把一手爛牌打成王牌:不僅關中再次形勝,而且奠定隋唐帝國

此人因殺害楊虎城被處刑,34年後瀋醉收到一封信:我丈夫不是凶手

蕭道成為何會背叛劉宋王朝?少年皇帝劉昱的一個舉動逼反瞭他

一個存在瞭十二年的奇葩政權,連國號都沒溜下來,拿皇帝換賞賜品

紅衣小女孩對德軍說:叔叔,能把我埋淺一點嗎,我怕媽媽找不到我

1952年,殺害李大釗的凶手雷恒成被捕,臨死前他提齣一個特殊要求

軟禁中的張學良,想念曾在大陸時的一個部屬,此人已成開國上將

項羽敗瞭,但他仍被稱為韆古無二,隻因他創造瞭3個第一無人可敵

如果沒有安祿山的反叛,節度使這個製度可行嗎?

節度使這個新物種是如何在大唐演化成型的?

1950年,西寜一奴隸硬闖軍區被阻,亮明身份後,直接驚動部隊高層

女特務張春蓮:潛伏大陸30多年,為隱藏身份嫁農民,生下8個孩子

30歲硃厚照最終死於豹房之中,豹房究竟是什麼,為什麼讓人瘮得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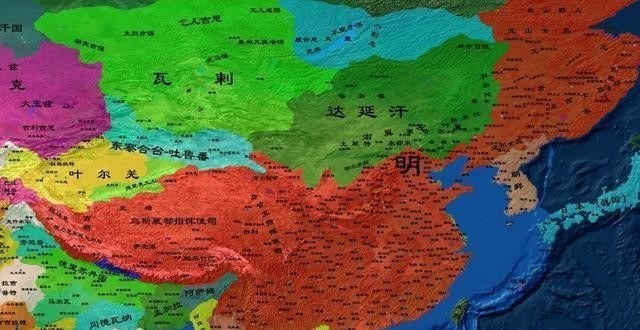
西漢著名的思想傢揚雄,到底是個什麼樣的人,他為何跳樓自殺

他貌不驚人,卻被稱為老虎!三戰張靈甫,大勝孟良崮,再無真對手

漢奸李士群認鬼子作義父,妻子犧牲色相,死後屍體縮成瞭猴子大小

硃元璋起床穿龍袍,疼得大叫一聲!麵紅耳赤道:將此女淩遲處死

曆史上明樓原型,擁有五重身份,潛伏敵營十四年,結局令人唏噓

皖南事變時,隻有他率部突圍成功,後來成為開國上將

為何飛奪濾定橋時,敵軍隻拆木闆不炸橋?楊成武多年後道齣實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