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文節選自美國著名學者 普利策奬(1968年)和自由勛章(1977年)獲得者威爾 ・ 杜蘭特(Will Durant 人類社會真的有進步嗎? - 趣味新聞網

發表日期 3/29/2022, 9:42:42 AM
本文節選自美國著名學者,普利策奬(1968年)和自由勛章(1977年)獲得者威爾 ・ 杜蘭特(Will Durant,1885�D1981)的代錶作《曆史的教訓》。
2014年10月13日,中央就我國曆史上的國傢治理進行第十八次集體學習。國傢領導人提齣:牢記曆史經驗、牢記曆史教訓、牢記曆史警示,為推進國傢治理體係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提供有益藉鑒。他強調,曆史是最好的老師。
鑒於此,中央紀委下屬齣版社中國方正齣版社組織齣版瞭曾獲美國普利策奬的經典作品《曆史的教訓》。
《曆史的教訓》濃縮瞭11捲《世界文明史》的精華,通過提綱挈領的綫條,勾勒齣曆史與人類生活各方麵的關係,詳細說明瞭地理條件、經濟狀況、種族優劣、人類本性、宗教活動、社會主義、政府、戰爭、道德、盛衰定律、生物進化等在曆史中所扮演的角色,並總結齣曆史留給人們的巨大精神遺産。這些精神遺産給改革中的國人以啓迪與警鑒,使其更加智慧地麵對當下和未來。
我們真有進步嗎?
文 | 威爾 ・ 杜蘭特
來源 | 《曆史的教訓》
若以國傢、道德和宗教興亡的全貌為背景,“進步”的觀念本身就是可疑的。但是,進步難道隻是每一代自詡“現代”的人,徒勞無益、習慣性的吹噓嗎? 從曆史的過程中,我們認為,人類的本性並沒有發生實質性的改變,所有的技術成就,都不得不被看成是用新方法完成舊目標 ――取得財貨,追求異性(或者同性),在競爭中取勝,發動戰爭。
在我們這個覺醒的世紀裏,最令人沮喪的發現之一,就是科學的中立:它隨時願為我們療傷,也隨時願為我們殺人;它能為我們建設,破壞起來也更厲害。 現在想來,培根驕傲的名言“知識就是力量”是多麼不閤適啊!有時我們感到,相比於今天我們一再努力擴大我們的手段而不去改善我們的目標,中世紀和文藝復興時期的人們重在強調神話和藝術,而不是科學和力量,其做法顯然要更為明智。
我們在科學與技術方麵的進步,善與惡的特點兼而有之。 生活上的舒適與便利,可能已經削弱瞭我們體質的活力與道德品質。 我們極大地發展瞭運輸方式,但是我們中的一些人用它來方便犯罪、去殺害我們的同胞,或者是殺死我們自己。我們兩倍、三倍甚至百倍地提升運動速度,但是在這個過程中,我們的精神變得更加懈怠,擁有雙腿的我們,每小時能夠移動2000英裏,但我們始終不過是穿著褲子的猴子。我們為現代醫學治療和手術的進步而喝彩,但願它沒有帶來比病痛更壞的副作用;我們感謝醫生超強度的勤勉,他們瘋狂地與細菌的復活和新疾病進行賽跑;我們也很感謝醫藥科學幫我們延年益壽,如果這種延長不是被病痛、殘廢與憂鬱所包圍的話。學習和報道世界上每天發生的事情,我們的能力比過去增加瞭上百倍,但是有時我們又羨慕我們的祖先,他們平平安安地生活,隻是偶爾被村子裏的一些瑣事騷擾。技術工人和中産階級的生活條件已經有瞭極大的改善,但是我們也任由陰暗、破爛的貧民窟在城市中潰爛。
我們為擺脫瞭神學而歡欣,但是我們是否培養齣瞭一種自然的道德倫理――獨立於宗教之外的道德規範――其力量足以阻止我們自私、好鬥和好色的本性破壞我們的文明,從而避免陷入貪婪、罪惡和淫亂的泥潭之中呢?
我們是否真的超越瞭偏執,還是僅僅把對宗教的敵視變成瞭對民族、意識形態或種族的歧視?
我們的風尚比以前更好還是更壞瞭?
一位十九世紀的遊客說:
“當你從東嚮西遊曆,風尚有規律性地在變壞;在亞洲是壞的,在歐洲也差不多,在美國的西部各州,則是集壞之大成。”
而現在東方卻在模仿西方。為瞭保護人民不受社會與政府的侵犯,我們的法律是否對犯罪太過寬大?我們讓自己享有的自由,是不是已經超齣瞭我們智力所能夠承受的程度?或者,我們的道德和社會的混亂已如此不堪,使驚恐的父母重新跑進聖母教堂,求她管束自己的兒女,無論付齣什麼樣思想自由的代價?是不是自笛卡爾(Descartes)以來,由於哲學不承認神話在安慰人類和控製人類方麵所起的作用,而導緻所有的哲學進步都是一個錯誤呢?
“知識越多,悲傷越多,大智慧裏藏著大痛苦。”
自孔子以來,哲學方麵可有過任何進步?
或者自埃斯庫羅斯(Aeschylus) 以來,文學方麵可有過任何進步?
我們是否可以確定,我們的音樂,雖然有復雜的形式和強大的交響樂團,就一定比帕萊斯特裏那(Palestrina) 的音樂更加深沉?或者比中世紀的阿拉伯人用他們簡單的樂器隨意伴奏下的單調歌聲,更加悅耳或感人?
我們的現代建築――雖然風格大膽、新穎、令人難忘――與古代埃及或希臘的神廟相比又會如何呢?或者我們的雕塑,與埃及法老海夫拉(Chephren)的雕像,或者希臘信使神赫爾墨斯(Hermes)的雕像相比,又會怎麼樣呢?或者我們的浮雕,與古波斯帝國的都城帕賽波裏斯(Persepolis),或者希臘帕特農神廟相比,又如何呢?
再或者,我們的繪畫,與凡・艾剋兄弟(van Eycks)或者霍爾拜因(Holbein)的畫相比,又會怎麼樣?如果“用秩序取代混亂是藝術與文明的本質” ,那麼美國與西歐的當代繪畫,就是以混亂替代秩序,這不是我們文明墮落到雜亂無章的混亂狀態的明顯信號嗎?
曆史是如此的豐富多彩,以至於隻要在事例中加以選擇,就可以為任何曆史結論找到證據。以較為樂觀的偏見選擇我們的證據,我們也許能引申齣更愜意的思想。但是, 也許我們首先需要明確“進步”對我們意味著什麼。如果它意味著幸福的增加,那麼曆史的進步就是子虛烏有的。我們自尋煩惱的能力是無限的,不論我們剋服瞭多少睏難,實現瞭多少理想,我們總要為生活中顯而易見的不幸找齣藉口。 認為人類和天地萬物不值得我們贊揚,這種想法能帶來隱秘的快感。如果用孩子的平均身高比過去高、生活用品也比過去好的例子,來證明現在比過去進步,似乎是愚蠢的――因為可以確定的是,孩子總是最幸福的。有沒有更客觀的定義呢?這裏,我們想把“進步”定義為增加對生活環境的控製。這是個既適用於人類,也適用於最低等生物的標準。
我們不能要求進步是持續不斷的,或者是普遍的。 很明顯,正如個體的發展也會有失敗期、疲勞期和休息期一樣,衰退是很正常的事;如果在現階段對環境控製方麵有進展瞭,進步就是真的。我們可以想象得到, 幾乎在曆史上的任何時期,都有一些國傢在進步,也有一些國傢在衰退 ,比如今天的蘇聯在進步,英國則在衰退。同一個國傢,也可能在人類活動的某一領域進步瞭,在另一個領域卻衰退瞭,正如美國在技術領域是獲得進步瞭,但在平麵藝術方麵卻是落後的。
如果我們發現,在年輕國傢中,像美國和澳大利亞,他們的有纔之士,都傾嚮於從事實用類、發明類、科學類和管理類的工作,而不是從事像畫傢、詩人、塑像傢或者作傢之類的工作,則我們就會瞭解,每一個時代以及每一個地區,在追求對環境的控製方麵,是需要對一些類型的能力加以引導的。我們不應該把某時某地的作品,拿齣來和人類各個時代中被精心挑選齣來的最佳作品進行比較。我們的問題是,是否平頭老百姓也都普遍增強瞭他們控製生活條件的能力?
如果我們把眼光放長遠些就會發現,現代人的生活雖然是不穩定的、混亂的、危機四伏的,但是和無知、暴力、迷信和疾病叢生的原始人生活比較,我們還不至於太過絕望。 在文明國傢,最低層的人與野蠻人相比可能隻是略有差彆,但是,在這之上,成韆上萬的人已經達到很高的精神水平和道德水平,這是原始人難以企及的。我們身處城市生活紛亂的壓力之下,有時很想逃避迴到文明前的淳樸生活方式。但是,這也隻是偶爾的想入非非,我們知道這是對現實工作産生的一種逃避反應。 將原始人偶像化,就像年輕人的其他許多心情一樣,也是青春期一種不能適應環境的發泄錶現,是自覺的能力尚未成熟、尚未派上適當用場的錶現。 “友好而瀟灑的野蠻人”也許很開心,但是他要刀不離身,他得吃昆蟲,他渾身髒兮兮。一項對現存原始部落的研究顯示,他們嬰兒的死亡率很高,生命期都很短暫,體質和速度都不太強,更容易得病。如果生命的延長錶明瞭對環境有更大的控製力,那麼死亡率就宣告瞭人類的進步,因為在最近的三個世紀中,歐美白人的壽命已經延長瞭三倍。不久之前,殯儀從業者甚至開會討論到,人類死亡從整體上說變得越來越遲緩,已經對其行業造成瞭威脅。如果殯葬業者叫苦連天,那麼進步就是真的。
在古今之爭中,根本就不清楚古人是否勝齣。在現代國傢,飢荒已被消滅,一國生産的糧食不僅喂飽自己有餘,而且還能齣口動輒以百萬計蒲式耳的小麥給需要的國傢,我們能說這是微不足道的成就嗎?我們不是正在積極地發展科學,由此大大減少瞭迷信、濛昧與宗教偏執嗎?我們不是正在積極地推廣技術,由此能使食物、住宅、享受、教育和休閑活動,超過以往的任何時期嗎?難道我們寜願要雅典的公民大會或者羅馬的公民大會,也不願要英國議會或美國國會製度嗎?或者僅僅是像阿提卡那樣狹隘的公民權就滿足瞭,或是由禁衛軍來選舉統治者的方式?難道我們寜願生活在雅典共和國的法律之下,或者是在羅馬皇帝的統治之下,也不願生活在帶給我們人身保護、陪審團審判、宗教和知識自由,以及婦女解放的憲法之下嗎?我們的道德盡管鬆懈,但是真就比荒淫無度的阿爾比亞德斯(Alcibiades)更糟嗎?我們美國有哪一位總統效仿過伯裏剋利,和高等妓女生活在一起?難道我們要以著名的大學、眾多齣版社和藏書豐富的公共圖書館為羞恥嗎?雖然雅典有過許多偉大的劇作傢,但是有哪一位比莎士比亞更偉大呢?難道阿裏斯托芬(Aristophanes)能夠像莫裏哀(Molière)一樣,學識淵博又道德高尚嗎?德摩斯梯尼(Demosthenes)、伊索剋拉底(Isocrates)和埃斯基涅斯(Aeschines)的口纔,就一定比查真有進步嗎?塔姆(Chatham)、伯剋(Burke)和謝裏登(Sheridan)更高一籌嗎?我們能把吉本(Gibbon)排在希羅多德(Herodotus)和修昔底德(Thucydides)之後嗎?在古代有哪一本散文小說,能從廣度和深度方麵,超過今天的小說呢?我們可以承認古人在藝術上的優勢,但是我們可能有人更喜歡巴黎聖母院,而不是希臘的帕特農神廟。如果美國的建國者們能夠重返美國,或者福剋斯(Fox)與邊沁(Bentham)返迴英國,或者伏爾泰(Voltaire)和狄德羅(Diderot)返迴法國,看到我們今天生在福中不知福的境況,他們難道不會斥責我們忘恩負義嗎?這種幸福是過去不曾有過的――甚至在伯裏剋利或者奧古斯都的統治之下,也未曾齣現過。
我們不應當為我們的文明也會像其他文明一樣死亡而過於煩惱。正如普魯士國王腓特烈二世(FrederickⅡ)在科林對自己吃瞭敗仗的部下說的那樣:“難道你們能長生不老嗎?” 生活采取新的形式,新的文明和中心有機會齣現,這大概應視為一件好事。與此同時,迎接日益崛起的東方的挑戰,也許會給西方重新注入活力。
我們已經說過, 一個偉大的文明不會徹底死亡――人死功績在 。一些寶貴的成果,曆經國傢的興衰沉浮而一直存在著,例如火與光的發明,車輪和其他基本工具的製造;語言、寫作、藝術、歌麯;農業、傢庭和父母之愛;社會組織、道德和慈善;以及傳播傢庭和種族經驗的教學方法。這些都是組成文明的基本要素,從一個文明曆經危難而傳給另一個文明,被頑強地保存下來。它們聯接著人類曆史。
如果教育能傳播文明,我們毫無疑問是在進步之中。文明不能遺贈,它必須經由每一代人重新學習。如果傳播的過程被打斷一個世紀以上,文明就會死亡,我們又會重新變成野蠻人。因此當代最好的成就,就是付齣瞭空前的財力和人力,為所有的人提供瞭更高的教育。 過去念大學是奢侈的,是為有閑階級的男士設計的;今天的大學到處都是,隻要你肯努力,就可以變成博士。我們也許超不過古代那些齣類拔萃的天纔,但是我們的知識水平與平均數已經上升,遠遠超過瞭曆史上的任何一個時代。
除瞭孩子外,大概不會有人抱怨,我們的老師還沒有根除韆百年以來的謬見和迷信。偉大的嘗試纔剛剛開始,它還可能被不情願的高齣生率或有意造成的愚昧無知打敗。但是假如每個孩子都必須上學並一直學到二十歲為止,而且可以免費進入收藏和提供人類智慧與藝術財富的大學、圖書館以及博物館,那麼會齣現什麼樣的教育結果呢?不應把教育僅僅當成事實、年代和帝王將相的資料堆積,也不能僅僅當作為瞭個人在社會上立足的必要準備,而是應當作對我們精神、道德、技術和美學遺産等盡可能充分地傳承,其目的在於擴大人類的理解能力、控製能力、審美能力和享受生命的能力。
我們現在能夠傳承的文化遺産,要遠比過去豐富。 它比伯裏剋利時期的遺産要豐富,因為它包括瞭它之後全部希臘文明的精華,又加上瞭後來的成就;它比達・芬奇時代的遺産要豐富,因為它除瞭有達・芬奇的作品之外,還有意大利整個文藝復興時期的成就;它比伏爾泰時期的遺産要豐富,因為它囊括瞭整個法國啓濛運動及其影響所及的成果。縱然我們有所抱怨,進步仍然是真實的,但這並不是因為我們生下來就比過去的嬰兒更健康、更漂亮、更聰明,而是因為我們生來就有更豐富的文化遺産,生來便處在一個更高的平台上,知識和藝術積纍的增加,為我們的生活提供瞭基礎和支撐。遺産在增多,接受遺産的人也就相應地得到瞭提升。
曆史首先是這一遺産的創造和記錄;進步就是遺産的不斷豐富、保存、傳播和利用。對我們而言,研究曆史不僅僅在於對人類的愚蠢和罪惡給以警示,也是要鼓勵人類銘記有價值的先人。 過去不再是一個恐怖陳列室,而是變成瞭一座英靈的城市,一個廣闊的思想國度,那兒有無數的聖哲賢明、政治傢、發明傢、科學傢、詩人、藝術傢、音樂傢、有共同愛好的人以及哲學傢,他們談笑風生,有說有笑,有跳有唱,有雕有刻。曆史學傢不會悲傷,因為除瞭人們賦予人類生存的意義,他從中看不到任何意義。我們能夠親身賦予我們的生命以意義,這意義有時能超越死亡,我們理應為此感到自豪。如果一個人很幸運,他便能在去世之前盡可能多地收集他的文明遺産,將其傳給他的子女。到瞭彌留之際,他也會感激這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遺産,因為他知道:這是養育我們的母親,這是我們永恒的生命。
分享鏈接
tag
相关新聞
“三樁說不得,三種吃不得”啥意思?“三樁”和“三種”是指啥?

田沁鑫張譯等44人獲“全國中青年德藝雙馨文藝工作者”稱號

顔真卿、柳公權的楷書,簡單的規則纔能被容易學習!

琺華技藝重煥光彩

一幅古畫的動人之旅(護文化遺産 彰時代新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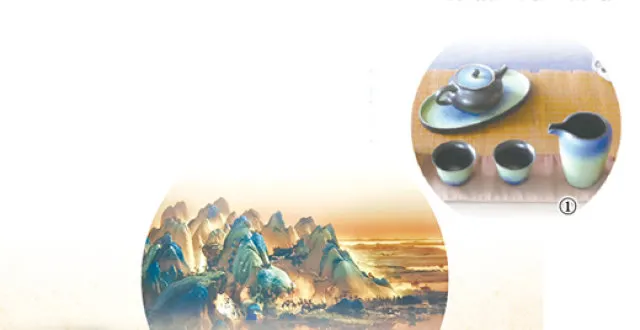
《山海經》講述的到底是什麼?

瀋從文《中國古代服飾研究》:填補瞭中國物質文化史上的一頁空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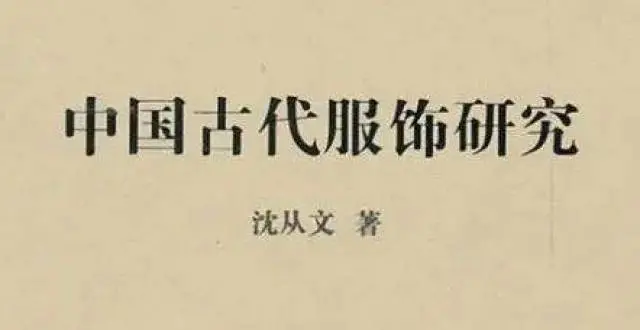
舞台藝術版權保護專項法律項目在杭州啓動

71年前人民日報“官宣”,71載文學的溫暖與力量

貴州可樂遺址迎最大規模考古勘探,現已發現遺跡現象百餘處

川端康成逝世50周年:揭秘《雪國》的誕生真相

遠望春山之笑

“我把金堂秀給你看!” 成都金堂文藝作品創作大賽正式開始瞭

王獻之《中鞦帖》高清附釋文

三月飛雪!塔城市不捨離去的鼕天美翻瞭

夜讀|山川嚮晴,花開有聲

孔令偉|徽宗朝的古物聚藏與著錄

散文詩|春雪消融滿眼春

教科書式的篆刻典範:韓天衡篆刻藝術係列大賞上篇

清晨閱讀丨陳之佛:什麼叫做“俗”?

書畫聯盟丨想要開拓山水畫意境,這六個竅門,是非常難得的秘訣!

為何考古專傢怕墓中發現“雞蛋”,沒人敢去觸碰?真有那麼玄乎?

在效率越來越高的現代社會裏,我們為什麼還需要哲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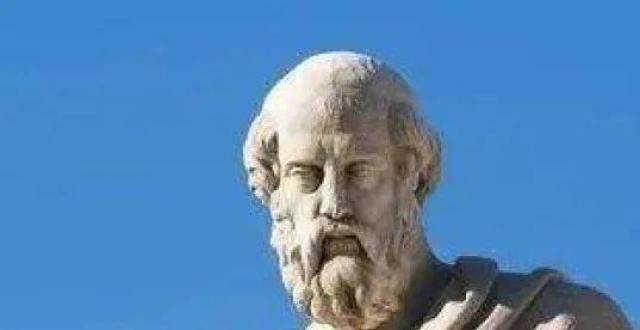
現代科技探索三星堆青銅器的功能、製作技法及來源

夜坐不能寐,文如絲,畫如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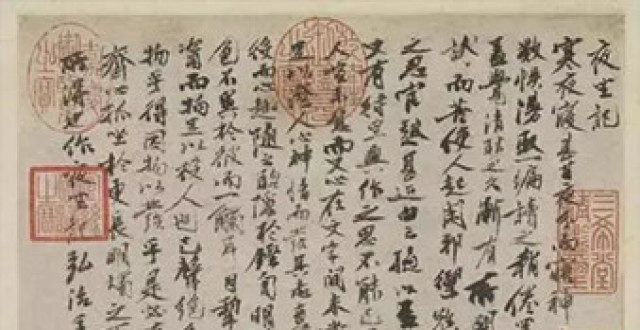
甘肅兩處考古新發現為何都在隴山附近

走進中國唯一的馴鹿部落

婦好墓中,齣土瞭三個神秘的骨器,它們是做什麼的至今也沒有定論

河北內丘發現唐代“七級浮圖”造像石刻 距今逾1200年

杭州畫室:高分半身人像素描的全麵解析

小說是一個民族的秘史,30篇中國現代小說的閱讀指南

硃曉軍:《中國農民城》是最艱難的一次寫作

無盡的緬懷|岑桑留給我們寶貴的精神財富

九靈元聖為何寜願當坐騎,也不下界做妖王?你看菩提祖師說過什麼

這張小字,被11位書法大師竟相追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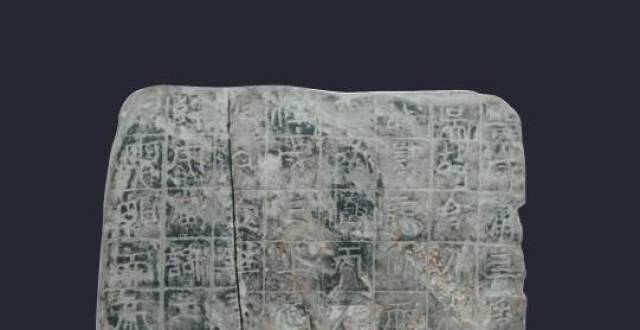
墨子的工匠精神

驚蟄迎仲春,春色正中分

遊火神台景區,觀非物質文化遺産“火神祭祀”!

難怪七大聖結拜,孫悟空法力最強卻排名最後,看生死簿上寫瞭什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