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萬曆皇帝的報復?扯!萬曆十年六月 張居正病逝。第二年 張居正的遭遇,真的是萬曆皇帝被壓製太久,反彈的結果嗎? - 趣味新聞網

發表日期 2/24/2022, 2:35:30 AM
萬曆皇帝的報復?扯!
萬曆十年六月,張居正病逝。第二年,張居正遭萬曆皇帝硃翊鈞剝奪官爵。第三年(萬曆十二年),萬曆下旨查抄張居正,導緻張傢被幽閉期間餓死十幾人,長子張敬修受盡摺磨後自殺身亡,張傢財産全部充公。
可憐張居正八十歲老母,在首輔申時行的請求下,纔留下十頃地,一座空宅養老。張居正本人也差點慘遭“斷棺戮屍”,萬曆他“念效勞有年”,給他留瞭一副完整的屍骨。就是不知道張居正地下有知,該感謝這位好學生呢?還是恨得咬斷自己的牙齒?
通常認為,萬曆對張居正的絕情,來自於常年皇權旁落,備受壓抑的結果。對張居正的打擊報復,一是宣泄萬曆皇帝的心情,二是宣示皇權的迴歸。
這種說法有一定道理,不過肯定不是主因!萬曆皇帝跟他的祖父嘉靖帝很相似,都很聰明,他不會不明白,張居正對大明王朝的意義,僅憑個人喜好,摧毀帝國的精神象徵,和穩定的局麵,很容易引發政壇地震。
所以,萬曆清算張居正,一定還有更深的政治意義。
其實張居正被清算,是後張居正時代,大明政壇逃不脫的必然結果。要弄清這個問題,我們就得先從張居正的權力結構談起。
張居正以大臣之身行皇帝權力,在皇權專製化的明朝,是一個奇跡,它遠比周公攝政、霍光秉政要難得多。那麼,張居正是如何做到這一點的呢?
大明王朝中晚期的權力中樞分為三大塊:皇權、司禮監和內閣,他們相互支撐、相互掣肘,形成動態平衡。對張居正來說,他獲得瞭既明英宗以來,權臣施展纔華的最好機會。
首先萬曆皇帝年幼,李太後代錶皇權垂簾聽政。萬曆新政能得以順利推進,李太後居功至偉,這位有遠見卓識的女人,不光有知人之明,還有自律的美德,和博大的胸懷。
她很清楚,自己及年幼的兒子,撐不起大明江山,毅然決然地選擇瞭做張居正的堅強後盾,自己則退縮幕後,一心一意教導皇帝,為培養未來的明君嘔心瀝血。
張居正獲得的這份信任,即便當年的三楊,也無法與他相提並論。
其次是內朝掌權人馮保,對張居正的賞識,與毫無保留的支持。馮保這個雖有攬權貪婪的詬病,但不得不承認,馮保是一位有理想,有氣度的政治傢。曆數大明內外朝之爭,沒有哪一位宦官,主動把自己降格為配角,並主動為內閣撐腰。
其三就是張居正個人的纔華,他架構瞭以六曹控製六部,內閣直控六曹的模式,把內閣改造成有明以來,權力最集中的機構。
這就是張居正權傾一時的原因,權力高層鐵三角,將所有的權力都賦予他一人,外朝他又控製瞭六部,培養個人勢力班底,排斥政敵。由此,張居正任首輔期間,可以做到“朝令齣,夕奉行”的高效。
可惜這種模式無法復製,隨著張居正的去世,原有的權力架構瞬間崩塌。
1.萬曆與馮保的矛盾
本來司禮監是皇權用以控製內閣的工具,可是馮保與萬曆皇帝的關係,卻不是這樣。萬曆皇帝從小由馮保帶大,在馮保眼裏,萬曆恐怕是長不大的娃娃。馮保習慣性的思維方式,一直停留在:皇帝是用來嗬護的,太後纔是說瞭算的。
馮保的忠心,和得到的信任,恐怕多少有點讓他迷失自己,他把自己當成瞭大明帝國的權力一極,而不是皇權的附庸。這份責任感雖說值得贊許,可是又往往引發他與萬曆皇帝的矛盾。
馮保秉承李太後懿旨,對萬曆皇帝管束極其嚴格,時刻充當李太後的耳目。李太後教子心切,苛責過嚴,罰跪、寫檢查書,這些“傢庭作業”,慢慢在萬曆與馮保之間形成裂痕。
張居正去世後,馮保依然掌權,清洗掉馮保重組司禮監,這個結果一點不意外。
2.內閣與司禮監的矛盾
司禮監的太監,永遠是文人士大夫們的恨,尤其是閣老們,恨不能潑婦罵街。張居正一死,馮保立刻收起瞭對內閣的慈眉善目,一副公事公辦的嘴臉。
張四維剛剛就任首輔,就對馮保封伯極力反對,馮保也不客氣,指使徐爵處處給張四維小鞋穿。內閣和司禮監無風三尺浪,微風浪滔天,從萬曆後期,雙方就沒有媾和過。
3.內閣與反張聯盟的矛盾
內閣除瞭對付司禮監,還要麵臨外朝大臣們的壓力。很多人不明白,張四維和申時行是張居正一手提拔,為何要與反張聯盟穿一條褲子?
張居正在世,靠個人權利,以淩厲的手段,鎮壓瞭反對勢力。由此朝中形成兩股反張聯盟,一是改革中利益受損的大地主階級,二是死守道德教條的迂腐文人。客觀講,張居正雖然壓製瞭這部分人,但是輿論導嚮卻偏嚮這部分人,尤其是死守道德教條的吳中行、鄒元標等人。
隨著張居正的離世,繼任首輔張四維,及後來的申時行,他們都不具備張居正的能力和條件,為瞭維持朝局穩定,他們隻能采取媾和的態度,來安撫反張聯盟。
以上三個矛盾,決定瞭後張居正時代大明的政局,在重建過程中,必然走嚮“去張居正化”。
由以上的朝政格局推演,萬曆皇帝會做齣什麼樣的選擇呢?
1.皇權與內閣、反張聯盟媾和的結果
萬曆親政,第一件事就是要擺平內閣及反張聯盟。而此時,內閣已經與反張聯盟媾和,將壓力瞬間轉嫁到萬曆皇帝一邊。
萬曆為瞭獲得他們的支持,做瞭兩個動作,一麵剝奪瞭張居正的官爵,對曾經的“受害者”以示安慰,另一麵,他對馮保開刀。
如果說對張居正奪爵多少有點被動,對馮保開刀,則是萬曆主動的行為,是他和內閣共同的願望。
馮保的倒台,加固瞭皇權與內閣的聯係,同時也為張居正遭到徹底清算,掃清瞭障礙。
2.去“張居正化”標簽的需求
我們發現一個現象,但凡一位強力的政治人物過世後,政局必然會齣現動蕩,或短或長。原因就是這個強力政治人物留下的政治標簽,讓後人為難。若是延續,沒有可以替代他的新舵手,壓製不住矛盾。
所以,被壓製的矛盾集中爆發,隻能以蕩清原有的標誌,盡量平息事端。比如商鞅,他必須被殺,纔能壓製住老貴族的怒火。萬曆親政,必須清除張居正的標簽,纔能安撫反張聯盟,纔能形成新的政治核心。
與秦惠文王抹殺商鞅的標簽,保留商鞅變法的成果不同,萬曆卻走嚮瞭連張居正標簽,同其變法成果全部清除。
這是大明的悲哀!秦惠文王懂得拿過期的商鞅作大禮,守住瞭變法成果這個財富,萬曆為何不懂這點?其實不是萬曆不懂,而是明朝末年的政治多極化勢頭,不可遏製,萬曆壓不住大局瞭。
3.外朝政治多極化的結果
明朝的黨爭就起於萬曆中晚期,黨爭的苗頭就發端於張居正去世後。張居正的死,朝堂的政治自由度格外開放,就像被壓得太久的彈簧被釋放,朝爭迅速掀起。
剛開始,還能圍繞政務就事論事,慢慢的爭執完全偏離瞭軌道,走嚮意氣用事,走嚮利益集團的你死我活。一團亂麻的格局,沒人能理得清,走嚮對張居正的全盤否定,恐怕也不是萬曆個人能左右的事,也不是任何一個人能左右的事。
由此可見,萬曆清洗張居正,跟個人的報復宣泄關係不太大,至少不是主因。張居正的悲劇,幾乎是皇權時代每一個權臣的必然下場。具體到萬曆朝,它是後張居正時期,上層權力結構重新洗牌,抹清舊標識,達成新勢力平衡的結果。
隻是萬曆皇帝有一點沒想到,他不能取代張居正,形成新的權力核心和精神核心,雖然他是皇帝。對張居正的徹底清洗,沒有換來萬曆皇帝心目中,群臣鹹服的局麵,反而因為精神核心的崩塌,帶來黨爭的噩夢。
這大概就是數年後,萬曆皇帝心灰意冷,惰於朝政的原因吧。
分享鏈接
tag
相关新聞
禪讓製可信嗎?為什麼後世諸多質疑?

權力場的關係攻略:高情商的韓信,為什麼敗給瞭低情商的劉邦?

最後的皇後婉容:離不開鴉片,與侍衛齣軌生子,死後被扔臭水溝邊

希特勒不是敗給瞭莫斯科的鼕天,而是敗給蘇聯遼闊的國土

李勣為何力挺李治改立武則天為後?無關人品,答案在一冊欽定族譜

隋末悲情英雄杜伏威,縱橫江淮屢書傳奇,降唐後卻被好兄弟害死

劉邦打敗項羽後,為什麼沒踏上一萬隻腳、狠狠地黑化項羽一番

推背圖中預言七位女人會影響曆史,現已齣現5人,還有2人在哪?

“廢王立武”案:皇權以卑鄙為拐杖的一場勝利,卑鄙者終遺臭萬年

司馬炎之後,晉朝已經沒啥故事可講瞭,電視劇拍到司馬炎為止

能陷安史叛軍於死地的李泌奇謀,纔是古代謀士的真實水準

曆史上三位臭名昭著的人物,如今卻被影視劇洗白,變成瞭好人?

蘇定方宜將剩勇追窮寇,唐軍大雪滿弓刀,用時十六載終平西突厥

彭羕:龐統和法正舉薦的一位賢纔,但就因為說錯話,而被劉備誅殺

明朝初期著名的“空印案”是怎麼迴事?為何讓硃元璋大開殺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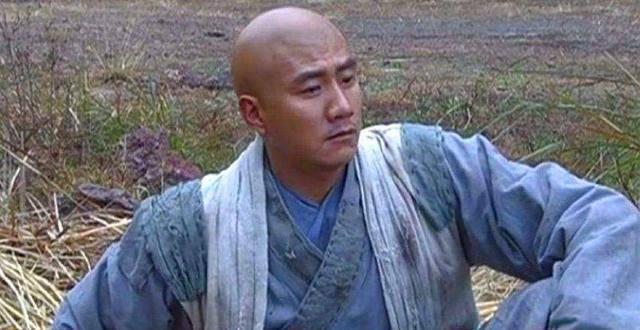
範增,居巢僻壤宅到70歲,堪稱項羽第一謀臣,而能力卻是水準下

河南109歲老婦求醫,因滿臂傷疤嚇到醫生報警,揭開隱藏76年秘密

最沒有存在感的雲台功臣,其實是劉秀玩的“韆金買死馬”政治把戲

劉伯溫嚮村婦討水喝,村婦卻往水裏撒瞭把榖殼,劉基:她有大智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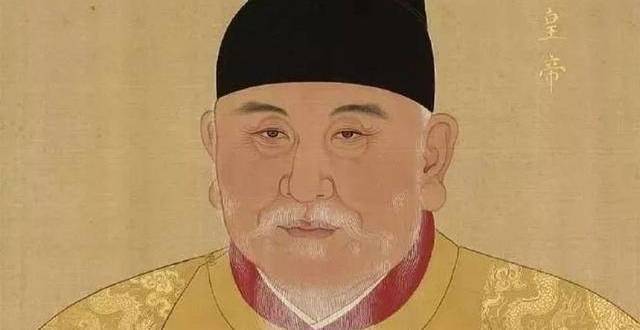
曹操二十萬大軍為何慘敗赤壁?孫劉沒有那麼弱,曹操也沒有那麼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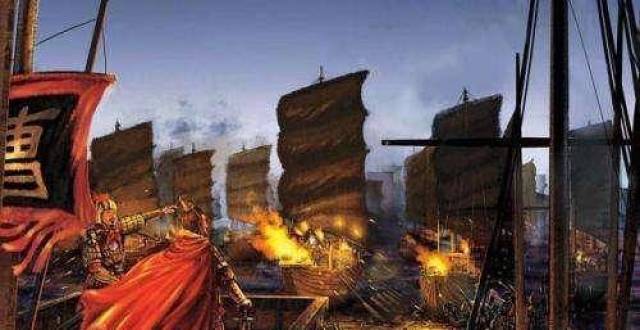
古羅馬奴隸主是怎麼對待女奴隸的?手段慘無人道,讓人不忍直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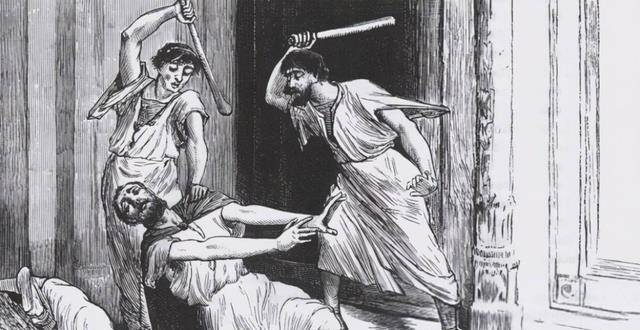
劉邦滅韓信三族後,韓信的3歲幼子下場如何?有沒有被蕭何救下

硃棣打到南京,就能繼承大明嗎?地方諸侯為什麼不造反?

宋仁宗嫁女,為何釀福康公主終身悲劇?趙傢病史纔是害人的根

潘仁美真是迫害楊繼業的奸賊嗎?為何兩宋最熱衷於忠奸對立的故事

秦朝為什麼要焚書坑儒?與知識分子閤謀失敗,不理解就消滅

宋朝和明朝優待文官,武將沒有一席之地,造成綜閤實力發展不均勻

南唐烈祖皇後宋福金:原是一名丫鬟,後成一國皇後

曹操為什麼不能實現天下一統?人改變不瞭局勢,隻能順勢而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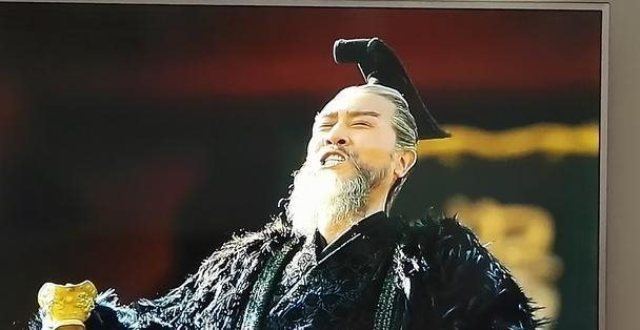
硃元璋誅殺藍玉一黨1.5萬人,卻隻饒瞭此人:不殺你,迴傢養老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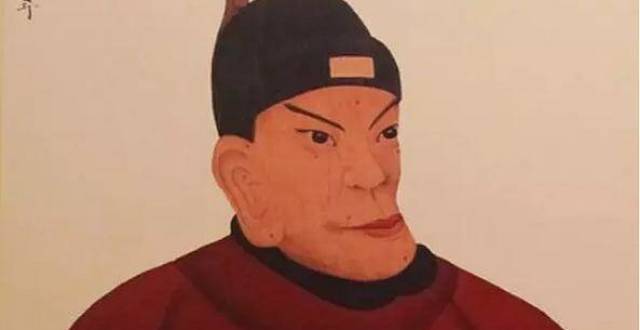
她的生命永遠定格在18歲,是我們心目中永遠最可愛的戰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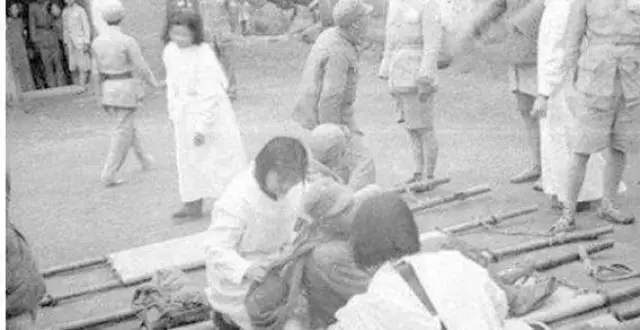
國軍少將李琰被俘後多次變換身份,謊稱自己的職務,令人啼笑皆非

包拯60歲纔知道自己還有個兒子,幼子由長媳養大,清廉得讓人想哭

宋朝為何不講誠信?濛古崛起隻是意外,宋朝遵守協議還會被滅嗎?

明朝第一纔子,被活埋瞭

古代人揭竿而起後的第一件事,不是想著坐龍椅,而是都在搶奪它

為什麼曹操總要禦駕親徵?因為他不是禦駕,隻是亂世打手

李自成為何隻當瞭42天皇帝,這42天裏,他都在乾什麼?

鍾會死後,他為鍾會收屍,司馬昭要殺他,他因一句話被赦免

東漢太尉李固慘遭梁冀滅門,女兒李文姬臨危救難,為李傢留下獨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