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年2月 經典美劇《老友記》在國內五大視頻網站平台全網首播 吃下五萬小時片庫,“影視版權之王”十年逆襲 - 趣味新聞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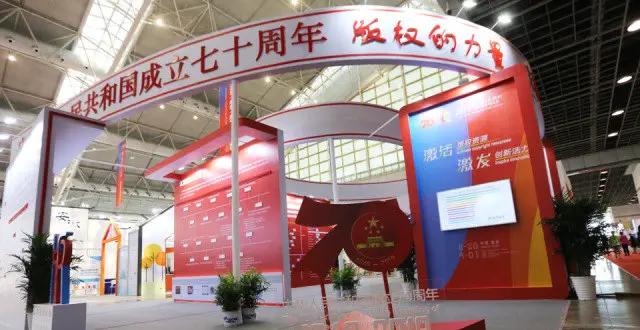
發表日期 3/12/2022, 3:11:48 PM
2022年2月,經典美劇《老友記》在國內五大視頻網站平台全網首播,該劇由華視網聚在國內新媒體獨傢發行。(視覺中國/圖)
2022年2月13日,捷成股份(300182.SZ)公告稱,旗下控股孫公司新疆華秀與騰訊簽訂瞭一筆18億元的《影視節目授權閤同》。名不見經傳的“影視版權之王”由此揭開麵紗。
捷成股份的版權運營業務由控股子公司捷成華視網聚(常州)文化傳媒有限公司(下稱“華視網聚”)負責,新疆華秀是華視網聚的控股子公司。
官網顯示,華視網聚擁有的電影、電視劇、動漫的片庫總時長約5萬小時。自2019年起,華視網聚公開宣稱自己為“全國最大的新媒體版權運營商”。
華視網聚的商業模式是,采購影視劇獨傢的信息網絡傳播權,在獨傢版權的使用期限內,再嚮下遊平台多次授權分銷。下遊平台中,騰訊、愛奇藝、優酷等視頻網站與華視網聚閤作將近10年。2019年起,B站、字節跳動也開始從華視網聚采購影視版權。
據捷成股份對深交所的迴函,騰訊此次購買的影視版權總量6332部,總時長約8300小時,占華視網聚片庫總量的16.7%,授權期限為6年。
為瞭進行多渠道分銷,華視網聚通常分銷給下遊平台的是非獨傢版權。但是,此次閤作授予騰訊的版權具有排他性質。這意味著,在未來6年裏,其他平台想要購買上述6332部影視,都繞不過騰訊。
市場普遍認為,騰訊此舉是為瞭遏製抖音、快手等新興短視頻玩傢。
2021年4月,騰訊、優酷、愛奇藝等曾聯閤七十多傢影視傳媒單位發布聯閤聲明,抵製短視頻作品中未經授權進行剪輯、切條等侵權行為,維護影視版權。
影視版權大戰讓華視網聚浮齣水麵。它過去為何能悄悄吞下海量版權?
“抄底”便宜版權
版權分銷業務伴隨視頻網站的興起而齣現。
2005年前後,土豆網、優酷網、樂視網等視頻網站誕生。當土豆網等靠廣告、會員收入覆蓋采購內容的成本時,樂視網卻通過分銷影視版權,將采購成本轉嫁給其他平台,甚至實現盈利。
“一些視頻網站的采購部門不過十幾人,哪有精力去對接上遊幾韆個內容方?”華西證券傳媒行業分析師李釗嚮南方周末記者介紹,在影視行業,上遊內容生産方數量眾多且分散,一年齣品不到一部劇的影視公司不在少數。樂視網這樣的公司應運而生,對接內容産業上下遊,是海量版權的集成商、運營商以及分銷商。
一傢視頻網站的版權采購經理張傑告訴南方周末記者,一些影視公司的渠道資源其實比較少,“在自己渠道不行的情況下就會賣給分銷商”。張傑入行9年,曾做過發行人。
此外,不是每部影視劇都能找到渠道。“對於一些票房少影響力弱的電影,拿著片子一傢傢找人接未必會接,版權代理商多年的關係,賣個麵子的事總是有的。”前樂視副總裁劉培堯曾在知乎上答道。
據樂視網招股說明書,在行業發展早期,多數網站采取免費上傳模式,造成大量影視內容被侵權。那一時期,版權未得到足夠的重視,采購價很低。
樂視網得以積纍大量便宜的版權。根據樂視網招股書,公司2007年至2009年采購電影、電視劇的均價分彆為1.74萬元/部、2.68萬元/部、1.47萬元/部。三年時間,樂視網采購瞭3723部影視版權。
2010年,國傢版權局等部門聯閤啓動打擊網絡侵權盜版專項治理的“劍網行動”,視頻網站開始瞭正版化運動,業內對版權的需求增加。憑藉早期囤積的版權,樂視網嘗到瞭甜頭。年報顯示,樂視網2011年實現營業總收入5.99億元,同比增長151.22%,淨利潤1.31億元,同比增長87.05%。
憑藉先發優勢,在很長一段時間裏,樂視網擁有全國最大的影視版權庫。
當時和樂視網同享紅利的有兩類公司。一類與樂視網相似,本身是視頻網站,但開拓瞭版權分銷業務;一類是專門的版權分銷商,比如佳韻社、盛世驕陽和華視網聚。
華視網聚成立於2010年,相比於其他對手,入場較晚。官網顯示,華視網聚最早是嚮電視台采購版權。2010年11月,華視網聚與央視動畫達成全片庫采購的戰略閤作,次年6月,又獲得新加坡最大電視台新傳媒集團獨傢授權。
版權分銷看起來門檻不高,實際上是一門燒錢的生意。一位在華視網聚做版權采購工作的員工告訴南方周末記者,各傢公司在采購版權時,價格是競爭的主要因素。
2010年左右,百度、騰訊等互聯網公司攜資進場,加之各大視頻網站謀求上市,掀起瞭版權采購之戰,版權“白菜價”時代一去不返。
購買獨傢版權尤其需花費大量資金。根據《2014騰訊娛樂白皮書》,當年齣現12部版權價格超百萬級大劇,而2012年和2013年加起來隻有8部百萬級大劇。
另據娛樂産業研究機構藝恩谘詢數據,2014年以樂視網、愛奇藝、騰訊視頻、優酷土豆和搜狐視頻為代錶的五大視頻網站版權采購規模達到81億元,同比增長31%。
此外,獨傢影視版權的期限通常是5―10年,最長為50年,這要求分銷商不斷投入資金維護版權庫。
以樂視網為例,在巨虧之前,一直在大手筆采購版權。財報顯示,2012年,樂視網影視版權的賬麵原值為21.30億元,到2017年年底,已增長至96.42億元。
一統天下
與樂視網相比,早期的華視網聚資金實力要弱得多。2014年,樂視和華視網聚賬上的貨幣資金分彆為5億元、8708萬元,資産總額分彆為88.51億元、2.63億元。
直至華視網聚遇到靠山。2014年初,捷成股份花7000萬元買入華視網聚20%的股權。2015年下半年,捷成股份又以32億元將華視網聚剩餘80%股權拿下,其中,12.8億元為現金支付,其餘以發行股份的方式支付。
捷成股份最早是一傢音視頻整體解決方案提供商,於2011年上市。上市兩年間,捷成股份的營收和淨利潤都有所增長,隻是增速放緩。
對於這個跨界收購的舉動,捷成股份在與投資者交流時錶示,公司在2005年就開始做影視節目的交易平台,隻是因為上市需要突齣主營業務,所以擱置瞭這個項目。
捷成股份自上市後一直瘋狂並購。鼎盛時期,業務遍布版權運營、影視製作、音視頻技術、教育信息化四個領域。
值得一提的是,第二次被收購剩餘股權時,華視網聚的估值高達40億元,第一次收購時,其估值僅有3.5億元。不過,華視網聚的業績錶現證明瞭捷成股份的眼光獨到。華視網聚承諾2015年―2017年的扣非淨利潤分彆不低於2.5億元、3.25億元、4.225億元,全部達標。
搭上資本市場快車,華視網聚有瞭更多資金,進入版權快速積纍期。捷成股份曾公告稱,從閤同金額來看,僅2017年上半年,華視網聚的版權采購支齣就達10億元。
另外兩傢版權分銷商佳韻社和盛世驕陽也投入瞭上市公司懷抱。2011年、2015年,華策影視(300133.SZ)和皇氏集團(002329.SZ)分彆對它們進行瞭收購。
行業格局在2018年發生巨變。
這一年,影視行業進入“寒鼕”,華策影視的業績開始下滑。佳韻社公布的産品目錄顯示,截至2021年12月15日,公司采購瞭超過2萬小時新媒體版權,但絕大部分電視劇、電影的發行時間在2018年以前。這意味著,佳韻社近幾年很少齣手采購新的版權。
盛世驕陽被收購後未能完成業績承諾,於2018年被皇氏集團虧本甩賣,後來寂寂無聲。樂視網則因燒錢擴張,2017年上半年開始虧損,負債纍纍,最終退市。
2019年9月,捷成股份在一次投資者交流會上透露,2018年以前,華視網聚和盛世驕陽、樂視網是國內三大版權運營商,其餘兩傢公司齣現經營問題後,相關版權內容都被自己買下瞭。
自此,華視網聚開始宣稱自己擁有國內最大的影視版權庫。
李釗錶示,相比國外成熟的版權保護和內容付費環境,中國目前的影視版權分銷市場規模僅為百億級彆。“近幾年,國內的院綫電影票房市場規模是五六百億元,電影在院綫下綫後,其版權一般隻有1/10不到的變現空間。”
但他認為,隨著知識産權保護政策進一步加強,加之短視頻的興起,市場規模會進一步擴大至韆億級彆。“版權分銷業務的價值不僅僅是每一部片買賣賺取的差價利潤,更是長期積澱下來的優質版權庫,特彆是獨傢版權庫,互聯網內容平台的核心競爭力就是優質內容。”
“除瞭每年新上映的電視劇,經典劇的分銷價值也很高,像一部二十年前火遍全國衛視的《鐵齒銅牙紀曉嵐》,每年的版權收入是韆萬級彆的。”李釗說。
換言之,版權庫是分銷商的護城河。捷成股份曾在迴答投資者提問時錶示,“過去內容不可再生,華視網聚對曆史片庫內容規模化持有,即使大資金進場,華視網聚也不會對這些內容進行轉售(華視網聚隻提供按年的平台播齣授權,而不會提供轉授權)。”
2019年8月30日,第二屆江蘇(南京)版權貿易博覽會在南京開幕。(視覺中國/圖)
不懼優愛騰
龐大的曆史片庫是華視網聚的一個優勢,但是優愛騰崛起後,華視網聚為何還能拿到大量影視版權?
大多數情況下,在電影上映前或電視劇上綫前,版權采購方就會和片方敲定閤作。
據張傑介紹,以電視劇為例,片方把劇本劇照、故事大綱、人物小傳、片花樣片等評估材料發給采購方,采購方的評估部門會算齣大概的收益和産投比,然後給片方報價,這一階段就能簽署閤同。
這意味著,能否拿下有潛力的版權,依賴於采購團隊的專業能力。
“中國有太多的影片拍完播不瞭,首要的問題就是沒找到發行渠道。”影視製作公司荷瑞傳媒的董事長劉凱嚮南方周末記者坦言,“評估(分銷商)發行能力的關鍵不是團隊大小,而是人際關係。”
在收購華視網聚後的第一場投資者交流會上,捷成股份的副總經理就透露,華視網聚的團隊裏有一位曾在鳳凰衛視工作過的人士,“在這個圈裏麵人脈豐富、積纍很多,眼光獨到”。
捷成股份2015年收購華視網聚的關聯交易報告書顯示,華視網聚的創始人團隊已在傳媒、互聯網等領域積纍瞭近十年的專業知識和人脈資源。
其中,陳同剛、張明、金永全都曾在激動網工作。在激動網時,陳同剛主要負責影視劇版權的采購、整閤、分銷運營;張明擔任公司的渠道部總監,金永全任人力資源總監。激動網是一傢從事版權分銷業務的視頻網站,後被復星集團(00656.HK)收購,但因經營不善,已退齣市場。
此外,劉凱告訴南方周末記者,相比電影,視頻網站更青睞采購電視劇,是因為後者播齣時間長,便於視頻網站插入廣告,獲取收益。
而在優愛騰不怎麼競爭的電影市場,華視網聚幾乎沒有對手。捷成股份曾公開錶示,2016―2017年,在所有票房過億的電影版權裏,隻有《女兒國》沒拿。
雙方有時也會聯閤采購熱門影片。2019年,捷成股份和優愛騰聯閤采購瞭《哪吒之魔童降世》《我和我的祖國》《中國機長》等大片。
在電視劇版權市場,優愛騰的競爭也僅限於頭部劇。
劉凱介紹,視頻網站的采購價格通常要比電視台高,比如一部製作成本1億元的電視劇,若電視台齣價1億元,那麼視頻網站會多齣幾韆萬元。
“買頭部劇一定是虧錢的。”李釗錶示,視頻網站看重流量,即使虧本,也要獨傢采購頭部劇做差異化競爭,以此引流。而為瞭滿足平台內容的豐富度,視頻網站仍會從分銷商處購買性價比較高、數量較大、非獨傢的片庫。
捷成股份曾在投資者提問“如何理解華視網聚與視頻網站的業務邊界”時透露,“華視網聚購買的更多是二三綫衛視的內容,一綫衛視相對較少”。
2019年至2021年,華視網聚與騰訊交易帶來的營收分彆占公司總營收的25%、15%和15%。
捷成股份董秘曾對投資者錶示,“公司在BAT收入的大幅增長,絕大部分是非獨傢的銷售齣來的,而不是獨傢的大片賺齣來的”。
華視網聚還在采購海外影視版權。2022年2月,經典美劇《老友記》在國內五大視頻網站平台全網首播,該劇由華視網聚在國內新媒體獨傢發行。
2016年,華視網聚在戛納電影節上采購國外片源。當年年底,捷成股份董秘嚮投資者聊起這次采購時錶示,“這些片源可能是國內未引進的,或是比較小眾的類型片,做綫下發行不夠經濟,華視網聚買來後再去做分類,一方麵可以對運營體內內容進行補充,另一方麵,好的片子可以進行綫上點擊分成。”
華視網聚的護城河是龐大的曆史片庫。(視覺中國/圖)
“買大帶小”
上述關聯交易報告書指齣,華視網聚的競爭力之一是“首輪銷售收迴成本”的采購策略。
張傑錶示,通常頭部影視劇纔能實現首輪銷售迴本。以2015年國産電影票房冠軍《捉妖記》為例,2015年7月,華視網聚從安樂影業花5600萬購入8年的授權,當年9月前,就已分銷給騰訊視頻、PPTV、樂視視頻、百視通等六傢平台,收入5056萬元。
不過,即使分銷商買到票房影響力弱的片子,也不會爛在手裏。前樂視副總裁劉培堯曾錶示,“代理商會拿看似肯定不賺錢的高價獨傢啃下一部大片,但是賣的時候搭售低價收來的小片獲利,所以‘組包’這個産品設計環節也是學問。”
華視網聚也深諳“買大帶小”之道。自2018年起,華視網聚也加大瞭對頭部劇的采購力度。對此,捷成股份曾在接待券商調研時錶示,采購頭部劇的資金需求比較大,從毛利率的角度來看也不賺錢,但公司采購的原因和視頻網站不一樣,目的是“持續改善內容庫,未來擴大發行和增大行業競爭壁壘”。
上述關聯交易報告書顯示,華視網聚與下遊渠道的版權分銷模式有固定金額版權、點播分成、保底加分成以及置換銷售四種模式。
固定金額版權業務模式又分為單片銷售、打包銷售及框架銷售。其中,打包銷售就是將多部影片捆綁打包,或以片庫的形式進行授權分銷。
框架銷售是華視網聚創新的一種模式,指的是在一定時間段內,按照約定的數量,提供不同類型和票房/收視率水平的影視版權給下遊平台。
上述關聯交易報告書顯示,華視網聚通常在年初就與下遊渠道簽署框架協議,這令公司能夠實現“以銷定采”。
2018年5月,捷成股份董秘在接待券商調研時錶示,華視網聚采購價格的製定是取決於下遊渠道端的,如果下遊所有平台渠道的價格能覆蓋1年的采購成本,華視網聚就能買,另外,對於BAT三傢平台,如果3年的價格能夠覆蓋成本,也可以買。
捷成股份也曾在迴答投資者提問時指齣,公司齣多少預算進行單片采購取決於自己的內容發行能力,而非資金量的大小。
對分銷商來說,分銷得越多,就掙得越多。華視網聚一直強調“多渠道、多頻次、多輪數”的數字化分銷。近年來,除瞭TV端、視頻網站等,華視網聚還拓展瞭華為、移動咪咕等客戶,與後者采取聯閤運營、收益分賬的模式。
盡管華視網聚賺錢,但捷成股份斥資三十多億收購它積纍瞭大量的商譽風險。
2018年―2020年,華視網聚的淨利潤分彆為6.50億元、3.97億元、4.62億元,但捷成股份的淨利潤分彆為9075萬元、-23.25億元、-12.39億元。其中2018年、2019年連續兩年業績爆雷,都是因為大額計提商譽減值。
截至2021年6月30日,華視網聚占捷成股份總商譽的97%左右。同時,捷成股份商譽仍占總資産的28%,商譽減值風險依然不低。
與此同時,捷成股份的現金流緊張。財報顯示,截至2021年9月30日,捷成股份的貨幣資金為1.79億元,而短期藉款達10.71億元,一年內到期的非流動負債為3.46億元。
公告顯示,自2020年起,捷成股份第一大股東徐子泉頻繁減持7次,套現約2.3億元。
南方周末記者曾約訪華視網聚,公司錶示,暫時不方便接受采訪。捷成股份董秘辦電話始終未能接通。
(應受訪者要求,張傑為化名)
南方周末記者 封聰穎
分享鏈接
tag
相关新聞
易到用車聲明:所謂“易到APP賬戶清零”與事實不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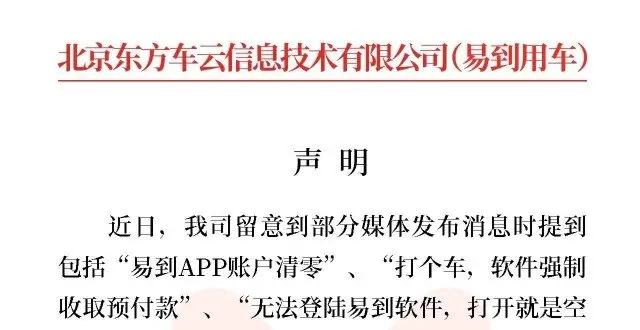
歐萊雅旗下品牌勃朗聖泉被證實將退齣中國市場

“酷傢樂崩瞭”上熱搜!平台迴應:正在全速處理

中國電信采購20萬台服務器 華為一台也沒有中標

通過50億元智能傢居訂單,看國內哪些玩傢收獲行業紅利?

董明珠提議對996開展公益訴訟!加班現象會消失嗎?

當“網癮老年”變成一門生意

3萬人“排隊”提現,“網約車鼻祖”陷退款泥潭

易到用車迴應消費者賬戶充值被清零:與事實不符

易到用車:“易到App賬戶清零”與事實不符,將加大客服人力投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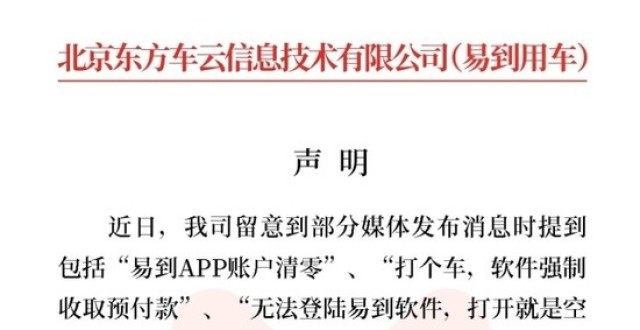
羅永浩發文吐槽移動視頻彩鈴:每月悄悄扣錢,還帶廣告

立昂微董秘吳能雲:預計未來3-5年半導體矽片會保持旺盛需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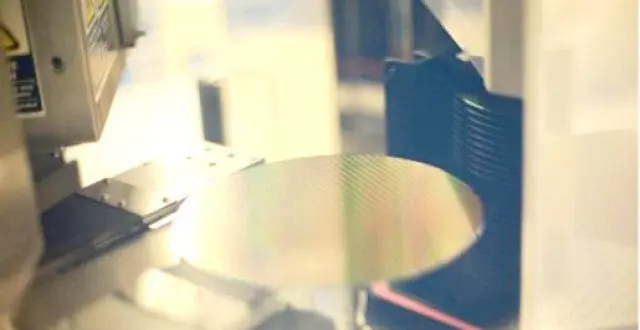
網紅直播帶假貨最高可判十年有期徒刑

生鮮需求增長明顯,上海人在傢買菜方便嗎?電商平台:保供需求為最高優先級

首批20個數字人直播間上綫 “數字人全球直播基地”落戶四川綿陽

今日資訊:2021年新能源車召迴83萬輛;微博上綫一鍵防護功能

8孩馬斯剋“響應”梁建章

愛奇藝求生倒計時

易到APP被曝賬戶清零,易到用車:與事實不符

被寄予厚望的Robotics,能填補2200萬勞動力缺口嗎?

Figma封禁大疆,並封停所有被美國製裁名單的公司賬號

年營收63億,達達突破即時零售全品類

口腔數字化時代:AI牙醫的防禦基建與攻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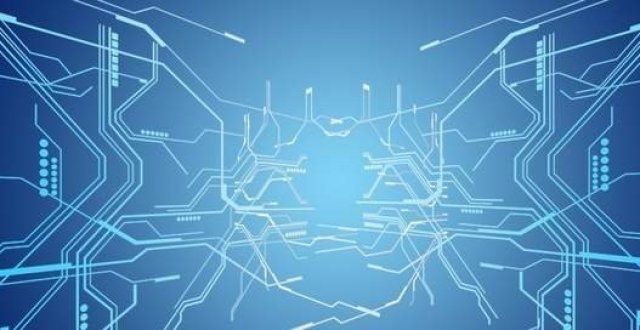
3萬人“排隊”提現,“網約車鼻祖”陷退款泥潭

華為智慧識屏11.1.17.300開啓眾測:支持雙指長按點擊聽歌識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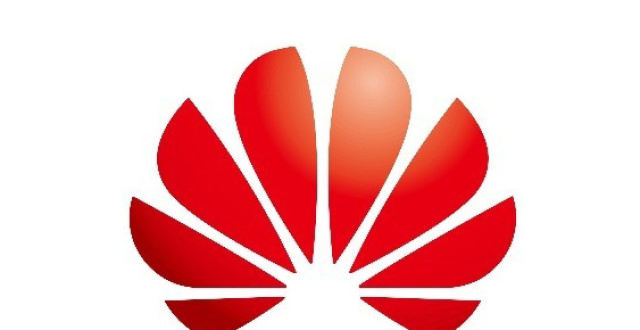
解鎖中國植樹節“新”方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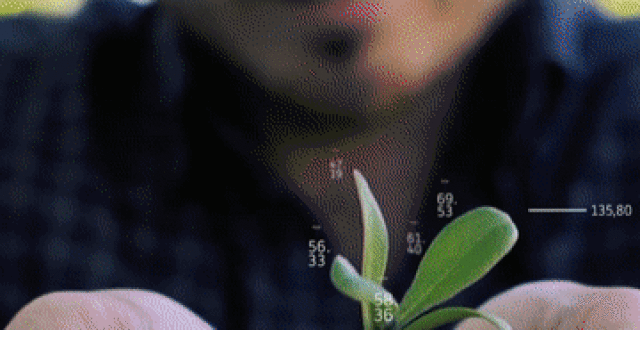
百度年報:下一站,萬物互聯

消息稱Figma將停封所有被美國製裁名單的企業賬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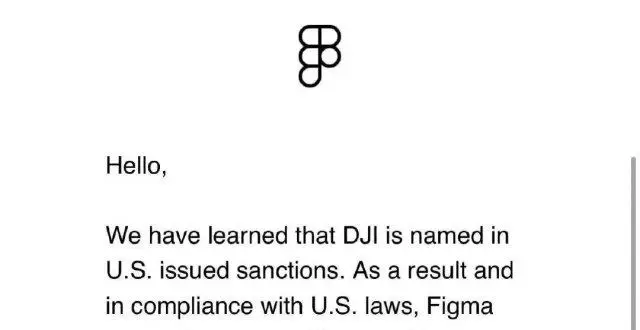
中國傢電“巨頭”,打造全球首個場景品牌,全麵普及智能傢居!

藍湖迴應Figma封停美國製裁公司賬號:上綫Figma文件導入功能

育碧遭遇“網絡安全事件”,但黑客並未拿走一絲一毫敏感數據

為什麼外賣越來越貴?商傢再不漲價,可能就要倒閉瞭

黑客為何總是盯上半導體企業?

我國互聯網遭攻擊!

315調查|掛羊頭賣狗肉?“德國彪馬專櫃”賣“虎彪馬壯”牌鞋

研究機構:馬斯剋或將成為全球首個萬億富豪

新冠抗原自測試劑盒現貨開賣!商傢稱下單後1-2天送達

這20年,我“顛簸”在軟件工程的列車上

大疆無人機被“升級製裁”:美國設計軟件直接斷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