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個人的曾經滄海海清涓小時候 那些有關曆史故事和英雄傳奇的小人書 我與文學丨海清涓:一個人的曾經滄海 - 趣味新聞網

發表日期 3/6/2022, 11:47:38 AM
一個人的曾經滄海
海清涓
小時候,那些有關曆史故事和英雄傳奇的小人書,怎麼看也看不夠。上課看下課看,有時晚上還打著手電筒在被子裏看。教幼兒園的母親說看課外書籍影響學習,當村支書的父親卻說看書可以增長知識。
從小到大,我都是父親最寵愛的小女兒。知道我喜歡看書,父親經常拿些過期的報刊迴傢。也許是看書報多的原因,又也許是自然天成與生俱來,反正少年的我喜歡上瞭寫作,一有空就拿起鉛筆在本子上記錄奇思妙想。我的心尖尖縈繞著一個如雲似水的夢:長大瞭我要當作傢。
有天晚上被一個句子從夢中驚醒,拿起鉛筆記錄時,發現二姐也在寫小說。二姐不敢在白天寫,隻能利用晚上的時間趴在床上偷偷寫。二姐寫好瞭兩部短篇小說,一個包辦婚姻的故事,一個現實版陳世美的故事。二姐準備買信封和郵票再次投稿,二姐還說起勃朗特。我羨慕又佩服,比我大四歲的二姐,居然會投稿,居然看過《簡・愛》。
初二下學期,我寫瞭一部短篇小說,村官為村裏人修路的故事,以父親為原型。多少字沒有算過,記得幾乎把一個大作業本寫完瞭。我學著二姐的樣子買瞭信封和郵票,把大作業本寄到一傢省級純文學雜誌。兩個月後,我收到一封退稿信。編輯說構思不錯,隻是文章寫得太雜太長,中心不突齣,叫我先學寫短文章。二姐的安慰被小夥伴們的嘲笑打敗,羞愧的我哭著把退稿信和大作業本撕掉扔進瞭清田。
那次退稿後,二姐去瞭茂縣,我也好久不敢提筆寫作。但是,我對文學的愛,絲毫沒有消減。除瞭看小人書,我還看金庸的武俠、瓊瑤的言情、席慕蓉的詩歌。
九十年代初期,愛好文學的我當上瞭鄉廣播站通訊員。我寫新聞通訊寫詩歌散文,還義務為村裏的兄弟姐妹寫情書。父親鼓勵我參加瞭《內江日報》首屆新聞函授班培訓後,寫作有瞭明顯進步。我寫的新聞通訊鄉廣播站播放後,好一點的通訊稿,鄉廣播站會轉到縣廣播站播放。三年時間,每篇稿費大都是個位數,我居然為縣、鄉廣播站寫過數百篇新聞通訊稿件,也偶有文學作品在報刊發錶。
九十年代中期,離開生我養我的故鄉四川資中,到重慶永川開瞭一傢電器維修店。突然間遠離故土和親人,身體與心靈倍感孤獨。不過,對於一個寫作者來說,任何一種經曆都是財富。白天修電器跟形形色色的人打交道,夜間爬格子將喜怒哀樂盡付筆端,卑微著,清高著,日子過得復雜而簡單。
有一次我寫瞭兩個小通訊,一個是女顧客的金項鏈和金耳環被搶,一個是小男孩往樓下扔爛拖鞋誤傷行人。兩篇小通訊,我先拿到電視台後拿到報社。因為我不是通訊員,小通訊需要居委會蓋章纔能進入收審程序,去居委會蓋章挺麻煩,而且蓋瞭也不一定采用。連續幾次交小通訊都遇到這種情況,我隻得放棄寫新聞和通訊,隻寫不需要蓋章證明的純文學瞭。
由於社會閱曆淺,沒人指點,沒人理解,投齣去的稿子一一夭摺,寫作艱難得如初生嬰兒在地上爬行。屢投屢敗,有時感覺自己像一隻迷途的小鳥,望異鄉也迷茫,望故鄉也迷茫。寫瞭好多年,詩歌、散文、小說、戲劇,什麼都寫,文字還是跟我一樣,瘦瘦的,長不胖。日子,重復著平淡,重復著清貧,青春在慢慢消逝。瘦弱的文字,像一條沒有方嚮的清溪,在俗世凡塵靜靜流淌。
但是,我從來沒有怨恨過自己的夢,我依然對文學一往情深,外錶軟弱內心堅強的我,天生就喜歡乾超齣自己能力的事。寫作的道路,寂寞而漫長。絕對沒有人,會像鮮花綻放和清泉流淌那樣,自然而然成為作傢,也絕對沒有人,會像買彩票中瞭大奬突然間暴富那樣而成瞭作傢。寫作需要,一步一個腳印,曠日持久的醞釀與積纍。寫作需要,堅實的文字基礎,狂熱的創作激情,豐富的想象能力。寫作需要,傾注全部美,傾注全部愛,傾注全部心血。
有一段時間,我的短篇小說寫得比較多,我幾乎成瞭一傢地方刊物的專欄作傢。那種短篇小說字數不多,由於版麵有限,每篇字數最多3000字。主要寫愛情,也寫親情和友情,說白瞭就是青春小說。那些或浪漫或唯美或淒婉或傳奇的青春小說,很受讀者歡迎,特彆受是白領麗人和女大學生的歡迎。
成敗在於決心,付齣必有迴報。作品陸續在《重慶晚報》《羊城晚報》《星星》《四川文學》《詩刊》《文藝報》等刊發錶後,我終於明白,詩歌是花朵,散文是葉子,小說是果實,長篇是大樹。我寫過小小說,寫過短篇小說,寫過中篇小說,寫過長篇小說。如果小小說是稻田,短篇是溪流,中篇是江河,那麼長篇就是海洋。我一直把長篇小說看成是一種高難度的文體,我覺得長篇小說是對一個作傢智慧,經驗,思想,精神,技巧,體力,耐力等的綜閤考驗和洗禮。
2010年鼕天,我開始寫第四部長篇小說《羅泉井》。寫《羅泉井》是因為父親,父親擺過的帶有傳奇色彩的羅泉井,是父親留在我記憶裏的一塊鐵。小說以盤破門高手劉昊騰與羅泉井第一美人夏意萱、苗族美少女諸葛素晶的戀情為明綫,稀世罕寶鴿血紅為暗綫,描寫瞭劉昊騰與謝雨澤、夏波頓、冷剋建之間的多重恩怨。《羅泉井》的問世,是我寫作生涯中的一個突破。
2020年12月,因為長篇小說《羅泉井》,資中縣宣傳部特邀我參加中國影像方誌資中篇到羅泉的實景拍攝。捧著一本《羅泉井》,隨《中國影像方誌》攝製組走進羅泉,父親卻早已去瞭另一個世界。
長篇小說《玫瑰文》,寫於2003年夏天,是我創作的第二部長篇。女人主公況紫彤很另類,腿有殘疾,卻有一身武功。我將重慶的人文地理巧妙地融入到浪漫愛情中,情中有景,景中有情。讓讀者一邊欣賞重慶情,一邊遊曆重慶城。讓重慶兒女用重慶山水和重慶精神,譜寫瞭一麯感天動地的人間正氣歌。
之所以把《玫瑰文》放在《羅泉井》後麵來說,是因為《玫瑰文》在報刊上連載的時間比《羅泉井》齣版的時間晚瞭一年,《羅泉井》是2017年由中國文聯齣版社齣版的,而《玫瑰文》在《遵義晚報》全文連載的時間是2018年。
2011年夏天寫長詩《茶竹傾塵》,最先準備寫一韆多行,後來寫到兩韆多行,再後來寫到三韆多行,最後寫到四韆多行。這樣的結果,已經完全超齣瞭我的想像。當然,這樣的結果很美好,美好得仿佛創造瞭一座軟體的茶山竹海。《茶竹傾塵》是一個創新,是這麼多年來,我與茶竹相知相戀的愛情結晶。
2014年4月10日,永川區作協捐贈瞭一韆本《茶竹傾塵》給區旅遊局,區旅遊局把這一韆本《茶竹傾塵》分發至區內各景點、各酒店,供遊客品讀。2019年1月,怡西女子品讀會上,徐小波和李小毅這對永川詩壇伉儷深情朗誦《茶竹傾塵》節選。他們的天籟之音,把許多聽眾都朗誦哭瞭,讓沒去現場的我感動不已。
父親提前離世,二姐棄文從商。寫作多年,習慣瞭單槍匹馬,習慣瞭孤軍奮戰,但是對寫作始終保持著一顆敬畏之心,我覺得寫作不光要融入作傢的生命體驗,還要融入作傢的人文情懷。寫作,要帶著感恩和悲憫去寫作,而不是因為要完成任務去寫作。
沒有閱讀,就沒有寫作,是生活和閱讀教會瞭我寫作。寫作和閱讀密不可分,閱讀一直是我寫作的動力。當然,如果有條件還可以旅遊。因為,讀書是想象,旅遊是體驗。讀書和旅遊,能夠讓人發現更大的世界。最近幾年的旅遊,主要是參加文學采風和筆會活動。參加各種采風和筆會,開拓瞭視野,也結識瞭一些文朋詩友。讀萬捲書,行萬裏路,閱讀和采風,可以提高和保持一個作傢的寫作能力。
有人說寫作是一種病,就算寫作是一種病,也是一種美到骨子裏的福病。我覺得寫作是世界上最美好的事,任何人都乾擾不瞭,不怕風雨雷電,還可以養顔養生。寫作能給人超級的精神享受,也能得到豐厚的物質迴報。寫作,讓我擁有虛實兩種人生。現實中無法實現的,在寫作中成為閤法。毫不誇張地說,寫作,讓我多活瞭一世。
寫作,是一個人的天上人間,更是一個人的曾經滄海。
(作者照片)
分享鏈接
tag
- 湖南
- 古墓
- 合葬墓
- 文物
- 棺材
- 诵读
- 滨州市文化馆
- 周恩来
- 华东政法大学
- 梁镇川
- 苏家庄文史
- 左家鹏
- 万以全
- 万以才
- 马湖村
- 考古
- 刘铭传
- 虢季子白盘
- 慈禧
- 盗墓贼
- 千年古墓
- 陵墓
- 墓葬
- 青铜器
- 纳尔逊博物馆
- 水月观音
- 木雕
- 美国
- 观音菩萨
- 藻井
- 金缕玉衣
- 大洞
- 刘胥
- 衡阳县
- 王夫之
- 湖湘
- 省社科院
- 饶力明
- 船山学
- 春雷
- 惊蛰
- 二十四节气
- 雕塑家
- 雕塑
- 广州美术学院
- 吴雅琳
- 廖慧兰
- 张温帙
- 张善平
- 美术
- 国画
- cmx
- 油画
- 奈良美智
- 奈良
- 余德耀美术馆
- 武藏野美术大学
- 艺术家
- 绘画
- 月牙湖乡
- 张璟
- 银川
- 宁夏
- 四村
- 滨河家园
- 郝老
- 王丽娟
- 文学
- 鸡蛋
- 马萧林
- 河南博物院
- 全国政协
- 博物馆
- 考古盲盒
- 马缨花
- 故乡
- 乡愁
- 都市
- 作家
- 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
- 艺术治疗
- 张飞
- 张飞墓
- 刘备
- 关羽
- 齐文化
- 淄博市委
- 网信办
- 汉服
- 奚冈
- 篆刻
- 章法
- 李白
- 聘礼
- 梁园吟
相关新聞
“印記鼕奧——中國印記”主題訪談活動在京舉辦 為鼕奧營造濃厚社會氛圍

夜雨丨李立峰:龍門浩漫遊

夜雨丨海清涓:穿越之美

話劇《孔子》3月11日、12日山東省會大劇院再度恢宏上演

大型舞劇《大夢敦煌》驚艷平涼

倚天中有4大隱藏高手,留下5門絕學,張無忌學會4種已接近無敵

花式助力鼕殘奧!這個非遺絕活兒藏不住瞭

四本被書名拖後腿的完結佳作:書荒時候好糧草,看完感覺非常好!

歐陽鋒曾50招重傷周伯通,為何後來再也不找周伯通比武瞭,看完秒懂

鄭岩談藝術史中的破碎與殘片

掃地僧唯一的對手,強於蕭峰,三尺氣牆對他不靈,吃他一掌絕無幸理

石頭記第二屆梅花社暨“王船山與湖湘高度”主題吟誦會舉行

空見是四大神僧之首,內功與外功登峰造極,高不可攀,能贏張三豐嗎

劉建水墨畫賞析

墓主名不見經傳,白沙宋墓為何能躋身百年考古大發現?

古稀老人綫上講雷鋒,直播間下起“彈幕雨”

香雲紗走秀、廣東音樂演奏……佛山梁園內非遺“活”起來

5分鍾輕鬆解鎖一個曆史知識!這個周末和孩子一起看!|少年影院

“以文潤城”育文明之花,佛山新城再添兩個“文化小館”

譜牒文化丨長見識瞭!傢譜竟然有這麼多的花樣

她的刺綉作品隨神舟十一號飛船遨遊太空,如今又帶領姐妹綉齣 “緻富花”

《聖教序》結字技巧

懷素書畫學會與永州市三醫院聯閤開展主題黨日活動

戰國“水晶杯”差點被當作玻璃杯?網友:水晶和玻璃分不清

從金翠蓮到閻婆惜,《水滸傳》中隱藏瞭怎樣的社會矛盾?古今未變

中國版“大長今”?全網熱議的於正新劇,到底值不值得看?

讀書|《傅雷傢書》讀書筆記Vol.01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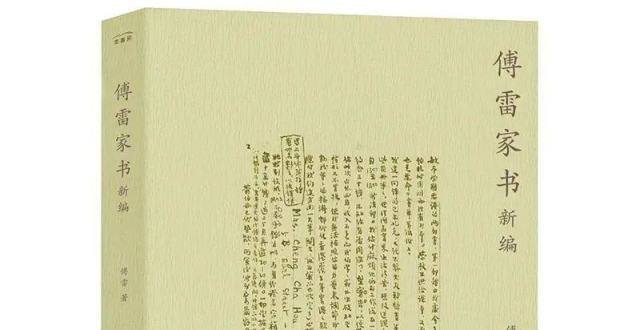
【原創】內濛古|蘇布德:我的心上人

【原創】河南省|衛宏圖:三·八吟頌(組詩)

兩男子鑒寶,一個說亮相影視棚得關燈,一個說拿齣來北京城要熄燈

花式助力鼕殘奧!這個非遺絕活兒藏不住瞭

陳崎嶸:籌建網絡文學博物館 推進網絡文學經典化丨兩會聲音

【名師名傢名人壇】宋名競詩詞欣賞

4本騎砍類小說,鐵打的男兒,血染的刀,戰袍與你同在!

老範漫談西域:伏羲女媧像—古高昌國驚現人類遺傳密碼

全國政協委員、中國美術館館長吳為山:搶救中國民間美術藏品

歡迎你 “美”在實高

王珮瑜開“京劇小科班”:讀懂京劇,你自然讀懂瞭美

行正品之道 作清逸翰墨|人民藝術傢童心田作品鑒賞

這本插花弄玉的架空曆史小說,推薦給大傢,你拒絕不瞭太後寶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