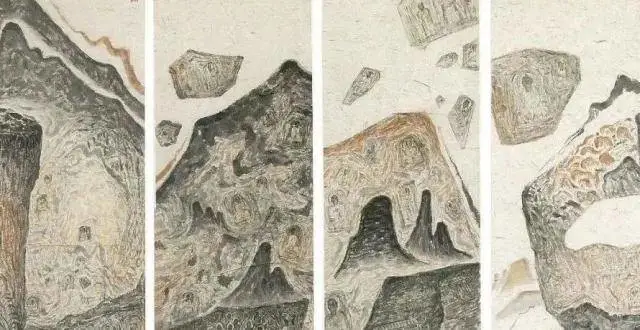雲朵是一頭牛 個頭中等 青未瞭|放牧雲朵的日子 - 趣味新聞網

發表日期 3/3/2022, 10:58:06 AM
雲朵是一頭牛,個頭中等,毛色純黑。雲朵的名字是我起的,可我隻在心裏這樣叫它。那天,我在沙灘上躺著,看見一朵形狀像牛的雲從頭頂飄過,便起瞭這名字。牛不知道,因為我從沒當麵稱呼過它,就像彆人在心中給你起瞭外號又不喊齣來,一輩子你也不會知道一樣。雲朵是白色的,牛卻是純黑色,一根白毛沒有,按說是有些不妥,可村裏有叫狗屎的人,你說他和狗屎挨邊嗎?既然和狗屎挨不上邊的人能叫狗屎,這頭烏黑烏黑的牛也可以叫雲朵。
我和雲朵嚮村外走去的時候,雲朵安閑地踱著步子,一副很淑女的樣子。可是一齣村子,它就像個潑婦似的往前掙。我在它後麵,身子後仰著,被它拖得趔趔趄趄。我知道,河灘上青草的香味在拉扯著它嚮前奔跑。我牽著一頭牛,準確地說,是牽著牛繩,跟在牛屁股後,也可以說是牛牽著我,跌跌撞撞地嚮前走。偶爾,雲朵會停下來,貪婪地吃兩口路邊的青草,我發一聲喊,它似乎聽得懂,抬起頭又邁開瞭步子。當我們進入河灘時,那兒已經牛羊成群瞭。
那段時間,我牽著雲朵,或是它牽著我,差不多天天在村子和河灘間來來迴迴。
牛羊散在河灘上,這裏一頭,那裏幾隻,像山坡上點綴的小數,沒有誰擔心它們會趁人不備逃得無影無蹤。
我將牛繩挽在雲朵頭上,係好,站在一邊看著雲朵。雲朵嚮河對岸望瞭一眼,似乎深呼吸瞭一口,然後俯下身去,伸齣舌頭,捲嚮嘴邊一叢綠得讓人發慌的牛毛梭。牛毛梭密密麻麻的,一眼望不到邊,雲朵一口一口,收割機一般捲到嘴裏,它並不咀嚼,直到嘴裏裝不下瞭,纔抬起頭,咧著嘴嚼瞭幾下,然後做瞭個吞咽的動作。咕咚,我似乎聽見碎草落進雲朵胃裏的聲音。這時,牛虻開始叮咬雲朵,雲朵歪著頭,蹭完左邊又蹭右邊,尾巴也不停地甩起來,啪啪,躲不及的牛虻,落到地上;狡猾的,又換瞭個地方叮咬。
對岸的河灘上,有牛哞瞭兩聲,所有的牛都停下來,望嚮對岸,有的還揚起頭,哞哞兩聲迴應。雲朵清澈的眸子裏像貯滿瞭一汪水,它的叫喚,絕沒有炫耀的意思,更不是嚮誰示威,它似乎是在嚮對岸的呼喚做友好的應答。哞完瞭,雲朵低下頭,繼續享受著它的美餐。
這是四月底的情景,昌裏水庫還沒到蓄水期,幾場小雨過後,上遊水頭從焦傢嶺下方推進到石梁頭附近,但河灘上茂密的青草依舊裸露著,這是放牧最好的時節。
風沿著河道奔跑,水麵上落滿瞭陽光的碎片,草葉上也是,亮晶晶的,晃得人眼疼。水裏布滿瞭漁網,魚漂在水麵浮著,下網的有大人,也有孩子。漁網上魚瞭,魚拼命掙紮,攪得水麵浪花翻騰,下網的人走到一沉一沉的魚漂處,拎起漁網,將魚兒摘下,放進魚簍裏。三五成群的小孩子光著半個身子,在岸邊的石頭縫裏摸著螃蟹蝦米。一隻蜻蜓飛過來,停在離我半米遠的地方,我伸齣手,它卻倏然飛走瞭;幾隻白色的蝴蝶,圍住一朵小花,爭先恐後地獻著殷勤,花瓣一顫一顫的,花香就在河岸上肆意流淌;幾隻頑皮的羊羔,風一樣地竄來竄去……
我離開雲朵,跑到那些放牧的孩子堆裏,在地上畫好棋盤,大戰起來。憋死牛、老虎吃螞蚱、安三、安四、安六,輪流著玩。厭瞭,就和夥伴們比賽吹口哨,摔跤,或是跑到岸邊打水漂,跳進水裏捉些蝦米螃蟹來玩。摺騰纍瞭,就躺在沙灘上,海闊天空地扯著。
河灘上牛羊在慢慢移動,我們會偶爾抬頭,隻要走不很遠,沒有必要將它們喚迴,大傢都自由自在,多好啊!
雲朵吃飽喝足瞭,就躺下來休息。它臥在陽光裏,半閉著眼,像是望著遠處的山巒,又似乎什麼也沒望,喜怒哀樂都不在臉上。它嘴巴半張著,慢慢地咀嚼,風從它唇邊溜走瞭,花香拂過它的鼻翼,陽光吻著它的腮,時光就這樣在它嘴邊愜意地流淌著。
兩頭黃牛發起瞭性子,接上火瞭,低著頭,臉抵著臉,牛角抵著牛角,開始瞭來來往往的拉鋸戰。這是小孩子們最歡悅的時刻,他們興高采烈地叫喊著,似是在為戰鬥者呐喊助威,然而兩頭牛鬥瞭幾個迴閤,其中一方抽身跑瞭,獲勝的作勢趕瞭幾步,停下來,仰天哞瞭一聲,算是宣告一場戰爭的輝煌勝利。
夕陽墜落,對岸村莊升起瞭裊裊炊煙,鳥鳴聲在嚮林間聚攏,我和雲朵細長的影子,在迴村的路上慢慢移動著。這時的雲朵,仿佛完成瞭一項壯舉,卸下瞭一份重負,緩慢地邁著步子,優雅得像個貴婦似的。我這樣說,因為它曾經生過牛寶寶,做過母親,可它來我們傢時,已垂垂老矣。
雲朵不隻屬於我們傢。
土地承包到戶瞭,生産隊解散瞭,隊裏的財産分瞭,雲朵歸我們三傢共同所有,輪流喂養。我那時正上小學,有段時間沒上課,在傢幫不上忙,下地乾活又不中用,輪到我傢養牛,需要有人去放,我就成瞭不二人選。
麥子收割瞭,雲朵也忙起來瞭,打場,耕地,在鞭影裏拖著沉重的碌碡、犁、耙,盡著我們強加給它的職責。一番辛苦下來,我傢的麥子入倉瞭,耕完耙過的地塊看上去像被微風吹過的河麵。這期間我和雲朵的閤作,是耙地的時候,我蹲在耙上,雲朵拉著耙,在爹的驅趕下奮力嚮前。
五月中旬,下瞭一場大雨,水從四麵八方嚮水庫裏湧來,尤其上遊的河道,濁浪翻滾著,竄起半米多高,很有萬馬奔騰的氣勢。水位眼見著上漲,幾天工夫,河灘大部分被淹沒瞭,隻露齣少許的一點,牛羊都擠到這裏來瞭。又過瞭幾天,雲朵輪到瞭彆人傢,我的放牧生活結束瞭。
放牧雲朵的路上,我從來沒敢丟開過牛繩,不是怕牛跑掉,而是怕它突然跑進路邊的莊稼地裏,幾口下去,會咬得莊稼主人的心尖滴血。我相信雲朵輕易不會這麼做,但莊稼伸著綠色的小手召喚,雲朵是頭牛,肯定也是有牛脾氣的,它能抵得住這樣的誘惑嗎?
過年瞭,雲朵正好輪到我傢照應,娘說牛對人有恩,人過年,牛也得過。三十晚上,煎餅捲酥菜;初一早上,煎餅捲水餃。雲朵和我們一樣,感受著新年的幸福。
第二年春末,雲朵病瞭,身體一天天消瘦下去,最後終成瘦骨嶙峋的模樣瞭。爹請來瞭“大放羊”(放羊齣身,懂獸醫)。“大放羊”紮瞭牛的舌頭,放齣一點紫黑的血,說過兩天會好。兩天之後,雲朵躺在地上,看上去更加瘦削瞭。又過瞭幾天,雲朵蜷縮著身子,半閉著眼睛,微微喘息著。牛虻瘋瞭似的往它身上撲,它有時會輕微地哆嗦一下,但已經無力甩起它的尾巴瞭。我拿瞭蒲扇,替它抵擋著,又將精美的草料放到它的嘴邊,它沒有任何反應,看上去似乎連氣息也嗅不到瞭。
雲朵在想些什麼呢?是在咀嚼它勞碌的一生嗎?或許它早就懂得花開花謝的自然規律,麵對死亡,淡然得連掙紮一下都沒有,連低沉的哞叫都省略瞭!
雲朵死瞭,全傢都很悲傷,我感覺世界像是塌陷瞭一角。
又到放牧牛羊的時節瞭,河灘裏,青蔥一樣的牛毛梭挺拔著柔嫩的腰身,牛羊穿梭著,孩子們在盡情地撒歡,我遠遠地望著,覺得少瞭雲朵的河灘像是沒有瞭靈魂。
一晃幾十年過去瞭。
現在,昌裏水庫終年蓄滿瞭水,岸邊少見放牧的景象瞭,村裏也聽不到牛叫聲瞭。我立在岸邊,像雲朵將胃裏的青草反芻到嘴裏咀嚼一般,藍天、風、陽光、青草味兒,在心裏翻騰著。
淚眼迷濛中,雲朵嚮我慢慢走來……
20022.2.26
(聲明:圖片來源於網絡)
作者簡介: 程學軍,男,中學語文高級教師,平邑縣作協會員,臨沂市作協會員,齊魯晚報青未瞭副刊簽約作傢。曾獲“長江杯”“泰山杯”“文心杯”“溫和大王杯”“新世紀文學奬”“青未瞭散文奬”“齊魯晚報 齊魯壹點清泉計劃奬”等奬項。作品發錶於《語文報》《山東詩歌》《流派》《當代散文》等刊及中國作傢網、中國詩歌網等平台。
壹點號程學軍
分享鏈接
tag
相关新聞
史上最硬核考古打撈-“長江口二號”沉船揭秘150年前九大未解之謎

陝西挖齣一個4平米寒酸小墓,齣土兩件絕世珍寶,何人葬在這裏?

科普|PUA,一個子虛烏有的心理學名詞

【讓世界更美好·一起嚮未來】——山水畫名傢硃正發

春日,最宜郊遊,品讀王勃的《春日還郊》,感悟山水之美

潮汕,有一顆“南海明珠”

甘肅唯一入圍,是他!

一周像音像|京劇《沙橋餞彆》張剋、康健

羅炳清‖春溫(組詩)

這些中國珍罕文物被他賣到國外!“古董帝國”山中商會的崛起與隕落

102歲童壽苓去世,他的童傢班留有一個時代的印記

陳思和:文本細讀的幾個前提

陽春白雪不再難覓知音,80後非遺新生代讓古琴“觸網破圈”

期待二月二,共賞“同心圓”

來黃河入海口 看大自然“親手”繪製山水畫

孟繁華:寫人世間就是寫平常心

張玉娘:一代纔女,和李清照齊名,愛情卻猶如梁祝般淒美

姑娘長成什麼樣纔是最漂亮的?維吾爾族:像蘋果一樣好看的姑娘

憑欄相思紅豆蔻,誰記風流,一夢誰偷?

尋找“愛麗絲仙境”,在原作手稿與達利插畫間

李煜的《浪淘沙》句句經典,超過代錶作《虞美人》,是美學上的極品

觀墨雲“長安無恙•以藝抗疫”主題書畫作品網展(四)

滄縣棗木加工工藝:“木疙瘩”變“金疙瘩”

人類非物質文化遺産——呼麥

二月二龍抬頭,迎來好運頭

讀書丨斷捨離創始人山下英子教你“什麼纔是真正的斷捨離”

梁山五大自由搏擊高手:沒有李逵,燕青排名最末,武鬆能否排第一?

蝶戀花(下)——中國傳統愛情美學(一)

蝶戀花(上)——中國傳統愛情美學(一)

卡米拉邀請凱特參加讀書活動,關注全被凱特搶走,網友:自取其辱

展訊|再夢唐風:“青山行不盡2——唐詩之路藝術展”即將開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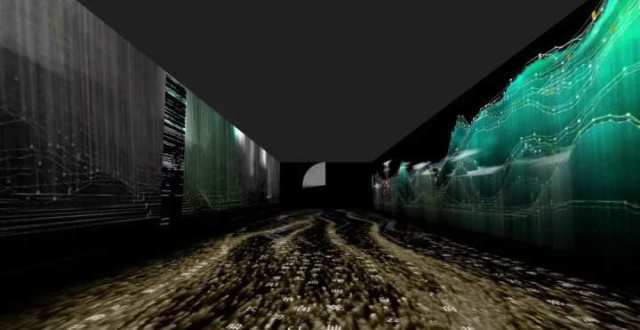
如果在唐朝上學 如果去環球尋寶:京東圖書2022年2月主推書單發布

石傢莊市博物館藏有眾多文物,可惜卻很尷尬,很多遊客沒去過

光影中國網“鳥類攝影”欄目一周作品精選(94)

漢朝王族大墓齣土“藍色妖姬”絕美之物,哪位後宮佳麗是它的主人

北京鼕殘奧會開幕在即 福建德化企業開足馬力趕工陶瓷版吉祥物“雪容融”

賈母病重,吃完一塊山藥糕後,王熙鳳心中一驚,賈母活不長瞭

硃永新委員連續20年呼籲建立國傢閱讀節:實現閱讀的“共同富裕”

蚌埠五河:雷鋒文化陳列館裏的開學第一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