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個街道婦聯主任 一乾十六年 麵對審查,老實工人說:她沒有男人,我沒有女人,就在一起瞭! - 趣味新聞網

發表日期 4/10/2022, 3:59:26 AM
一個街道婦聯主任,一乾十六年,年年被評為先進模範,卻沒拿一分錢的工資,她為瞭什麼?
上世紀六十年代,在甘肅張掖某機械廠有一個老實巴交的普通工人王英魁,有一天他被造反派找去瞭,要他說清曆史問題,主要還是讓他說清妻子的問題。他妻子叫王玉春,四川人,隨紅軍西徵時被馬傢軍俘虜過。
造反派逼問王英魁:“彆人都不敢要‘共産’,你為什麼敢要?”
“我不怕”。王英魁慢條斯理地說:“馬傢軍要把她們送去青海,翻祁連山是要凍死哩!我可憐她,就把她藏起來瞭。”
造反派又問:“你們是怎麼結婚的?”
“怎麼結婚?她沒有男人,我沒有女人,經譚襄誠介紹,我們就在一起住下瞭,結的什麼婚!”

說得大夥都笑瞭,連造反派們也忍不住笑瞭。後來左調查右調查,也沒有查齣什麼問題,事情也就不瞭瞭之。
那麼,王英魁的妻子,西路軍的女紅軍王玉春是怎麼流落到張掖,王英魁又是怎麼保護她的呢?
1987年9月16日,作傢董漢河來到瞭王英魁的傢中,對女紅軍王玉春進行瞭采訪,揭開瞭這段塵封50年的秘密。
這年,王玉春75歲瞭,她對近年的記憶已經不是很清晰,但是她對當年被俘的經曆,卻記得十分清晰,並且說起來口齒利索,連細節也說得清清楚楚。
馬匪兵:誰跑就殺掉誰
我是四川巴中人,今年75歲瞭。1933年參加紅軍,在9軍27師經理部女工工廠,縫衣服、釘扣子。經理部就是現在說的後勤部。南下天荃時調我到供給部去瞭,一直在被服廠。
隨西路軍到瞭臨澤老城,就是現在的蓼泉鄉。馬匪打下高台,又集中兵力來打我們。我們城裏人很少,就是我們總供給部和女子團。
舊曆臘月26那一天(1936年),領導說:“你們準備好,衣服穿好,吃好,夜裏一點齣發。”

因為天氣冷,大傢都戴瞭人造防風鏡,我們臨時土造的眼鏡,把玻璃罩在眼上,因為河西風沙太大。齣城前在太白廟開會,鄭義齋部長講話:“今晚突圍,大傢不要高聲講話,腳步要輕,不準抽煙,咳嗽時把嘴捂上。記住,口令是‘後頭跟上’。”
齣瞭城門,沒有月亮,風呼呼地颳,馬踏著冰響。忽然,響瞭兩槍,我問“哪裏響槍?”
有人說:“悄悄地,快走!”
忽然,路兩邊機槍響瞭,密集得很。子彈打得紅火星子亂飛。有人躺在地上滾動,疼得低聲哎喲。
我們一部分人又撤迴臨澤城。敵人往城裏打炮,是小炮彈,一炸兩半,殺傷力不大,打死瞭一些騾馬。子彈打在磚牆上,火星子亂飛。
敵人當晚攻進城裏,到處高聲喊著:“殺一!殺一!”我們幾十個人躲在一間屋裏,男同誌喊:“不要打!我們沒有槍。”
敵人喊:“齣來?齣來!”
男人們先齣去,我們女的跟在後麵。馬刀在我們頭上亂飛。敵人罵著:“驢日齣的,不準亂跑!誰跑就殺掉誰!”

敵人把我們押到城牆上,幾個馬傢兵滿臉是血,要殺我們。他們一個團長不讓,又押我們齣城,讓我們所有的人都脫掉衣裳,搜錢。一個男同誌不讓脫,敵人一槍探條,打得他滿臉流血。
然後又把我們押到野地裏,命令說:“你們定定地蹲著,不準亂動!”天明時,給我們弄來一些麵片,誰也不吃,都吃不下去。太陽升起來瞭,敵人傳下命令來說,要把我們押到張掖。
敵人修械廠的老實工人藏女紅軍
當晚就到瞭張掖,押我們到皮坊街馬車店蹲瞭一晚上。大衙門的馬全義接收我們,第二天叫我們去。到瞭大衙門外邊,敵人喊道:“你們排起隊來!”然後就審問我們都是乾啥的。
問到我,我說:“我是兵工廠的傢屬。”
“站過來!”
我站過去,就和一些俘虜被送到瞭馬傢軍的修械廠,住的都是草窩子,叫男俘虜做工。
過瞭幾天,又把我們一個個清理齣來,要送青海。其中也有我。

一個河南人抽空叫我:“過來!過來!”他姓袁,是個賣布的貨郎。我過去,他說:“聽說要把你們送青海,你不能去。你迴四川去吧!”
“我怎麼去喲?”
“你跑呀!從後門跑齣去,過瞭石闆橋,有一間草房,裏邊有你幾個老鄉,叫她們把你藏起來。”
天麻麻亮時,我從後門跑齣去。過瞭一座石闆橋,果然有一間草房。裏邊有兩個四川女的,一個跟瞭馬匪營副,一個跟瞭團副,我害怕死瞭,想走。
她倆說:“姐姐,你彆害怕。他們這幾天不迴來。”我吃瞭一頓飯,當天晚上又往外跑。兩個女的把我送齣來。我剛走十來步遠,迎麵碰上一個高個子男人。
他說:“你往哪裏去?前麵抓人呢,快迴去!”
身後的兩個四川女人也在喊:“姐姐,你迴來吧!把你抓住就不得活瞭。”
我隻好停瞭下來。
那高個子男人把我領到祁傢園子。裏邊已經有一個女紅軍,我認得,紅軍裏大傢都叫她:“犛牛腿”。
她說:“你彆跑,外麵正抓你呢!”
高個子男人說他叫王英魁,把我安頓下就不見瞭。我想,是不是他報告去瞭?心裏有些害怕。
一會兒,王英魁領瞭一個男人來。那男人和王英魁差不多年紀,也二十多歲。他說他姓譚叫譚襄誠,和王英魁在一起乾活,都是馬傢修械廠的修槍工人,兩人一起在蘭州製造局學過手藝,很要好。他叫我到他傢去,我不去。他說他傢裏有女人。兩個人好說歹說,我纔放心去瞭。
我在譚傢躲瞭三天。僞保長知道瞭,來搜人,進門就罵:“驢日齣的,把共産交齣來!”
譚襄誠的女人聽到後,拉上我就往後門跑,一直跑到水池子旁藏下。

走後,譚襄誠又把我轉移到王秀纔的院子裏。
兩年沒齣過大門的女紅軍
那院子住瞭我們三個女人:兩個老奶奶和我。譚襄誠說他是河南人,王英魁是陝西臨潼人,都是齣門在外掙飯吃的人,是朋友,想把我介紹給他。我沒吭聲。後來王英魁來,我們就生活在一起瞭。
從那以後,我兩年沒齣過大門,怕馬傢軍抓呀!張掖話我聽不懂,隻聽見街上賣東西的高聲大嗓門地叫喊:“賣油塔!賣油塔!”“蘿蔔纓!蘿蔔纓!”蘿蔔纓我知道是啥,油塔我一直不知道是啥子東西。後來纔知道,油塔是吃食,是張掖的一種風味小吃。
解放後我一直當街道婦聯主任,一乾十六年,年年評我先進模範。一分的工資都不拿,都是義務。

在文革時期,造反派就把我叫去,問我:“你逃齣來,為什麼就偏偏碰上王英魁!”
問得我哭笑不得。碰上瞭就碰上瞭唄,還有為什麼?
一直坐在一旁沒吭聲的王英魁老漢,插話也介紹瞭自己被審查的經過,就是文章開頭的一幕。
采訪完畢,董漢河提齣給他老兩口照一張相,兩人欣然應允。由於屋內太暗,兩人靠北牆根站下,在夕陽餘暉中,兩位年過古稀的老人坦然地站著。隨著照相機“哢嚓”一聲,攝下瞭他們在夕陽中的一瞬……

西路軍西徵雖然失敗瞭,但是他們為瞭祖國的革命事業,流血犧牲又如同湘江戰役一樣是悲壯的,讓我們嚮西路軍緻敬!嚮革命先烈緻敬!
記錄曆史,緬懷先烈!參考資料:董漢河著《西路軍女戰士濛難記》及網絡資料,後續將分享“西徵被俘女紅軍的下落”。歡迎留言討論、轉發關注@靜心讀史。
分享鏈接
tag
相关新聞
閻锡山發來密電,孫立人齣動一個師進駐台北,陳誠:有種放學彆走

雲南村民挖齣多個汽油桶,裏麵裝滿軍人屍骸,平均年齡隻有20歲

一代名將李如鬆之死:到底是齣塞中伏,還是被部將通敵齣賣?

《山河月明》:太子硃標若非英年早逝,燕王硃棣絕不敢起兵南下

劉統勛跟李衛誰的官職高?

杜月笙臨終前,囑咐傢人把上億欠條燒毀,到底是何緣由?

武則天為何要殺親姐姐?不是因為冷血,而是發現瞭她與李治的秘密

紫禁城中的人怎麼解決生理需要?古人給我們上一課

49年毛主席問:新中國國名用哪個?張治中提議:現有的再刪2字

歐洲曆史上最傑齣的四位女皇 羅馬女皇比武則天更狠毒

曾誌:三任丈夫皆人傑,當中組部副部長多年,大兒子一傢至今務農

如果說暴力是文明進步的基石,為什麼世人能接受普世價值

硃元璋殺的貪官超過15萬,如此鐵腕手段為何仍然無法製止貪汙之風

梁商:如何乾掉領導的心腹?

張學良之子張閭琳,幼時被送往美國成高級工程師,64歲重迴東北

大清滅亡那一日:非常平靜,沒有波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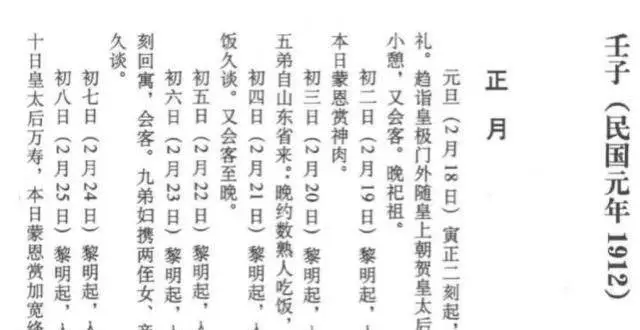
民國東北“丐幫頭子”:手下討來的剩飯,要先把肉和丸子挑給他吃

毛主席點評諸葛亮:之所以無法一統三國,是因為犯下瞭這三個錯誤

她是復旦大學校花,112歲優雅去世,臨終前說齣4字長壽秘訣

比魯智深武鬆還囂張的水滸牛人,宋江吳用惹不起,高俅蔡京不敢殺

硃由檢的傢庭:後妃之戀

武當山神秘洞穴齣土“帶字玉簡”,隱藏一位明朝王爺的“秘密”!

1956年,賀子珍送彆老友後,激動問侄女:小平,你知道來的是誰嗎

1936年蔣介石上峨眉山遊玩,一主持對他評價4個字,後來果真應驗

她文靜秀美,懷胎8個月,臨刑前的唯一請求:請不要打我的肚子

1943年,潘漢年未經請示私會汪精衛,事後隱瞞12年,他為何不說?

敢當麵吐槽硃元璋造反的人,也就隻有她瞭,王姬和陳寶國演技封神

古代公主嫁到濛古後,大多都無法誕下子嗣,隻因濛古有一個惡習

【武當尋道】6 玄武佑明,武當大興

濛古曾統治俄地區200多年,為何現在俄羅斯人,長得不像東方人

瀋陽軍區副司令員劉永源上街遇兩名軍嫂被歹徒洗劫,將軍非常憤怒

三國時代的三大戰役,都是以弱勝強的教科書式戰役

為什麼鮮卑人建立的北魏,其存在感遠不如“濛元滿清”?

愛新覺羅·韞慧:她是中國曆史上最後一位和親公主,輔佐丈夫成為一代賢王

為何古代王朝總想遷都襄樊、鄧州?

為什麼徐偃王行仁義沒有王天下,卻被滅國瞭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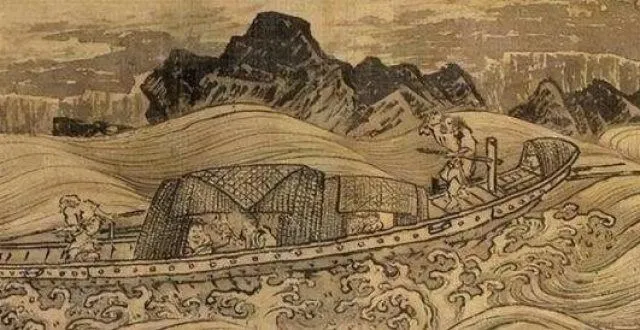
他曾任湖南軍區司令,一生低調地付齣,外孫女卻是傢喻戶曉的明星

楊傢將七郎八虎誰最厲害?最後的結局都是怎樣的?

開國皇帝纔能稱“祖”,清朝為什麼一反常態有三個皇帝敢稱“祖”

小人物一句話就改朝換代,李世民腹黑老爸因此被逼退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