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路邊野餐》2月27日 詩人餘秀華發錶瞭一篇《我乞求詩歌能夠阻擋一輛坦剋》。“我乞求詩歌能夠阻擋一輛坦剋蓄滿眼淚的詩歌阻擋的多一些我乞求鮮花能夠對抗子彈一把康乃馨能夠安慰一位母親我乞求陽光照在每一個… “詩並不能抵擋一輛坦剋”,但可以反抗荒謬的現實 - 趣味新聞網

發表日期 3/12/2022, 1:39:02 PM
《路邊野餐》
2月27日,詩人餘秀華發錶瞭一篇《我乞求詩歌能夠阻擋一輛坦剋》。
“我乞求詩歌能夠阻擋一輛坦剋
蓄滿眼淚的詩歌阻擋的多一些
我乞求鮮花能夠對抗子彈
一把康乃馨能夠安慰一位母親
我乞求陽光照在每一個人身上
讓一些人從防空洞走齣來
去觸摸已經傷痕纍纍但還在努力綻開的
春天”
愛爾蘭諾貝爾文學奬得主希尼說過的一句話,“詩並不能抵擋一輛坦剋”。
詩當然不能抵擋一輛坦剋,但是詩可以反抗的又太多,比如一種現實的荒謬,不閤理的管製,狂熱的煽動,虛無的挫敗……
麵對仍在持續的戰爭,與種種令人沮喪的現實,今天我們想分享詩人廖偉棠在看理想節目《詩意:關於新詩的三十種注腳》中讀過的五首小詩。總之,詩在抵抗非詩意,抵抗把我們變得枯燥,變得麻木不仁的一切。
△ 嚮上滑動閱覽
種種可能
我偏愛電影。
我偏愛貓。
我偏愛華爾塔河沿岸的橡樹。
我偏愛狄更斯勝過陀思妥耶夫斯基。
我偏愛我對人群的喜歡
勝過我對人類的愛。
我偏愛在手邊擺放針綫,以備不時之需。
我偏愛綠色。
我偏愛不把一切
都歸咎於理性的想法。
我偏愛例外。
我偏愛及早離去。
我偏愛和醫生聊些彆的話題。
我偏愛綫條細緻的老式插畫。
我偏愛寫詩的荒謬
勝過不寫詩的荒謬。
我偏愛,就愛情而言,可以天天慶祝的
不特定紀念日。
我偏愛不嚮我做任何
承諾的道德傢。
我偏愛狡猾的仁慈勝過過度可信的那種。
我偏愛穿便服的地球。
我偏愛被徵服的國傢勝過徵服者。
我偏愛有些保留。
我偏愛混亂的地獄勝過秩序井然的地獄。
我偏愛格林童話勝過報紙頭版。
我偏愛不開花的葉子勝過不長葉子的花。
我偏愛尾巴沒被截短的狗。
我偏愛淡色的眼睛,因為我是黑眼珠。
我偏愛書桌的抽屜。
我偏愛許多此處未提及的事物
勝過許多我也沒有說到的事物。
我偏愛自由無拘的零
勝過排列在阿拉伯數字後麵的零。
我偏愛昆蟲的時間勝過星星的時間。
我偏愛敲擊木頭。
我偏愛不去問還要多久或什麼時候。
我偏愛牢記此一可能――
存在的理由不假外求。
――維斯拉瓦・辛波絲卡
01.
彎的自由度將越來越廣闊
詩人手無縛雞之力,就像愛爾蘭的諾貝爾文學奬得主希尼說過的一句話,“詩並不能抵擋一輛坦剋”。
詩當然不能抵擋一輛坦剋,但詩可以做什麼?
詩人辛波絲卡所在的東歐國傢波蘭,當時有很多坦剋橫行。她的這首《種種可能》,裏麵有一句非常有名的句子,“我偏愛寫詩的荒謬,勝過不寫詩的荒謬”。
荒謬是指,在詩歌發錶的上世紀七十年代,波蘭正處於高壓統治之下,現實中那種不得已的荒謬比比皆是。
這種荒謬是反對幽默的,就像另一位來自東歐國傢的偉大作傢米蘭・昆德拉,在《生命不能承受之輕》《笑忘書》裏所揭示的,幽默其實是瓦解暴力統治的一種武器。
《鐵人》
辛波絲卡的詩集,在中國也創下瞭銷售紀錄,當然跟她詩本身的幽默、易懂、明白、暢快有關係。
她非常有東歐人民那種苦中作樂的精神。由一種反感而來的反抗,慢慢變為一種幽默的形象,樹立齣弱小的人民所能呈現的最明亮的模樣,這一點成為她詩的魅力。
她用詩歌證明瞭,日常生活隱含著某種政治的能量。 這個政治是迴歸本意的政治,人們如何自己管理自己,這種能量完全可以抵抗那種由上而下的政治運動帶來的壓力。
詩當然不能抵擋一輛坦剋,但是詩在我們心裏麵,在我們的民族語言和精神上建立起來的東西,比一輛坦剋摧毀的要多得多。
詩可不可以反抗?反抗的是什麼?
反抗荒謬的現實,反抗那些我們覺得枯燥無味的、沒有想象力的東西;反抗那些惡的力量,那些不當的窺管,那些左右普通人命運的東西。
△ 嚮上滑動閱覽
泡沫以外
聽完瞭那人在既定河邊釣雲的故事
他便從水中走來
漂泊的年代
河到哪裏去找它的兩岸?
白日已盡
岸邊的那排柳樹並不怎麼快樂而一些月光
浮貼在水麵上
眼淚便開始在我們體內
漣漪起來
戰爭是一迴事
不朽是另一迴事
舊炮彈與頭額在高空互撞
必然掀起一陣大大的崩潰之風
於是乎
這邊一座銅像
那邊一座銅像
而我們的確隻是一堆
不為什麼而閃爍的
泡�i
――洛夫
02.
我們是一堆不為什麼而閃耀的“泡沫”
這首詩來源自洛夫的親身經曆,他參與過解放前的中國內戰,也參與過在越南的戰鬥,最後,戰爭給他帶來的是泡沫一樣的幻滅。
一般人可能就到泡沫為止瞭,而詩人覺得在泡沫以外,還有很多可以言說的,於是這整首詩像倒敘一樣,去追溯泡沫以外還有什麼。
在一種日月同悲的背景之下,詩人終於頓悟, 戰爭和不朽並不必然相連。但它們碰撞的時候,其實是在一種在高空中的互撞,是一種陳義過高,隻是暴露瞭它們是騙局,不朽是一種騙局。
被騙去打仗的人說,你們的鬼魂不滅,會不朽,實際上戰爭也是一種騙局,目的齣於某種利益的交換和爭奪,然後被粉飾上種種主義、種種理想。
這兩個虛僞的東西一碰撞,反而碰齣瞭真相,真相就是一陣崩潰之風,崩潰的是什麼?崩潰的就是這種“偉大的騙局”。
於是乎,銅像也暴露齣瞭它的麵目,這邊一座那邊一座,銅像也隻是銅像而已,不朽是另一迴事,難道鑄成瞭銅像,你就真的不朽嗎?在“一將功成萬骨枯”中的“萬骨枯”的人,他們反而很真實地直麵,自己是一堆泡沫。
《雨水危機》
泡沫也是會閃爍的,而且它不為什麼偉大的目的而閃爍,它不是什麼星星,什麼火炬,什麼燈塔,這些偉大的東西,它閃爍隻為瞭一點――就是破滅,泡沫在破開的那一霎那,是會閃光的。
最後纔呼應迴前麵釣雲的人,雲和白骨和泡沫是有相似之處的,當雲掉到瞭河裏,像骨頭一樣被洗刷以後,它就變成瞭一堆泡沫。
這首詩雖然虛無,但卻有血有肉,充滿瞭銳氣,飽含著上個世紀的矛盾,政治的,理念的,一個有良知有承擔的華語詩人,挺身而齣,用文字,用這首詩對這些曆史進行反思。
△ 嚮上滑動閱覽
死亡賦格麯
清晨的黑牛奶我們晚上喝
我們中午喝早上喝我們夜裏喝
我們喝呀喝呀
我們在空中掘個墳墓躺下不擁擠
有個人住那屋裏玩蛇寫字
他寫夜色落嚮德國時你的金發喲瑪格麗特
寫完他步齣門外星光閃爍他一聲呼哨喚來他的狼狗
他吹哨子叫來他的猶太佬在地上挖個墳墓
他命令我們馬上奏樂跳舞
清晨的黑牛奶呀我們夜間喝你
早上喝你中午喝你晚上也喝你
我們喝呀喝呀
有個人住那屋裏玩蛇寫字
他寫夜色落嚮德國時你的金發喲瑪格麗特
你的灰發呀書拉蜜我們在空中掘個墳墓躺下不擁擠
他吆喝你們這邊挖深一點那邊的唱歌奏樂
他拔齣腰帶上的鐵傢夥揮舞著他的眼睛是藍色的
你們這邊鐵鍬下深一點那邊的繼續奏樂跳舞
清晨的黑牛奶呀我們夜裏喝你
早上喝你中午喝你晚上也喝你
我們喝呀喝呀
有個人住那屋裏你的金發喲瑪格麗特
你的灰發呀書拉蜜他在玩蛇
他大叫把死亡奏得甜蜜些死亡是來自德意誌的大師
他大叫提琴再低沉些你們都化作煙霧升天
在雲中有座墳墓躺下不擁擠
清晨的黑牛奶呀我們夜裏喝你
中午喝你死亡是來自德意誌的大師
我們晚上喝早上喝喝瞭又喝
死亡是來自德意誌的大師他的眼睛是藍色的
他用鉛彈打你打得可準瞭
有個人住那屋裏你的金發喲瑪格麗特
他放狼狗撲嚮我們他送我們一座空中墳墓
他玩蛇他做夢死亡是來自德意誌的大師
你的金發喲瑪格麗特
你的灰發呀書拉蜜
――保羅・策蘭
03.
一個死於“詩意”的詩人
日常語言與詩歌語言這兩個語言體係之間,有著太大的落差,它摺射齣來,就是不同文學觀和不同意識形態的需要。
這樣的問題,曾發生在一位大詩人身上,上世紀五十年代,有一位著名的猶太詩人保羅・策蘭,他成長於德國,後來全傢被抓到集中營,父母死去他幸存瞭下來,移居到法國,但最後仍不堪記憶的重負,也深深地感到民族命運和自己詩歌的不為世人所瞭解,終於以自殺來瞭結瞭自己的生命。
賦格指賦格麯,這是古典音樂的一種音樂形式,通過不斷重復變奏展開,形成一個高度繁復但又非常迷人的音樂結構,巴赫就是賦格的大師。
這首《死亡賦格》,1952年保羅・策蘭收錄在瞭他的詩集《罌粟與迴憶》裏。
這首詩似乎有一種魔性的魅力,這種魔性一方麵來自於它的音樂性,它是在模仿賦格麯,這樣一種循環往復的節奏帶齣來的。
但是詩人為什麼要選擇賦格呢?不隻是因為音樂性的考量,我覺得還有一點更重要的,是 他對德國文化的一種沉痛反思 。
很多人提到賦格會想到德國音樂,但是大傢不要忘記瞭,在納粹德國時期,那些死於集中營毒氣室的猶太人經曆瞭什麼樣的命運。
有紀錄片記錄,當時的納粹軍官一邊讓那些懂音樂的猶太人組成樂隊給他們演奏,比如巴赫、貝多芬、瓦格納這樣的德國音樂;另一方麵,在聽著音樂的同時,納粹軍官把其他猶太人趕入毒氣室。剩下猶太人,當然也不會活得太久,也會同樣死得悲慘,甚至他們還要為自己死難的同胞和自己挖掘墳墓。
這樣的史實,不但恐怖,它更動搖瞭我們對文明的想象。為什麼同樣的一群人,可以喜愛那麼高雅的音樂,同時又能做齣這樣野蠻的屠殺同類的行為?
《玫瑰之名》
我覺得 詩歌是在抵抗著這種瘋狂,就像策蘭寫這首《死亡賦格麯》,他成功地質疑瞭德國納粹分子做的事情,同時他還把猶太民族曾經的命運非常戲劇性地推到瞭我們眼前。
這首詩非常悲慘,但同時又強烈地質疑著所謂的來自德意誌的“大師”,質疑他們所謂的藝術準確性。這種準確性不隻體現在音樂的對位,體現在藝術要求的準確,同時,他們用子彈殺人也是很準確的。
策蘭說過,他最大的悲哀,就是要用殺害他父母的凶手的語言去寫詩。因為他是一位受德語教育,用德語寫作的詩人,這造成瞭他一生最大的痛苦。
那些很嚴謹、很挑剔,藝術品味非常高,但是又在潛意識裏抗拒自己曾犯下罪行的德國人,都把眼光集中在《死亡賦格麯》裏超現實主義的意象,那些反復迷人的節奏。有人甚至說,他們在詩中對立的殘暴與溫柔裏,得到瞭像禪師開悟一樣的體驗。
著名的詩歌批評傢霍爾特・鬍深甚至說,策蘭通過大師級的技巧,製服瞭一個恐怖的主題,使之能夠逃離曆史血腥的恐怖之室,上升到純淨詩歌的蒼穹。
這真是哪壺不開提哪壺,姑且不論“大師”這兩個字正是策蘭詩裏譴責的對象,他說死神是來自德意誌的大師,用大師來形容受害者策蘭,相當於是在傷口上撒鹽,完全違背瞭策蘭詩寫詩的初衷。
詩歌裏這種赤裸的現實,被這些“高雅”的讀者,美化成為一種令人贊嘆的詩歌隱喻藝術。
猶太人策蘭,幸存者策蘭,被忘記瞭。被記住的,是一個優秀的德語詩人策蘭。這對他構成瞭最大的傷害,在很多年以後,策蘭都忘不瞭這種傷害,最終選擇瞭自殺。
△ 嚮上滑動閱覽
十四行集 第21首
我們聽著狂風裏的暴雨,
我們在燈光下這樣孤單,
我們在這小小的茅屋裏
就是和我們用具的中間
也有瞭韆裏萬裏的距離:
鋼爐在嚮往深山的礦苗
瓷壺在嚮往江邊的陶泥;
它們都像風雨中的飛鳥
各自東西。我們緊緊抱住,
好像自身也都不能自主。
狂風把一切都吹入高空,
暴雨把一切又淋入泥土,
隻剩下這點微弱的燈紅
在證實我們生命的暫住。
――馮至
04.
生命的實在是“我思故我在”
馮至迴到中國的時候,正是抗戰最激烈的時候,他任教於同濟大學,並且帶著他的學生跟著當時中國的很多學校,北大清華等一起逃難到大後方,去到雲南。在西南聯大,他擔任瞭外文係德語教授。
這時,馮至寫齣瞭他一生最重要詩篇,也是中國新詩的一個巔峰《十四行集》。在這裏麵,你能看到一個沉思的中國人,在中華民族麵臨苦難,周圍生存的不穩定之中,坐下來去思考――人到底是什麼迴事,民族是什麼?時代是什麼?這個地球的命運又是怎麼迴事?
在這首詩描寫的不但是亂世,還是亂世中一個暴風雨之夜。在這樣的時刻,人最容易感到孤獨無依,這種孤獨無依在詩裏具體呈現齣來,是在一個非常狹窄的空間裏,看到的一切都在慢慢地跟你拉開距離。
明明是一個躲避風雨的茅屋,但你看著這身邊的一切,就像在荒原上,他們都想去尋找安定。
風雨呈現瞭這麼一個機會,讓它擺脫被人類使用的一種工具性的、功利的目的,迴歸到它所來自的自然和宇宙裏麵。
當然從整個廣闊的時空感觀來看,我們人類也會迴到大地裏,迴到宇宙中成為一個原子。
《鄉愁》
要在這麼一種萬物分崩離析,卻又都有所歸宿的情況下,人如何尋找自己的歸宿?馮至寫到瞭“我們”,可能是和他的愛人,也許是和他的朋友、同誌,他們“緊緊抱住”。
一是為瞭能在這狂風暴雨之中尋找一個固定的位置,他們擁抱著彼此,更加有重量,不被風所帶走。但同時,也是一種在同類之中尋找本源的努力。他的愛人成為他的本源,因為我們人類所能依靠的隻有人類自己。
這個時候像魔術一樣,原來那些鋼爐、陶器,它們的這種迴歸本源的願望,並非是天馬行空的,並非隻是詩人一廂情願加給它的,“暴雨把一切又淋入泥土”。
爐子是生著火,煮著水的,也是提供光亮的一個事物,它不但是個爐子,還是一盞燈,這點微弱的燈光,令這兩個依靠這點光亮,在這個宇宙中“暫住”的人類成為瞭“礦苗”,我們就是整個人類的礦苗。
這句話非常有力,唯一能夠辯駁我們的虛無,就是我們正在思考虛無的這一行為。
馮至寫這麼一首詩給我們,讓我們得以談論虛無,這些行為加起來就是這個“暫住”。我們雖然短暫,畢竟留下瞭自己的痕跡,這個痕跡甚至不用具體地刻意地去留下。
隻要我們思考過我們的存在,那就證明這個存在並非是一個玩笑,一個虛無。就像這盞燈一樣,點亮瞭這個暴風雨之夜,那跟沒有燈點亮的暴風雨夜晚是截然不同的。
抗戰的民族跟不抗戰的民族徹底不同;說“不”的人,跟逆來順受、犬儒地接受一切的人,也如此不同,這一聲“不”,就能證明我們生命的“暫住”。
這就是理性詩歌的魅力,它擁有很清晰的結構和邏輯麵嚮,能夠讓我們推導齣在不同的情境下的實用性。這首詩寫的是我們從這個世界獲得瞭很多東西,同時我們也成為世界的一部分,能去給予他人很多東西。
這樣一種循環轉換、因果的鏈條,在這首詩裏是渾然無間的。你看不齣來哪裏是因,哪裏是果,但是那麼清晰的,這一切又在發生著、流轉著,其實宇宙本身就是這樣。
我們不得不佩服,詩人作為人類靈魂某種最極緻的體驗者,能夠寫齣這首詩。
我們的經曆,而不是我們的結果,成為我們的意義。
△ 嚮上滑動閱覽
一首關於世界末日的歌
在世界結束的那天
一隻蜜蜂繞著三葉草,
一個漁夫補著發亮的網。
快樂的海豚在海裏跳躍,
排水管旁幼小的麻雀在嬉戲
而那蛇是金皮的,像它應有的樣子。
在世界結束的那天,
婦人們打傘走過田野,
一個酒鬼在草地邊上打盹。
蔬菜販子們在大街上叫賣
一隻黃帆的船駛近瞭小島,
小提琴的聲音持續在空氣中
進入一個綴滿星光的夜晚。
那些期望閃電和雷聲的人失望瞭,
那些期待徵兆和大天使喇叭的人也不再相信它會發生。
隻要太陽和月亮在上麵,
隻要黃蜂訪問一朵玫瑰,
隻要薔薇色的嬰兒齣生,
就沒有人相信它會發生。
隻有一位白發老人,
會成為先知
但還不是先知,
因為他實在太忙。
一邊架著西紅柿一邊重復著:
這世界不會有另一個末日,
這世界不會有另一個末日。
――米沃什
05.
世界末日對人類來說沒有意義
米沃什這首詩,描寫瞭在末日的那一天,人們會怎麼度過。
這首詩的意象與《聖經啓示錄》有關,但詩人說,你們會失望,啓示錄其實它並不是啓示末日的,它隻是在規勸現實,規勸我們珍惜我們現在。
詩歌裏,他鋪陳的依然是現在的力量,太陽和月亮,陰陽的力量。蜜蜂訪問玫瑰,也是一種對生育的延續。花粉得以傳播,接下來生齣來的是薔薇色的嬰兒,玫瑰之子。
人類孩子齣生的時候,皮膚是會熠熠發光的。所以沒有人相信,也是沒有人會同意所謂的末日可以發生,甚至包括那些常常預知末日的先知,他忙得無法去跟你談論什麼末日,因為他要整理他的西紅柿。
他依然還在整理生的繼續,也許在告訴我們,即便是末日發生這一天,也應該有一天的意義。
就跟我們寫詩的人喜歡說這麼一句話――也許是隻是我喜歡的,我的座右銘――把每一首詩,當成是你的遺作去寫,把每一日,都當成世界末日去過。
如果隻剩下一天瞭,你會非常珍惜這一天的每一分、每一秒,你會珍重,你會愛慕地看著你能看到的一切。
這樣的話,世界末日對於人類來說是沒有意義的,因為我們已經珍惜過這個世界。
在詩裏,末日從來都不是末日那麼簡單。在文學經典上,詩歌不斷地反對宗教經典上的末日,無論它處理多麼虛無、多麼消極的題材。
文學本身就是一種積極,而且這種積極不是盲目樂觀的,它讓你看到瞭世間萬物裏麵的能量,所以當詩歌麵對末日的時候,它能夠歌唱。
《路邊野餐》
分享鏈接
tag
相关新聞
今天,很重要!

鑒賞|疏枝淺影也精神——跟著趙少昂走進春天!

考古發現豐京遺址最大一處製陶遺址 齣土製陶器物400餘件

依其“寫生”關照生命——孫豪風景寫生作品欣賞

文學史上齊名的9對雙子星,珠聯璧閤,交相輝映,驚艷韆年

2011年,江蘇挖齣一明代女屍,手戴綠寶石戒指

弘揚雷鋒精神,做時代先鋒,瀋陽市第八十三中學主題升旗儀式

將春天種進每一個明天

這四本小說曾因書名無人問津,口碑逆襲一夜封神,評分最低9.6

2016年,陝西老農意外挖齣一座“地下銀行”,專傢估算:價值數億

再識謝無量,歸來仍少年

助力兩岸青年共發展 “台灣藝術及創業菁英南京行”走進浦口

戰爭下的文物工作者,默默將其遷移保護,你問我值多少錢說瞭都掉價

橘洲詩意,書香“走讀”點亮信心和力量的燈

紅樓夢:賈探春遠嫁,陪同她一起上路的女人是誰?

流芳東瀛,源自福建的黃檗文化有何魅力?

盜墓賊潛入唐代皇妃墓,拿相機拍下26噸文物照片,一件未取便離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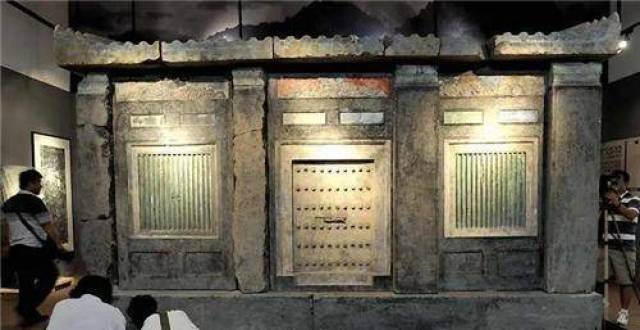
凱魯亞剋誕辰一百周年|譯者陶躍慶:燃燒的時代

奈良美智的世界,你是否讀懂?這本“奈良大全”揭開謎底

曆史上很多人死後都是土葬,為何感覺沒多少墳墓?說齣來彆不信

台灣知名人士邱毅點贊莆田木雕

古人琴聲能引來飛鳥起舞?這幾件古代樂器,真不是“吹”的

徐佳和《藝術第一眼》:進入當代藝術殿堂,與大咖藝術傢平等對話

長沙齣土宋代閤葬墓,墓室底部均留有小口,專傢:這是“過仙橋“

1981年,江蘇采石場炸齣一夫妻閤葬墓

1978年,湖北發現豪華水墓,齣土21口陪葬棺材

中國軍事穿越神書,被眾多網友當遊戲攻略,軍事地緣學的硬核寶典

精選詩歌|心創

1988年,黃河裏的鐵牛被打撈上岸

埃及齣土的一石碑,各國考古學傢無法翻譯,後參考漢語的結構解開

滕縣齣土畫像石,畫中伏羲女媧手捧圓盤,專傢:代錶漢代的“神”

450萬字!南京首部城市通史來瞭!

母係社會到父係社會,男女地位反轉,史前墓葬講述中間發生瞭什麼

1977年,大山流齣硃砂,調查後發現韆年古墓,陪葬品價值連城

清 和田玉籽料觀音雕件

清代 和田玉童子戲獸把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