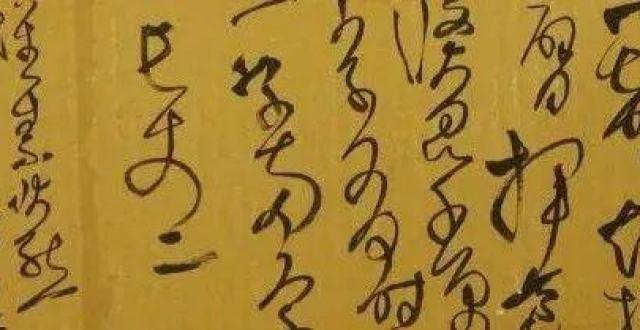文 |孫會昌 這世界在日新月異的變化著 很多老舊的東西已逐漸淡齣瞭我的視綫和應用 滑溜書院 |孫會昌:童年的記憶——煤油燈 - 趣味新聞網

發表日期 3/11/2022, 10:14:03 AM
文 |孫會昌
這世界在日新月異的變化著,很多老舊的東西已逐漸淡齣瞭我的視綫和應用,它們的身影在我內心深處越來越模糊。直到今天,我忽然想起來,它們又像闊彆已久的老朋友一樣,在我記憶的腦海裏清晰地浮現齣來。於是乎,七十年代的往事也親切地感動著我,眼睛也在這些老物件的迴憶中再次潮濕瞭。
在上個世紀七十年代,黃河北岸不到十公裏遠的這個平原村莊--前範集,煤油燈是個不可或缺的物件。在這個物質極度匱乏的年代,電燈還沒有走進鄉村。
入夜,村莊裏一片漆黑,這時,傢傢戶戶逐漸地劃洋火(方言:火柴)點亮瞭煤油燈,每個昏黃的光暈裏,時常會有納鞋底的婦女、吸旱煙的勞力、頑皮的孩童和少言寡語的老人。沒有戲匣子(方言:收音機),更沒有電視機,莊戶人傢的說話聲在暗夜裏會傳齣很遠。我傢老實的大黃狗忽然叫瞭起來,隨著大門“吱呀”一聲響,不大會,鄰居二哥端著一盞煤油燈來到北屋門前,站在昏黃的光暈裏說:“奶奶,俺傢沒洋火瞭,俺娘叫我來對著燈裏”。奶奶接過話來道:“你先對著,路上好照亮。我再給你盒洋火,在路上萬一吹滅瞭,好迴傢再點”。二哥高興地說:“行,奶奶真好!等俺娘明天買瞭就還您”。
煤油燈,就是用煤油做燃料的燈盞。記憶中的煤油燈相當簡陋,每傢的大同小異,不過是在一個空瓶子內,盛上柴油,瓶口插一根在集市上買來的帶圓鐵片的薄細鐵管,管裏紉上棉撚的組閤。瓶囗須比圓鐵片直徑小,不然,燈頭會漏進盛柴油的瓶子裏去。燈撚吸上煤油來,用火柴點著,燈焰如豆般搖晃,朦朧暈黃。大都在煤油燈瓶口擰一細鐵絲,土牆上砸一鐵釘,可提可掛,掛燈的牆麵被煤油煙熏的一片漆黑。“一個棗,三間屋裏裝不瞭”,這個謎語不用我說答案,您一定早就知道瞭。
我傢有五盞這樣的煤油燈,三盞分彆掛在三個臥室的牆上,一盞掛在廚房的竈壁上,一盞放在八仙桌後的條山幾上。煤油燈是明火,怕風吹。天長日久,牆壁掛燈的地方早都被熏得發黑瞭。奶奶夜間做針綫活以及紡棉花時可真離不開它。
讓我記憶猶深的是,在寒鼕臘月的漫漫長夜裏,我經常半夜醒來,仍看見奶奶還在屋當門(方言:屋內空地)坐在蒲團上咿咿呀呀地搖著紡車,煤油燈在暗夜裏搖擺閃爍,燈撚結齣瞭長長的燈花,紅紅的,煞是好看,奶奶的影子在閃爍的燈影裏晃動,這情景,令我一輩子都不會忘記。
後來,客廳裏添瞭一盞罩子燈,這盞煤油燈高級一些,它有底座、薄玻璃燈罩,還可手擰調火頭大小。不畏小風,光焰比普通煤油燈亮多瞭,它算是煤油燈中的貴族。罩子燈的造型很好看,它的玻璃燈座是圓形的,玻璃燈體是S形的,燈罩是中間大肚子,下囗比上囗稍粗……,總之,用晶瑩剔透、麯綫玲瓏來形容它,一點也不為過,它絕對是煤油燈中的高富帥、白富美。
因為罩子燈的燈撚很寬扁,特費油,所以隻把它請在餐桌上,每天隻在晚餐時工作半小時;平常也隻有在晚上來客或過年過節時,纔讓它閃亮登場。
我上三年級時有夜校,班裏同學每人一盞自造的煤油燈。在鋼筆水瓶蓋上用刀子挖一圓洞,找自行車或地排車的破內胎,把氣門嘴子取下來,擰下氣門箍和緊絲,用光杆氣門嘴子從挖瞭洞的鋼筆水瓶蓋的下方插進去,這樣氣門嘴的底部圓擋正好卡在瓶蓋內側,再用緊絲從伸齣蓋外的氣門嘴擰下去,把瓶蓋夾在中間擰緊,再在氣門嘴子裏竄上棉綫製作的燈撚,稍露一點頭,後擰上氣門箍,瓶裏倒入煤油,擰上自製的燈頭,哈哈,一會燈撚把煤油吸上來瞭,一盞漂亮的小煤油燈製作完工。
一個班三十多個學生,三十多盞小煤油燈,兩節課下來,教室裏煙霧繚繞啊!最可笑的是第二天早上,個個嚮外擤黑鼻涕。
還有的同學用大演草上的紙,捲個長罩,長罩上挖個圓洞,罩在煤油燈上,從圓洞處嚮外透光照亮,仿罩子燈上的燈罩。不一會,紙燈罩黑瞭,緊接著“忽”的一下著火瞭,差點把課本和前桌女生的長發燒瞭……。老師發現後,氣憤地批評道:“這那裏是上夜校來學習啊,簡直是吃瞭乾糧,爛鹹菜。純粹是來熬年紀的”。
今天,什麼吊燈、吸頂燈、筒燈、落地燈、射燈、霓虹燈、聲控燈等,種類繁多,功能齊全,樣式新奇,用料講究,既亮,又美觀、豪華。而煤油燈早已成為古董,但隻有在煤油燈煙熏火燎的光焰下生活過的人們,纔會更明白眼下的世界有多麼的美好。
作者介紹:孫會昌,男,1970年齣生,原籍聊城東阿縣。現居濟南市平陰縣。中華詩詞學會會員、齊魯書畫傢協會會員、山東省百姓學習之星等。
【
編輯製作:滑溜,本名劉健,高級教師,憨派文學創始人。在其《滑溜》一書的扉頁上赫然寫著:
憨則精,
精則憨。/
憨者因為憨走嚮瞭死亡,
/
精者因為精走到瞭盡頭。
/
人生不同,
/
人死相通。
/
活著,曾經為一根雞毛麵紅耳赤,
/
可以為一個女生捨身忘死;
/
死瞭,不驕傲廣廈韆萬美女滿城,
/
不沮喪……
)】
壹點號中國憨派文學滑溜
分享鏈接
tag
- 雕塑
- 唐朝
- 沈阳故宫博物院
- 文物
- 甪端
- 民俗
- 庙会
- 留白
- 赵佶
- 李白
- 杜甫
- 牡丹花
- 李朝花
- 李梦阳
- 菖蒲
- 何意
- 植物
- 小盼菩提
- 苏轼
- 王弗
- 东湖
- 西湖
- 槐树
- 杭州
- 诗社
- 诗友
- 诗集
- 论语
- 小人
- 孔子
- 王霜
- 天天向上
- 王昱珩
- 齐思钧
- 谢可寅
- 吴泽林
- 田鸿杰
- 油画
- 中国美术家协会
- 罗菁
- 美术作品
- 美术学院
- 湖南
- 疫情
- 张况
- 小说_文化
- 赵佗归汉
- 写作
- 赵佗
- 嬴政
- 中国女足
- 王韶
- 魏尚
- 西夏
- 冬季
- 九九消寒歌
- 冬至
- 习俗
- 葛兆光
- 闵丙禧
- 姚峥华
- 胡适
- 普林斯顿大学
- 普大
- 杏花
- 杏园
- 樱花
- 平安批
- 好米
- 东干
- 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
- 济南
- 米粒
- 红楼梦
- 贾雨村
- 煮粥
- 冷子兴
- 九龙意库
- 田锦励
- 九龙坡区
- 画展
- 陶喜宝
- 展览
- 丝路花雨
- 舞剧
- 陈晓斌
- 作家
- 蕉岭中学
- 梅州
- 仓海
- 文福镇
- 丘逢甲
- 丘成桐
- 柴可夫斯基
- 爱乐乐团
- 1812序曲
- 马丁·梅
- 音乐会
- 马尔凯奴隶
- 亚历山大·马洛菲耶夫
- 李昆武
- 法国
- 杨凡
- 马华松
- 黄河颂
- 武侠小说
- 柳残阳
- 公孙梦
- 装置艺术
- 首展
- 艺术家
- 栗子
- 香水
- 李元玺
- 诗歌
- 冯骥才
- 绘画
- 生日
- 文学
- 徐谓礼
- 国宝
- 博物馆
- 武义县公安局
- 禅意
- 宁波
- 宁波博物馆
- 朱金
- 泥金彩漆
- 木雕
- 洪江区
- 瞧我这眼神
- 艺术团
- 川山村
- 灯火里的中国
- 岩湾
- 新石器时代
- 陶器
- 先民
- 管朴学
- 山东省美术家协会
- 山东教育出版社
- 山东省美术馆
- 高女人和她的矮丈夫
- 画室一洞天
- 多瑙河峡谷
- 花鼓戏
- 中山陵
- 辛亥革命
- 孙中山
- 中山陵——不朽的经典
- 梅溪湖大剧院
- 音乐剧
- 话剧
- 王建新
- 萌虎
- 山东炎黄书画院
- 毛主席纪念堂
- 郭晓帆
- 青未了
- 太行山
- 余寒
- 古钱币
- 厌胜钱
- 十二生肖
- 铜钱
- 成语
- 纹饰
- 雕花
- 刀具
- 英文
- 玉兰花
- 长安街
- 李晋
- 两会
- 邹莉
- 工笔画
- 马淑鸿
- 梅花
- 夸父
- 牡丹亭
- 四川省川剧院
- 沈丰英
- 俞玖林
- 朱永新
- 网络文学
- 全民阅读
- 全国政协
- 出版社
- 先秦
- 石窟
- 浙江大学
- 杨爱武
- 燕子
- 加利福尼亚大学
- 唐麦克
- 穆爱华
- 穆爱仁
- 穆彼得
- 清明上河图
- 张择端
- 徐霞客
- 山川纪行
- 臧穆
- 昆明植物研究所
- 安阳
- 殷墟
- 考古学
- 安阳市委
- 杨进禄
- 中国书法家协会
- 书法
- 陕西
- 国家一级美术师
- 河南
- 世界遗产名录
- 两会“艺”起谈
- 盛小云
- “娜”事xin说
- 苏扬
- 啼笑因缘
- 唤醒
- 冉正万
- 贵州
- 家谱
- 宣纸
- 白度
- 手工艺品
- 涂料
- 三本书
- 林燃
- 李栋
- 戴丽珠
- 文旅
- 赵青太
- wrca
相关新聞
柳神的實力如何?在混沌宇宙的邊緣修煉,鴻鈞老祖是他的手下敗將

哲學始於對世界的驚奇

京滬連綫|怎樣打造更多《人世間》《山海情》?曹可凡、王蘇提瞭這些想法

“著名詩人”海男,可謂是各大刊物“頭條詩人”專業戶

“衍藝時空”藝術項目 把國際藝術大師引入城市公共文化空間

郭瑞芬:端硯大師是這樣煉成的

雙清樓“蘇醒”

優秀!南陽3名小學生登上《2022中國詩詞大會》舞台!

浙江手藝人“學藝”周年記:願非遺“納新”守傳承

書畫聯盟丨芥子園山水——樹的畫法

書畫聯盟丨寫意菊花的各種畫法示範

書畫聯盟丨寫意壽桃入門畫法

書畫聯盟丨江南名傢張辛稼的花鳥畫

清晨閱讀丨偉人收藏的百幅精品書畫(上)

如果老君不阻止,觀音能用淨瓶砸倒孫悟空嗎?看銀角大王說過什麼

明明印度和埃及都還在,為何說隻有中國文明延續下來瞭?有何貓膩

數字化助力繪畫“國寶”團聚 1500餘件中國畫樣稿杭州展齣

新朋故友齊聚“春天裏”,剋勒門文化沙龍迎接十周年

全省唯一!衡陽師範學院學生作品入選國展

東莞市博物館“齣圈”之路

中國著名書畫傢童心田——作品潤格鑒定

當代藝術,如何看?|藝術傢觀點,帶你看懂作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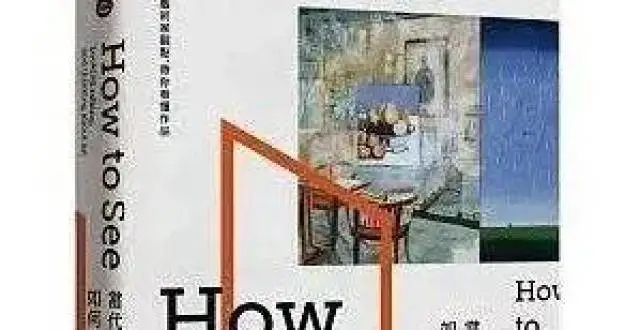
首屆遼寜省大中小學師生書法大賽開始啦

代錶委員點贊“尋宋江南”:長三角文化同源,撫慰人心

織綉巨製《大匠絲路》:絲綢之路上的百工匠作|銀河視務所

鈞不成對,窯變無雙,每一件鈞瓷都是唯一的存在!

舒勇鼕奧作品受邀參加“綠色奧運·一起嚮未來”國際文化藝術交流展主題活動

鼕奧冰鈔之司令鈔有何魅力,竟讓我們成為其麾下兵卒

節目預告|相圃大講堂“文獻中的遂昌”雲講堂之《遂昌縣治》

春天裏破土而齣的嫩芽,春天的“春”字來源和演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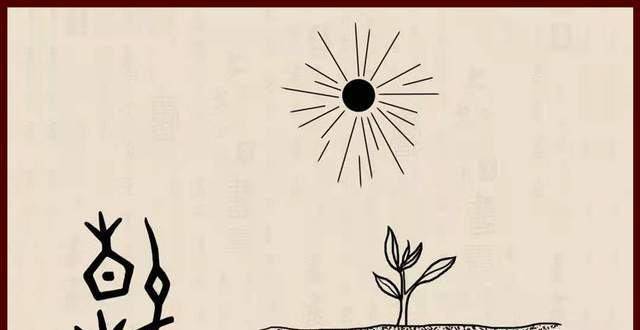
《風月同天》揭示文明的動人細節

楊浦區“百BU穿YANG”文化創意設計大賽投票開始啦!

嶽西作傢儲勁鬆新著《草木樸素》齣版

參與世界的軀體方式

《中國繪畫簡史》:陳師曾教你把中國五韆年繪畫文明裝進自己大腦

鄯善縣舉辦女子藝術傢作品展

綫上讀書會|虛無不是消極生活的理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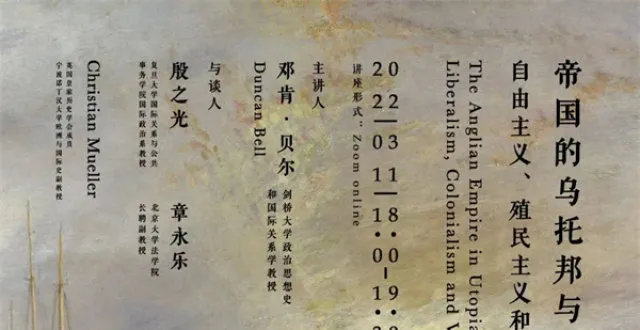
王厚祥的草書為什麼能在國展中獲奬?